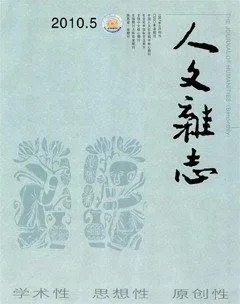中國哲學本體論中的有限性視域
內容提要在中國哲學本體論中,有限性視域相對于無限性視域如“天道”、“天理”或“太極”等而存在。有限性視域與人的存在相關,主要以經驗世界為研究對象,其之所以存在的根源與人、器物和事理的有限性直接相關。在中國哲學本體論中,有限性視域具有重要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其意義在于為人類提供了一條現實的有限超越之路。
關鍵詞 有限性 經驗世界 人 物化 有限超越
[中圖分類號]B2;B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0)05-0043-08
在中國哲學本體論中,有限性視域相對于無限性視域如“天道”、“天理”或“太極”等而存在,其主要指向有形、有象的現實存在的現象世界和經驗世界,對有限性視域的本體論探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從根本上看,其構成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基礎。
有限性視域的本體論研究對象
一般而言,在任何哲學的本體論研究中,哲學家們所面對的世界,往往是有形、有象的現實存在的世界。比如,《周易》對本體世界的追尋是從“立象”和“設卦”開始的,即“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象”是指某種物象,所謂“象也者,像也。”可見,“象”就是指具體的物象存在。“立象以盡意”是指,一旦把“象”所指向的具體物象確定下來,就可能透析出其存在的意義。同樣,“卦”也表現為具體現象的存在,設立“卦”的目的也是為了尋求研究對象的確定性,從而達到通曉“情偽”的目的。
從時間起點的角度看,對有形、有象的現實世界的認識,必須存在一個起點、開始或源頭,才能達到對本體的認識。老子在《道德經》中說:“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這里的“紀”是指規律或道理,也就是說,只有從起點上進行認識活動,才能發現“道”的規律。本質意義上,這里的起點無疑是有限性視域的有形、有象的現實世界,只有這個世界才能出現在時間或邏輯起點上,被我們感覺和思維,被我們把握。
中國哲學中的有限性視域與康德哲學中對經驗世界的規定頗多一致之處。在康德哲學中,經驗世界是首先存在的確定世界,無論從邏輯起點或時間起點看,人類的認識都是從經驗開始的。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因為,如果不是通過對象激動我們的感官,一則由它們自己引起表象,一則使我們的知性活動運作起來,對這些表象加以比較,把它們連結或分開,這樣把感性印象的原始素材加工成稱之為經驗的對象知識,那么知識能力又該由什么來喚起活動呢?所以按照時間,我們沒有任何知識是先行于經驗的,一切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的。”在康德哲學中,“經驗”是一個在認識的基礎上確定其內涵的基本概念。“經驗”一方面指感性材料即感覺,另一方面指科學。在康德看來,科學、經驗和自然界都是同一的。所以,經驗世界在康德哲學中,無論在邏輯起點或時間起點上均處于起點位置。
從經驗世界中一般現象的角度看,有限性視域中的經驗、事實或現象,并不必然呈現為“道”的狀態,倒往往表現為紛紜、繁雜、無序甚至混亂。如何使現象世界歸于有序和統一?
儒家從“正名”開始應對現象世界。“名”相當于“概念”,概念具有規范性,某一存在如果具有概念的規定也就被賦予了相對的確定性,“正名”就是尋求規范性、確定性和秩序性。當子路問孔子,如果fvuqGbCUQGciHRojLen7AquP417s0PrYYD4PReFNjCc=從事治理國家,以何為先?孔子明確答復:“必也正名。”這里的“正名”不僅僅是指正社會關系之名,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從更深的層面看,其包涵著賦予世界以普遍秩序(使事物各有條理而不妄)之義。由此,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實”的理論。“制名”就是確立規范性,“指實”即以“名”指稱或表示實在,使“名”與“實”呈現出對應關系,從而為把握現象世界提供可能。
道家應對現象世界的態度與儒家“正名”的思路略有不同。雖然道家也承認“名”的存在和“制名”的必要性,如“始制有名”,但關鍵在于道家認為“名”具有局限性,甚至認為“道”也沒有永恒的“名”,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此也就不存在“正名”的問題。道家面對現象世界,不是從名實之辨而是從有無之辨探尋萬物的規范性、確定性和秩序性問題。所謂“有”是6enGy4i7ub+74GP/gy6fKYUmRh1WAT2U1IgMLAhvtps=指現象的存在,“無”則指向對存在的否定,如老子認為,“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是萬物之母。二者本質上是“同出而異名”的關系。從有與無“同出而異名”的角度看,老子的有無之辨是在同一個層次上展開的,所謂“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具體事物(有)由看不見的‘道’產生”。“有生于無”是在“反者道之動”的層面上揭示的“有無相生”之義。在同樣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生于有。”這里的有無之辨,即“有生于無”、“無生于有”或“有無相生”,是在一個“是”或“存在”的視域中展開的,其相當于西方哲學中的“是論”或“存在論”(On-tology)。
雖然儒家和道家應對現象世界的方式不同,但從探尋現象世界的規范性、確定性和秩序性的角度看,無論名實之辨還是有無之辨均具有一致的目的。儒家的“制名以指實”是以“正名”達到認識事物實在和本質的目的,道家的“有無相生”則似乎更突出對天地萬物的生成、本原及規律等認識,這與儒家追問人、物或事的實在或本質無疑具有一致性。所以,在有限性視域中,中國哲學家共同的研究目標和對象均指向了對天地萬物規律的認識和揭示。如韓非子明確把“道”說成萬物的規律,并提出標志事物規律的“理”的概念與之相應。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稽也。”“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這就是說,“道”為規律,“道”、“理”相應,萬物莫不遵循“道”的規律。這里強調了“道”的作用和地位,但同時又突出了“萬物”遵循規律的重要性,這依然是有限性視域中對天地萬物規律認識的展開。
從哲學的發展看,在有限性視域探詢現象世界的統一性和規律性,一般在兩個層次上展開。其一是在時間先后或生成順序的層次上,探討萬物之所以產生的宇宙根源;其二是在抽象存在形態上探討天地萬物存在的總規律。一般將前者稱為宇宙本原論,將后者稱為宇宙本體論。實質上,在中國哲學中,以上兩個層次并不完全分離,其雖然是在不同視域下展開,而最后均達到殊途同歸的目的。比如,在生成論的層次上老子認為:道“為天下母”,但同時也在宇宙本體論的層次上規定:“道者,萬物之奧”。“母”象征著存在的本原或初始的形態,“奧”是形容深不可見之處。“道”為天下母,無疑是在時間發生或生成序列上揭示本原問題。而“奧”則意味著認識不可能達到的終極形態或認識極限的本然形態。二者雖具有不同的視域,但實質上并無截然的分野,無論在時間先后順序還是在抽象存在層次上,其最終目標均指向天地萬物所遵循的統一性或規律性,這依然屬于有限性視域中所討論的問題。
在有限性視域中,以探求天地萬物的統一性或規律性為目標,并不排斥哲學家從不同維度或進路展開探索,從而,其哲學理論形態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比如,從宇宙本原論的進路,對存在的統一性探詢往往以追問世界的始基、基質為形式。“五行”說提出五種基本元素,表現出對存在本原的追溯,即:“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同樣,中國哲學史上的“氣”論,也可以看作是對世界的基質或本原的探詢。張載認為:“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于氣而已。”這里的“道”是指規律,世界的本質存在都統一于“氣”,“氣”構成了存在的基質。對存在的基質追尋,可以看作是對世界存在統一性的追尋,但似乎有明顯的局限性。因為,在把自然元素,如水、火、氣等理解為世界存在本體時,其實質上把存在的統一性問題與世界的構成問題聯系在一起,這就意味著將本體問題轉化為科學問題。科學問題與本體論的建構明顯有異。如熊十力認為:“本體論是究是闡明萬物根源,是一切智智(一切智中最上之智,復為一切智之所從出,故云一切智智),與科學但為各部門的知識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對存在的統一性探詢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還原或追問世界的本原,以揭示宇宙萬物生成和變化的規律。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論,就是將萬物的存在通過回溯而達到宇宙本原。在儒家哲學中,也有類似的對宇宙本原的探詢。如朱子哲學的核心為理氣論,“理”為天地萬物所遵循的規律,即:“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理”在天地萬物之先存在,并產生這個世界的始基或基質即“氣”,“氣”的流行發育,便生成萬物。
當然,無論研究事物的基質或探詢宇宙本原,主要是從對象世界本身尋找存在的統一性。但還存在著不同于從對象世界探詢存在統一性的方式,那就是以主體的觀念性存在為出發點,比如中國哲學傳統中的“心性”論,從身心、從主體心性實踐的角度人手來探索宇宙和人生本質的統一。在宋明理學中,“心學”主張在“心”的基礎上達到世界存在的統一性,從而將天與人、宇宙與人生統一于主體的心性,其明顯是從主體心性的角度,攝合實然與應然、事實與價值。然而,由于這種還原意味著把存在統一于特定的精神現象,這就決定了其依然沒有超越有限性視域。
如果說,宇宙本原論主要是試圖在世界的始基或還原的層面達到世界存在的統一,宇宙本體論則是以抽象的形式,確立存在的普遍性形態,試圖解決有限性視域或經驗世界中的有限性問題。比如,柏拉圖的“理念”、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程朱理學中超驗化的“理”均是如此。其目的是提出超越事物本身的“理念”、“絕對理念”或“理”的概念,并認為只有“理念”或“理”具有真實性和絕對性,以此確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統一存在的形態,以解決現象世界的有限性問題。但從另一方面看,抽象形態的形而上學是在經驗世界的存在之外去規定存在,從而易與現實的知行活動發生隔離。雖然形而上學家們用深刻的思辨構筑了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統一存在的形態,但本質上屬于脫離于人的知行的工程。正如克爾凱戈爾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評論:“大多數體系制造者對于他們所建立的體系的關系宛如一個人營造了巨大的宮殿,自己卻側身在旁邊的一間小倉庫里,他們并不居住在自己營造的系統結構里面。”由此可見,以抽象化形式構建一種特定的存在形態,不僅不能解決有限性問題,反而因其抽象化,存在易于被消解于觀念的形態,從而失去實在性。
有限性視域的本體論根源
在有限性視域中,無論是探尋世界存在的始基、基質或本原,還是抽象形態的形而上學,在根本上均表現出有限性或片面性特征。為什么會出現這一有限性特征呢?中國哲學家們對于有限性的思考無疑具有多重維度,其主要涉及到的是經驗世界中人、器物和事理的有限性問題。
人的有限性具有多種表現,比如生命的有限,莊子曾說:“吾生也有涯。”怛在哲學層面,人的有限性問題主要表現為人認識能力的有限。康德哲學對人的認識能力的研究,正說明人的認識能力僅局限于現象界,人只能認識現象,現象界之外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認識無法把握的。康德認為,對純粹理性的能力的批判表明,我們只能認識到對象中那些由我們理性所放入的東西,而形而上學則力圖借助于純粹理性,也即先天概念來認識。對純粹理性的批判使我們相信,認識是不可能越出經驗的范圍的。,在經驗中并不提供上帝、自由和靈魂不死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從純粹理性中揚棄它對上帝、自由和靈魂不死的奢望,揚棄對人是一般先驗對象的奢望。康德揭示出,由于人局限于經驗世界,其認識能力不可能超越經驗范圍而進入無限領域,去把握上帝、自由和靈魂不死。由此可見,人的認識能力表現為有限性。
中國哲學家也從不同角度揭示人的認識能力有限性問題。比如,老子對“名”的有限性的探討,實際上內在地反映出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性的思考。老子認為:“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這里的“制”是制造、制作之義。在無限性視域中,“道”以自身為根據永恒、獨立存在,這樣的存在是無法用經驗性之“名”來概括和說明的。人認識“道”就必須使“道”成為經驗的對象,這就需要“制名”。“制名”就是起名。從認識規律看,“制名”的目的是在對象中把握實在,即“制名以指實”。在此意義上,對象與認識的關系,似乎不僅僅在于“制名以指實”,而且也在于“指實以制名”,即“制名”在認識活動中具有必要性。但在根本上,由于“名”是有限性視域具有自身局限的規范,某“名”一旦確立便被賦予了相對的確定性,即蘇轍所說:“凡名皆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因此,雖然老子肯定“制名”的必要性,但對其局限性也有清醒的認識,即“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是知道止于何處之義,其顯示了對“名”的限定或限制。以上老子對“名”的必要性和局限性的揭示,無疑涵有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性的深刻思考。
在現實世界中,由于自身局限,人往往表現為“不該不遍”的“一曲之士”,大多數“一曲之士”往往局限在自身立場而對他人立場展開批評甚至攻訌:“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與心斗。縵者,窖者,密者。”莊子對“一曲之士”的批評,并非局限在人類的個別性中,而是普遍性地展示了一幅人類有限性的畫面。
與人認識能力有限性相關,人在情感和價值領域也表現出有限性。莊子指出:“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也,涕泣沾矜;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床,食縐卷,而后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表面看,莊子是談論人生無常,但實質上揭示了與人認識能力有限性相關,人在情感和價值領域也表現出的有限性。與人所處的具體境域相關,對事物的厭惡與喜好的評價,對于幸福與痛苦的感受,無不是暫時性的、條件性的,因而表現出有限性。莊子以麗姬被俘時的痛哭與得寵于晉王后的對其痛哭的后悔為例,說明人對于好惡的評價受制于外在環境和自身局限;以“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為例,說明人的苦樂情感具有不能自主的限制。當然,從本質上看,人在情感和價值領域所表現出的有限性依然與人認識能力相關。
從器物層面關照有限性,是哲學家們對于有限性思考的又一維度。所謂“器”乃是有形之物,“物”則是指萬物,二者具有一致的規定性,均指向有形的萬物存在。從萬物存在的整體角度看,“天”和“地”無疑是負載萬物的最大存在,但天地在本質上依然表現為有限性,比如老子說:“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天地不能久”是對萬物存在永恒性的最普遍的質疑,由此也就決定了自然現象中萬物具有有限性,所謂:“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不僅自然之物是有限的,人化之物同樣也不例外。《韓非子》中著名的“矛盾”故事,就說明了人化之物的有限性問題。“矛”與“盾”均是人類工具,作為器物層面的工具,其僅具有具體的作用或功能,比如,制造“矛”這種工具的主要目的是進行刺殺,一旦“矛”具有這種刺殺功能,就不可能同時再具備其他功能,這就決定了“矛”的有限性。當然,從“矛”本身的視域看,其可能具有很多優點,比如非常鋒利、美觀、實用、貴重等等,但作為器物層面的工具功能的有限性決定了其不可能超出自身功能而達到無限。當試圖以工具功能的有限性去突破自身說明工具的無限性時,便不能自圓其說,從而陷入二難之地。
與器物層面的有限性緊密聯系,有限性問題也涉及事理層面。一般認為,事物的規律或基本原理具有客觀性和確定性,比如:水往下流、人要吃飯等,但實際上,人在認識和把握規律時所形成的“客觀”標準也要以具體的境域為條件,而不是永遠依照一個標準,這實際上也反映出所謂“客觀”標準的有限性。比如,由于地球萬有引力的存在,水一般往下流,但這也是一個有條件的規律和標準。孟子說:“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撤之,可使過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勢”是指趨勢或趨向,事物的規律也是以變化的趨勢或趨向而變化。同樣,人要吃飯是一種事實,但如果是“嗟來之食”,則有人寧可餓死也堅決拒絕吃飯,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哮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當然,內在地看,“水可過桑”的現象其依然內在地含有地球萬有引力規律的存在;不吃“嗟來之食”似乎也內在地包含著“人要吃飯”這一事實,而僅僅是在事物存在條件改變韻情況遮掩下了“水無有不下”的一般規律,或者在價值的維度上掩蓋了“人要吃飯”的事實緯度,這似乎并沒有否定水往下流、人要吃飯等一般事物的規律。但中國哲學家在認可“水可過桑”或不吃“嗟來之食”時,并非缺乏事理層面對事物規律或基本原理的認識,而是在事實性的基礎之上,確定了超越事理層面的非單一性的維度。在此維度下,中國哲學家顯然認為“水可過桑”或不吃“嗟來之食”的主張正好反映出事理層面的有限性問題。
最后,由于萬事萬物的有限性,決定了在有限性視域中,其總體上表現為“反者道之動”的相對性特征,即莊子所說:“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目物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莊子認為,凡物沒有不存在相對的另一面,也沒有不存在相對的這一面。所以,“彼”和“此”的關系在任何時候都是“方生”即剛剛產生的關系。但“方生”也就是“方死”即馬上喪失。肯定的產生也就是肯定的否定,否定也就是肯定;對的也就是不對的,不對的也就是對的。莊子的以上表述,深刻地揭示出有限性視域中事物或概念的相對性。一般而言,某一事物或概念一旦存在,其就具有了自身規定,從其自身的視域看,其無疑是確定的;但此一事物或概念一旦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就無法具有其所沒有的其他規定性,它的有限性就隨之出現。有限性存在是一種暫時的或有局限的存在,隨時隨地蘊涵著轉化為他物的可能,這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義,由此也就決定了萬事萬物的相對性特征。
有限性存在與有限超越
在有限性視域的各種存在中,人超出動物和其他物種的特征是,人往往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超越特定境遇的存在。無論在認識層面抑或實踐層面之上,人都具有克服有限性的要求和能力。這種要求和能力使得人不僅要在有限性的存在領域展開活動,同時也要超越特定存在的領域。人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在有限性視域或經驗世界中“人之可貴”。老子把人作為“四大”之一,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所言的“道不遠人”,《易傳》的“自強不息”,都可以說是強調人重要性觀念的發揮。
但是,從根本上看,現實存在的世界決定了人不可能超越出這個世界之外,也不可能通過超越特定境遇的存在而使自身的有限性徹底消失,即人在事實的角度永遠不可能取得無限性存在的地位。由此決定了人在有限性視域或經驗世界中的超越方式為“有限超越”。所謂“有限超越”,是以克服人與萬物的有限性為目的,在現實世界實現的超越。雖然這種超越的結果依然具有有限性,但已與此前的有限性有所不同,其體現了在現實存在的世界中超越有限性的一種本體論訴求。
實現“有限超越”無疑具有相當廣泛的路徑和方式,但從本質上看,其首先表現為對“物”的超越。在中國哲學中,“物”是一個具有多重內涵的綜合性概念,如:“物,猶事也。”“事”本質上是人的主體活動,人在與具體對象的關系中才能形成“事”。“物,猶事”這個綜合性判斷揭示出,“物”首先與現象世界相聯系;同時,“物”也與人的存在緊密聯系,“物”在總體上表現為人活動的對象性。對“物”的超越不僅體現為對現實存在對象的超越,同時體現為對人自身的超越。在有限性視域或經驗世界中,雖然“物”表現出有限性的特征,如荀子所說:“萬物為道一偏”,但“物”的本質,即首先作為現象世界的存在,決定了對現象世界和現實事物的超越首先是對“物”的超越。
從超越的方式上看,對“物”的超越同時表現為對“物”的利用或以“物”為中介。荀子說:“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跤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湖。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善假于物”揭示了有限超越的方式、方法就是對“物”的利用或以“物”為中介。“善假于物”中所指之“物”,既是指自然現象中“物”,也指人化之“物”,其總體表現為人在經驗世界實踐活動中對“物”的一種要求。
從“善假于物”的總體要求看,其主要指向對“物化”的要求。所謂“物化”本質上體現為有限性事物對其他有限性事物的憑借。莊子在《齊物論》中通過“罔兩問景”和“莊周夢蝶”的寓言故事說明,“物化”就是在“有分”或“有待”中實現有限性事物的存在。“有分”就是有所分別,揭示的是有限性事物與其他有限性事物的區別性;“有待”就是有所憑借,揭示的是有限性事物對其他有限性事物的依賴性;“莊周”與“蝴蝶”、“罔兩”與“景”無疑是有所分別的有限性存在物,正因莊周憑借“蝴蝶”之夢,“罔兩”憑借“景”的活動,才實現了對其當下處境的超越。
從廣泛的意義看,“善假于物”或“物化”的超越過程在人類社會中,也表現為“制禮”與“作樂”的要求,即建立典章制度和文化通道。從本質上看,“禮”是指需要人在社會中憑借或依賴的規范性存在,所謂“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禮”是人實現安身立命的根本,具有支撐人的存在的重要意義。“制禮”意味著創制出人可以憑借、依賴或支撐人的存在,實現安身立命的社會規范。同時,“制禮”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在現實社會中,憑借“禮”的不斷發展和演進,實現有限超越的過程。
與“制禮”緊密聯系的“作樂”,也可以在寬泛意義上理解為創造人的文化形式或文化通道。如果說,“禮”是人在現實社會中憑借或依賴的規范性存在,那么,“樂”則是人在自然中憑借或依賴的化育性存在,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哀”均是指人的自然情感的表現形式,創造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性的文化通道,這是“作樂”的主要目的。通過“作樂”,人可以穩妥(而非泛濫)地實現其自然情感或自然本性的表現,從而達到其自身的超越。由此可見,在創造文化形式的意義上而言,“作樂”也可以理解為人的一種文化存在形式,人憑借或依賴這種文化形式,同樣能在經驗世界中實現有限超越。
從更深入的意義看,人的理性能力也表現為一種人可以憑借或依賴的存在形式。在西方哲學中,對人的理性能力或理解能力的研究具有各種維度,如唯理論者主張理性認識的可靠性,經驗論者主張感覺經驗的真實性,雖然其各自的出發點或理論基礎并不完全一致,但從其要達到的目的看,都是要確立人的理性能力或理解能力的具體存在形式。比如,康德根據形式邏輯學說來揭示人類知性的能力,按照量、質、關系、模態四種類型,確定了十二組人類知性能力的基本范疇。范疇一旦確定,就同時確定了人類的理性綜合經驗材料的規律。康德的最終目的在于,雖然人類的理性能力具有局限性,但發現人的理性能力的存在形式,也就為人類提供了可以憑借或依賴的工具,從而在經驗世界中實現超越。在中國哲學中,對人的研究同樣呈現出不同維度,與西方哲學確立人的理性能力或理解能力稍有不同的是,其更多地是指向對人的存在本質研究(從內容上似乎內在地涵蓋著對人的理性能力的研究)。如告子的自然人性論,認為:“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東西方也。”但孟子卻明確主張:“人無有不善。”無論是告子的自然人性論,還是孟子的“性善論”,雖然由于其出發點和理論旨趣的差異,決定了理論主旨的差別,但從其各自要達到的目的看,其無疑均是要確立人的存在本質。人的存在本質如果確立,就可以憑依對這種本質的揭示,在經驗世界中實現超越。
需要指出的是,對人的存在本質研究、人的理性能力或任何具體對象的認識,從來就不可能確立為一種終極形態。根本原因在于,作為認識主體的人類自身的有限性,決定了其對于研究對象的認識僅能限于“一偏”即有限性認識,而不可能達到一種絕對化的終極認識形態。正如荀子所說:“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于后,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后而無先,則眾物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荀子對諸家限于“一偏”的批評,實質具有普遍性意義,荀子自身以及整個儒家的理論,也同樣可以視為是限于“一偏”。無論是荀子的“性惡論”,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均是囿于認識主體的有限性,而對人的存在本質作出的或偏于“惡”,或偏于“善”的有限性認識。
盡管人類的經驗表現出有限性的形態,但依然具有重要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其意義集中體現為人類的經驗的不可替代性,或不可或缺性。人類在有限性視域或經驗世界中,唯一可以依賴和憑籍的就是人類經驗,而不是任何天命。《詩經·大雅·文王》所說的“天命靡常”,《尚書·君》中的“天不可信”是對放棄人類經驗、準備投身天命的否決之言。在經驗世界中生存,在經驗世界中超越,是人類無法選擇的無二之路,而終極的“照之于天”的無限性視域就伴隨地存在于人類的有限超越之中。
責任編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