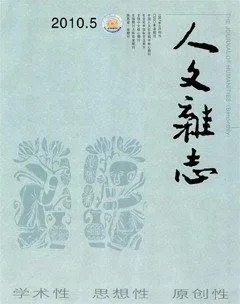時中.時變.時積
內容提要 荀子的禮是獨立于性情之外的禮之理,具有道德理性的知性特征,這種知性不是脫離情感欲望的抽象理智,它的智能正好就表現在把可教化的本能情感和欲求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一種可塑的、發展的普遍性的整體,荀子以遵札為前提,在具體的道德境遇之中,針對不同的情況而采取合乎權時的行為,這種權時的行動是以尊重人的價值為先導;同時,在處理經權關系時,把經所依據的道作為一切行為的根本,而荀子的道就是禮道。在此禮道的規約下,在具體的歷史境遇中恰當地處理道德行為,是孟子所說的“圣之時者也”,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們應遵從穩定的道德規范以及對一定人倫之則的認可。
關鍵詞 荀子 禮 時中 道德境遇
[中圖分類號]B2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0)05-0063-08
教化的本質就是個體在這個現實當中讓人的行為、思維、存在和他的善的本質和終極實體保持一致。對于性善論來說,由于人內心本有善端,只需修養以復明本性,而對于性惡論來說,卻需教化來復返其初,這也是荀子和黑格爾所致力成就德性的必由之路。黑格爾以教化人性、抑制沖動在于回到人之初的自在的不善不惡的倫理境界,而荀子以禮樂涵養性情復歸其樸的君子人格,因此其成德的思維可謂“異曲而同工”。荀子的教化理論源于其自身的情感自證,而禮樂本身緣情化性的特質與功能又賦予人矯情化性的德能。由于性本身不能自化,因而知性的德性教化只能在自然的情上用功而使其處于有所止的時中、時變、時積狀態,在情感與理性、善與惡的沖突中實現自身與社會的相契與和諧。這一思維理路與荀子的知性性格一脈相承。
一、時中:德性教化原則的秩序確認
禮既為教化之綱,又要發揮主體的意志自由,在家庭、國家、社會的不同層面進行教養,從而達到禮的形上意境,對于人生而言,能夠矯情養欲,規范行為;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能夠序長幼、等貴賤、分親疏而明人倫;對于飲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層面,以教化洗滌心靈塵弊,涵養倫理精神,提升道德境界。在不同的道德境遇中,對禮有所損益,因時而動,遇君則修臣下之禮,遇鄉黨則修長幼之禮,遇長輩則修弟子之禮,遇朋友則修辭讓之禮。這就是荀子所謂的“中”或“中道”,也就是禮儀。中是禮的內在精神和原則,禮是中的外在表現和形式,故荀子曰:“曷謂中?禮義是也”(《荀子·禮論》)。中就是不偏不倚,無過而不及,恰到好處。所以荀子把有益手理的事情稱-為“中事”,把有益于理的觀點成為“中說”。其實,“中”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據唐蘭先生考證,“中”在甲骨文中本為旗之類,后引申為中間之義。至晚在西周時期,中間、中央之義已上升為一種美德,成為“中道”,是禮教思想當中一個具有獨特內涵的范疇。在《周易》經文中也多次出現“中”,其中“中行”五見: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避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復·六四》:中行獨復。
《益·六三》:益之用兇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迂國。
《夫·九五》:莧陸夫夫中行,無咎。
參考西周初年的其他一些文獻,這里的中行應該含有倫理的意義。中行即中道,依中正之道而行的意味。正如惠棟的《易經學》所說:“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日時中。”《周易》經文中“中行”包含“中道”“時中”的思想,它把中與人事的吉兇禍福聯系起來,以天道言人事,立中正仁道之極,建立起立靜無欲的道德標準。后來《易傳》在解釋《易經》時,對其中所蘊含的“中道”“中行”思想加以發揮。《乾·文言》說:“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高亨先生注:“李鼎祚曰:‘庸,常也。’按庸由正中而來。正中者,無過,無不及,無偏,無邪也。正中之言乃為庸言。正中之行乃為庸行。”中,教人趨吉避兇的道理,要人行中道之德,達到崇德廣業,有所事功的目的。其實,“中道”也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后來子思所作的《中庸》對孔子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是戰國時期學者論述禮儀的一篇重要文章,說明中已成為禮的重要思想。《禮記·檀弓上》引孔子之言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跛而及之。”這是說制禮的原則要符合中。《禮記·仲尼燕居》引吼子言:“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問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孔子曰:“禮乎禮。”由此可見,孔子對禮與中作了循環論證,說明孔子《中庸》在思想內涵上是一致的。荀子言“中即禮”與孔子所謂一脈相承。在荀子的倫理思想中,禮主分,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中庸、中道思想,這說明禮并不是絕對地區別等級之間的差異,它在辨明等級的前提之下,又主張時中、權變,注重禮的靈活性,在等級差別之間找到一種中庸的和諧。荀子《儒效》云: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為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凡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說失中謂之奸道。
荀子《禮論》又曰:
故其立文飾也至乎窕冶;其立粗衰也,不至于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
文飾、聲樂、哭泣、言說是人的情志與行動,中流、中事、中說是人的情感、意志所達到的一種無所偏倚、不過不及的狀態,這種狀態是禮對心靈的涵養和教化,涵厚人的德性,規約人的行為,使知、情、意三者相互涵容、陶養、化通才能達到。否則,人的情感將流于隘懾,聲樂將流于惰慢,德性將流于卑俗。因而,中是一種行為處事的方式,是倫理的基本原則,是倫理的實然與應然的統一;中,也是行為的目標,體現人類對價值追求的源頭和歸屬。荀子在道德教化中以中釋禮,反映了禮為教化之綱,具全德之名,人的德性的形成是對禮規范的心靈體征、感悟,因而在禮德關系中,以禮釋德,認為禮是社會道德生活和人道的最高準則。“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規矩是方圓的準則,無規矩無以成方圓,無禮則無以成人,禮是人道的準則,是人之為人的標準,禮規范德,體現德,合乎禮的行為才有道德價值。《荀子·王制》曰:“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一旦事親、事兄、事上本根于禮,則這些行為便顯現出道德理性的智慧,分別具備孝、悌、順諸德。《荀子·大略》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后仁也,仁義以禮,然后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后禮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仁如果不合乎禮的要求去做,就不能叫做仁;義,如果不合乎禮的要求去做,就不能叫做義,而在《勸學》中明確指出禮是道德之極,“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指出仁義不能脫離禮而獨自存在,禮是決定仁義之為仁義的本質所在。《荀子·禮論》曰:“存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圣人君子的敦厚、大度、高尚、明察來自于遵循禮、實踐禮的積累和施行呈現在個體身上就是德,實踐先王之道以成就仁義忠節,就是實踐禮以完成、完善仁義忠節諸德。荀子強調“禮義辭讓忠信并舉”,辭讓忠信屬于德,此處的禮儀應歸于德。該篇又曰:“人之所惡者何也?曰:污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污漫、爭奪、貪利是邪惡行為,荀子列舉之作為無德的象征,與之對應并形成鮮明對比的禮義忠信應該屬于其反面——道德,更何況辭讓忠信本來即為德。在此,禮顯示出德的象征。禮不僅是道德之一種,而且還是包括諸多具體規范的人生大德,更是在諸德之中處于優先的地位。即是說,禮為德,又非普通之德,“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忠孝等是道德的個別,禮是道德的一般,是最高的道德。孔子在人生諸德中有標舉仁為人生大德的傾向,孟子沿著這一傾向繼續發展,凸現仁為人生最高之德,荀子便在眾德中指定禮為統攝一切德目的最高理想。“很有可能是荀子受其所抨擊的思孟學派的浸染,而在潛意識里接受其影響的結果。”
荀子德禮的本質是個體與實體、單一物與普遍物的關系。禮作為全名的道德規范,是讓受到教化的人的行為成為普遍規范的具性,使人的心靈具有普遍性的性質,能感受到人情的適中之處,不再污漫、爭奪、貪利,而是變得寬廣、舒展、理智起來。禮儀規范的作用就是把人們的心靈情感引入正常軌道,確認價值,獲得對禮儀的體認,使人們知孝敬慈愛之情,辭讓忠信之德,貴老長幼之倫,并內化于心形成仁德,表現于外形成義行,使個體在具體的境遇中表現為義之所在,行為合宜,情感適度。圣人制定禮樂緣于人情,人情是禮的根源,禮是緣情而作。荀子認為人之情莫過于生死,他說:“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楊驚注引鄭玄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禮也。”這樣,在禮與情的關系上,荀子總結說:“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荀子·禮論》)所以,荀子的禮,以人情的實際性質為基礎,并注入了一種偉大的道德情感和人文感受,從而能把人的情感表現歸融于其中,使之得到某種文飾。雖然人情不美,但是如果忽視禮之文飾,那么道德教化必然偏枯、僵死而行之不遠。因此,口、鼻、耳、目、體的的欲望必與情相對應,用以養口的有芻豢稻梁,五味調番;用以養鼻的有椒蘭芬蕊,睪芷香草;養耳的有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養體的有疏房、檻邈、越席、床弟、幾筵,生活中的種種緣飾無一不是為了賞心悅目,而合乎人情的要求。“稱情而立文”既是人性中審美的要求,也是制禮的出發點,滿足了這個要求,就便于以文來規約情,使性與情經歷外鑠教化的過程,達到情與禮的相洽和諧。
因此,荀子所謂的禮儀規范相對于德性來說,決不是一些干癟的普遍行為規則,而是要能感發人們的道德情感,使之得到提升而文明煥彩。禮儀雖然對人情有所約束,但是這種約束不是窒滅人情,而是涵而化之,文以明之,使文與情得到很好的統一,才有價值上的合理性,這就是“文情理通”,只有這樣,個體才能獲得德性。從形上來說,荀子的禮又具有普遍性實體的性質,是整個的個體,又是一般的個別,它具有諸德的普遍性特征,內涵深厚、寬廣,是個體精神的異化和觀照,以分辨為形式,以仁義為目標,個體成就恭敬、孝弟、辭讓、忠信之德就是分享了禮的普遍性的精神而異化為自身的德性品質。“先王之道,仁義之隆也,比中而行之”(《荀子·儒效》),禮實行起來中正恰當,是仁義的經緯蹊徑,仁義作為一種抽象原則是虛而不見,禮作為規則則是實而可操,仁義貫穿于禮之中,依禮中而行就是對仁義的踐履。禮是獨立于性情之外的禮之理,具有道德理性的知性特征,這種知性不是脫離情感欲望的抽象理智,它的智能正好就表現在把可教化的本能情感和欲求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一種可塑的、發展的普遍性的整體,故荀子謂:“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荀子·正名》)
可見,由于持性趨惡論,荀子必然明確地走向道德規范主義。他身處一個即將結束諸侯分立國家一統的時代,處理各種利益沖突需要一個普遍準則。他認為禮起源于對利益沖突進行處理所作的倫理秩序的構建,以合乎禮義的時中狀態分別確立個體在社會中的地位、身份、享受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從而有利于維護等級尊卑的社會秩序,因此,不是心性的血緣情感仁愛而是知性的自然情感的禮義成為荀子的理論關切。而禮儀為圣人所制,禮儀系統對普通人來說有著優先性和外在性,它是教化大眾唯一可操持的工具。從性惡論出發,的確突現了圣王教化的必要性,并從教化施與者的角度確立圣王所制系統的絕對權威。
二、時變:德性教化境遇的價值認同
“時”就是要“與時俱進”,荀子德性教化思想既固禮守中,亦重權應時。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這是孔子所說的學者漸進之次第,其中權是最高層次。《淮南子·汜論訓》也引孔子此言,高誘注曰:“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丑反善,合于宜適。”
春秋戰國時期禮學的重要發展之一就在于“變禮”的出現,禮學從思想到儀式都主張隨時而變,這樣就增加了禮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制禮有變禮,因時而動,隨時而變是制禮的一條重要原則。“禮,時為大。”(《禮記·禮器》)《周易》中明確提出“時”這個概念有多處。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時是人們行動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坤·文言》說:“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豫·彖》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圣人以順動,則刑罰輕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艮,彖》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的觀念貫穿于整部《周易》,其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是:待時而動,順時而行;要時止則止,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人們要依據不同的時境進行修業,這是古人對自然和社會人事規律進行抽象概括總結的智慧結晶。孔子也很重視“時”,“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因此孟子說孔子“圣人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中庸》則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治亂持危,朝聘以時”,“時措之宜”,這說明《中庸》也主張隨時而變。后來孟子吸取了遠古以來月令系統的思想,主張依時而作:“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孟子·梁惠王上》)《禮記·禮器》明確提出:“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也。”道家也講時,如老子說:“動善時。”(《老子·第八章》)就是指的要依好的時機而行動,莊子說:“安時而處順。”(《莊子·養生主》)就是指安于時境,順應自然。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先秦儒道思想中,時的觀念是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根本方法。人們隨自然界時間節律的變化而進行勞作休息,因此時的觀念又引人到社會人事中被引申為“時機”、“時勢”,指人們在社會事務中行動時,要把握恰當的時機,審時度勢才能立于不敗之地。“這是一種把時間觀念納入到自然和社會變化發展的吉兇禍福的因果鏈條之中的思維方式。”這一思想為荀子所繼承吸收,成為君子處事應變的基本準則。《荀子·不荀》言: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陷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于堯舜,參于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法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應變,知當曲直故也。
這段是荀子言“時變”的具體論述,其意概指:君子推崇別人的德性,稱頌別人的美好之處,不是為了阿諛奉承;公正坦率地指出別人的過錯,不是為了誹謗挑剔;說出自己的美德,并與堯舜相比,和天地相配,不是狂妄虛夸;隨著時勢的變遷而能屈能伸,柔弱順從,不是膽小怕事;剛強勇敢堅毅,從不向人屈服,這不是驕傲兇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君子能夠依禮為原則,隨機靈活應付變化之故。由此可見,“與時屈伸”、“以義應變”是荀子的應變之道。“與時屈伸”是《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思想的延續;“以義應變”則是春秋以來禮制思想的損益。“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乎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后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春秋繁露·玉英》)。禮有經,有變,說明禮也有與時俱進的一面,完善了禮的功能,在現實生活中擴大了禮的運用范圍,因此,變禮與變法具有相同的意義。誠如劉豐指出:“春秋戰國是禮樂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時期,‘禮崩樂壞’只是相對于嚴格意義上的西周禮制而言,從總體上看,經過這次轉型以后,禮學思想,禮之義得到空前的發展,禮學發展到更加豐富、成熟的形態。”
由此,在經權關系上,荀子以義解經也是對西周禮制思想的發揮和創造。孟子以仁義并稱,義有對仁節制的意味,但孟子還沒有把義與禮完全等同;而荀子則禮義并稱,以義為內在的價值表征。他說:“義者循禮。”(《荀子·議兵》)“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荀子·強國》)其實,在荀子思想中,義有三個層面的含義:(1)是指等級差別的規定。如“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順,是天下之通義也”(《荀子·仲尼》);“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這里是講尊卑貴賤各得其所就是義;(2)是指調節社會倫理關系的原則。“義者,內節于人而外接于萬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調于民者也。”(《荀子·強國》)(3)是指各種道德的根本。他說:“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荀子·強國》)筆者認為,荀子言“以義應變”之義當取“分”意。因為在荀子的思想中,義本身即含有“禮為經”的意蘊,所謂“義者,禮也”,這是道德教化所遵循的基本規范,同時,義之分從道德哲學的角度詮釋其本意是“宜”,即適當、恰當、正當、合宜之意。也就是說,道德主體在教化過程中通過分而辨尊卑貴賤,人倫規范,而使行為合情、合理、合宜,體現了道德的意義和價值。義作為一種潛在的德性,可以成為禮的合宜的、感性的人格化身,是通過努力修養、自我教化才能達到。
因此,在道德教化中,荀子既主張“固禮守中”,“以禮為經”,又主張“與時屈伸”,“與時遷徙”,從而把禮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這里孟子以具體實例說明禮要靈活變通。不知道變通的禮“猶執一也”(《孟子·離婁上》);“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離婁上》)“在主體的道德實踐活動中,德性化為德行,規范內化為德性,總是在不同的實踐生活場景中實現的,任何行為的踐行都離不開具體的境遇中如何處置具體的道德規范。”現代境遇倫理學認為在一個具體的境遇中面對的問題有七個“什么”為何?何人?何時?何處?何事?何如?這種將具體的道德行為化約到具體的境遇中,體現實踐倫理的特點,并且弗萊徹在《境遇倫理學》一著中,以其基督教倫理學的立場,將愛的原則作為其具體境遇的最高原則,肯定了任何道德判斷都是價值判斷,從而將人自身的價值擺到了至上的地位,在具體的道德境遇中處理規范和行為的關系,這對理解荀子的教化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荀子·修身》曰: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節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節之以師友;怠慢傈棄,則熠之以禍災;遇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對于性格剛強的人,要進行柔從化導;對于潛藏深沉的人,要進行平易善良的教導;對于兇猛乖戾的人,要對其進行引導使其不越軌;對于敏捷快速的人,要對其控制而使其平和安靜。總之,人的個性特征是影響教化效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在培養和塑造以溫柔敦厚為主要特征的君子型人格時,具有中庸溫和個性的人更容易教化成功,而那些極端或偏執個性的人,接受教化就困難的多。因此,教育者應該及時了解教育對象的思想狀況,觀察其言論,考驗其行為,針對教育者的個性特征,選擇合適的教育內容和教化手段,做到因材施教。故荀子曰:“禮恭而后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后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后可與言道之致。”(《萄子·勸學》)
可見,荀予以遵禮為前提,在具體的道德境遇之中,針對不同的情況而采取合乎權時的行為,這種權時的行動是以尊重人的價值為先導;同時,在處理經權關系時,把經所依據的道作為一切行為的根本,而荀子的道就是禮道。在此禮道的規約下,在具體的歷史境遇中恰當地處理道德行為,是孟子所說的“圣之時者也”,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們應遵從穩定的道德規范以及對一定人倫之則的認可。
三、時積:德性教化意志的自我遷化
作為其對存在的追問過程中貫穿的根本方法,海德格爾以其對新的時間境域的開啟而實現的對存在的澄明啟示人們,“必須把時間擺明對存在的一切領悟及對存在的每一解釋的境遇,這意味著只有將問題置入時間境域之中加以透視,才有可能透過表象,找到認識歧異得以形成的根源,進而才能更深入的把握問題的精髓和實質,所以,只有著眼于時間才能把捉存在。”當然,“以善為追求的目標,道德或倫理并非僅僅在消極的意義上‘保持存在’,毋寧說,道德的更本質的特點,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提升或轉換,換言之,它總是要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存在為指向。”因此,在荀子的德性思想中,“時”作為到場或延異的境界既蘊含了對自然存在的理解,又凝聚著人對其自身生存價值的確認,并寄托著人的在世理想,而主體的人格、德性可以看作是主體在“時”的境遇中自我遷化的顯現,這就是“積”的道德實踐。《荀子·性惡》曰:
圣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不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為禹,則然;涂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相為明矣。
以上文字圍繞如何解釋“圣人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這一現象而展開,揭示了其“時變”理論在具體生活情景中,的確存在著道德主體選擇行為以及成圣成德的困境。亞里士多德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說:“至于說到公正還是不公正,都需要有意地來做。如若是無意的,那就不是做不公正的事,也不是公正作為,而是機遇。”公正在亞氏是作為最高的德性,即使是如此,也受到機遇的挑戰。在荀子看來,禮固然重要,但人心之一本要求人們做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荀子·修身》)因此,“圣人可積而致卻不可積”的關鍵是“可以而不可使”。王天海疏證:以猶“為”也,可以,即可為,或可以為,說見《古書虛字集釋》。使,通事。《管子·侈靡》“不擇君而使”,許維通云“使與事,古為一字”。不可使,即不可事。事者,治也,為也。故“可以而不可使”,即“可以為而不可使之為也。”在把“可以而不可使”解作“可以為而不可使之為”這一點上,拙文的意見是一致的。縱觀荀子的論說,他對可與能作了細致的分疏,還討論了可而不能的原因。依荀子,可以為而不為,乃是因為不肯為;所謂不肯為,即不愿為,也即孟子所說的“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至此可以說,荀子已經涉及道德行為中的意志或意愿或志與功的問題。人作為道德主體,其向善的意愿及行為不是被決定的,而是主體自身力量的體現,道德既屬于精神追求,也屬于一種內在的覺悟,一種訴諸主體心靈的意志,人在這一點上完全應當由自主作主宰,有權確認人有行為的能力以及向善的意愿。誠如孔子所說“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孟子的思想揭示了人的主體的自由性質,并認識到了德性自由的特征,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為仁由己的理念。德性涵養如何,主體究竟能否在道德上達到理想的境界,這不是由天命所左右的,而主要取決于主體自身的努力。為此,他譴責那種對善和道德不追求的“自暴”、“自棄”:“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孟子·離婁上》)“自暴”、“自棄”完全是主體自主選擇的結果。反之,求仁向善也完全取決于主體自身,“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離婁上》)
荀子承孔孟之意,認為在道德教化中既要守禮之經,又要行時之變,賦予道德主體在踐仁行禮中心智的充分自由,因而,成人成德的教化之功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愿不愿的問題。荀子的心是知性心,泛指主體意識,又兼指與之相關聯的德性意志品格,其本身有向善的趨向,意志的指向,“心容,其擇也無翠”(《荀子·解蔽》),心的選擇是自由的自禁、自使、自行、自止,能夠在現實的時變境遇中自斷、自決地選擇自己的道德行為。心有所可,有所不可。心之所可即心所肯定的,反之,則是心所否定的,有所可有所不可都是意志的作用。荀子認為心必須依札才能有正確的選擇,“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荀子·正名》);“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
由此觀之,“在道德教化中,荀子是志功統一論者,既重視禮儀的涵養,又注重自我的遷化,肯定道德的自覺能動性,從而達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從理論的層面看,主體的知性自覺意識使德性向德行的轉化具備了自覺向善的方向,“尚志”所造成的堅定的意志品格又為道德行為提供了內在的力量之源,志功一致從主體自身的德性出發使德行具備了自然的向度。在外在禮儀的規約下,德行出現自覺、自愿而又自然的特征,使主體在自身德性遷化的過程中,通過道德境界的不斷充實而使人格境界獲得了提升。故荀子謂“德操能定能應”,修德且持守德行,才能應萬物之變而成偉業。亞里斯多德分析了德性自愿性和選擇性的兩個特點,在亞氏看來,“自愿和非自愿的行為決定了德性和邪惡的歸屬,只有自愿的行為才可以用德性和邪惡來判分,而非自愿的行為是被強制的或由于無知。”同時,他將主體自身的選擇能力看作是更為根本的品質,選擇是對可能的東西的選擇,是某種具體德行的選擇,“做一個善良之人還是邪惡之人,總是由我們自己。”這些言論實然體現了與荀子在道德教化中意志自由理論的相似性。
而黑格爾則在精神境界與荀子的意志自由理論相契相應。黑格爾肯定惡的歷史作用的目的,主要是肯定惡能促進善,惡是獲得善的手段,并且在和惡的斗爭中人類走向至善。“止于至善”才是惡的最終目的和人類的終極追求,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意志的絕對目的,即善,”自然意志揚棄的自由意志是善,揚棄的過程是自由的自然性、特殊性、抽象性不斷走向自由的物質性、普遍性、現實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與自然意志相對應的可能出現的惡,獲得了它的對象的定在——善,惡與善就是在自然意志的自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否定、揚棄、超越自己而實現它的外在的現實性,即從惡的自在狀態向自為狀態過度,走向自由意志善的自在自為的自由。
在德性教化領域,意志是自己決定自己,是自由,它的對象就是它自身,是某種“內在的東西”,也就是說道德意志把人格作為它的對象,所以道德意志使人成為主體性,成為能動的獨立自主的道德主體。對于黑格爾道德意志主體的自由論,荀子則從另一角度進行詮釋,體現了中西哲學倫理精神的相容、共通的一面。荀子提出“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把人從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序四時,裁萬物”,道德主體在面對復雜的倫理境遇或性命兩難時,雖然個體常常無法支配生活的一切遭遇,但是,主體可通過道德修養而做到道德高尚,并且在自我價值的實現、個體人格的提升上,主體卻擁有外界無法左右的自主性、能動性:“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荀子·天論》)在此,荀子實際上肯定了在道德領域,主體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存在,在荀子看來,主體意識的基本特點在于能夠自由的思維和選擇;人的形體固然可以被強制,但其意志的自由選擇卻是外力無法改變的,一般而論,道德行為的前提即是意志自由,如果主體缺乏自主選擇能力或因外界強制而不能作出自己的決定,那么對其行為很難作出善惡區分,就此而言,道德自由首先表現為意志自由,荀子以自禁自使為主體意識的主要特征,顯然有見于此。可見,無論是黑格爾或是荀子,都強調道德領域道德意志的主體自由,并把它作為自己人格上的沉淀,由自己進行道德選擇、善惡區分,而自由是道德意志的本質,自由只有作為主體,才是現實的、具體的、實踐的。
但黑格爾和荀子的自由理論又有所區別,黑格爾是在善惡概念的辯證和精神的發展中去把握主體的道德意志自由,道德意志是自己決定自己,因而是不受限制的,這種無限性不單純是潛在的,而且進而達到了自覺的階段,它是自身內部的普遍性環節和特殊性環節的對立統一,是“在自身中的反思”和“自為地存在的統一性”。“而荀子的自由更多的表現在處理天人關系上對自然神秘性的認識和對天命的節制,既強調了人的化性起偽的主觀能動性的‘制天命而用之’,又強調了遵循自然規律的‘聘能而化之’,實際上肯定了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主體便逐漸實現了自身的自由。”這種自由,已不再是黑格爾所指的個體的精神上的道德意志自由,而是在本質上展開為人類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的不斷進取的征服自然的歷史過程。
責任編輯: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