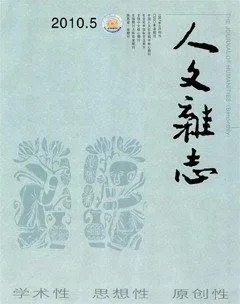“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雕塑發展
內容提要“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雕塑發展,既要繼承傳統,審視和重釋傳統,又要破除“西方中心論”從東西方各民族的雕塑文化中汲取人性健康的養料,既不失去和世界接軌的機會,又堅持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是后殖民時代的我們在“全球化”和本土化艱難悖反中的當務之急。本文從四個方面展開議題:1.重審中國傳統的雕塑精神:天人和諧的圓舞與柔韌不息的智慧。2.重審中國古代人物雕塑之憾:主體人之缺失。3.重看西方雕塑中注重人本體之光榮傳統。4.近觀東方雕塑(重點談印度雕塑文化)給我們的啟示。
關鍵詞 “全球化” 后殖民時代 中國雕塑傳統 西方雕塑傳統 東方雕塑一印度雕塑
[中圖分類號]J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0)05-0105-07
“全球化”問題是當代世界的焦點話題。它不僅僅只是知識界學者討論不休的關鍵詞,而且日漸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凸顯內容。“全球化”是危險,更是挑戰和機遇。積極的態度是:“全球化”之于我們絕不該是被動的適應、裹挾與拖曳,而應充滿了理性的思考與主動的選擇。相比半個多世紀乃至一個世紀前被西方帝國主義進行軍事、政治侵略的殖民時代,我們今日所處的“全球一體化”時代(“西方中心論者”以他們的經濟優勢霸權進而對第三世界進行文化心態、價值觀念的滲透與控制),是我們所面臨的后殖民時代,也就是文化帝國主義時代。這是一場沒有硝煙戰火的殖民。我們諸多的不警惕使民族傳統文化面臨著失語變種的危險,而一些西方文化優越霸權者卻在極力掩蓋他們的強權目的,諸如英國湯林森在其《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就一味突出“全球化”的文化宿命而否定“民族性”,甚至認為“國家民族是想象出來的社群。”其優越霸權的“全球化”乃“西方化”的固執昭昭可見。因此如何在現代性的進程中,在和世界接軌的路途上既不失去“全球化”的機會又堅持民族文化身份,既借鑒外邦又保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傳統就成為我們在后殖民時代,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艱難悖反中的當務之急。“全球化”不意味著文化的一體化,“文化的多樣性成為全球文化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
堅持民族文化身份,首先是要注重傳統,繼承傳統,發揚傳統。但是繼承傳統不是泥古不化,不是全盤沿襲,搞民粹主義,而是要取其精華。剔除糟粕。也就是說既要看到傳統的高妙精粹處,也要看到傳統的不足與鄙陋處。于是面對傳統我們就有審視和重釋的任務,這就要看看我們已具幾千年的文化哪些已經變成死的東西,需要堅決拋棄之;哪些變成了文明的碎片需要拾掇整合起來;哪些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需要我們大加弘揚,闡發它們不僅滋養著中國,且對世界文化都將補益非凡的意義。于是我們審視檢省的眼光就極其重要且迫切。在此我們需要體會當代后殖民理論家賽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周蕾等尖銳指出的“景象”:在“西方話語中心者”看來,東方的貧弱(“東方情調”)是西方強大優勢的一個驗證,在他們看來充滿了原始神秘的“東方舞臺深處蘊藏著一組異kBnL12weX8ClWw/pMaqwJ5dcf9/G7NaHnwsPGx338yM=常龐大的文化上的‘保留節目’。”這種“想象性”的豐富而扭曲的“東方”在西方人眼里就淪為“被看”的“他者”形象(如張藝謀電影中的“小腳”、“煙槍”、“紅燈籠”與“黃金甲”)。于是我們審視傳統的同時也就要重新來看西方。現代性的歷程不是西方化的歷程,全球化的歷程同樣不是,所以我們的今天就不僅僅只是要在中西碰撞中找出路(雖然注重中西碰撞——比較——學習是極其重要的環節,西方世界率先進行了現代性革命,給全世界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現代化經驗)。但中西碰撞的提法走到極端勢必就是從我們自身的角度強化了以西方經驗為藍本的“西方中心論”——“歐洲中心論”。也就是說,我們重看西方(或者看重西方),都不意味著在對抗中跟著西方人跑,更不能以西人的眼光做評判,那樣中國當代藝術就會淪為西方當代藝術的“中國卷”。因此我們要堅持的是在“全球化”視野中,破除“西方中心論”,從東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中汲取養料。基于人性健康的超越于東西方文化弊端的審美標準,才是全人類共享的價值尊嚴。
對于此大話題中的中國雕塑發展,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1.重審中國傳統的雕塑精神:天人合一的圓舞與柔韌不息的智慧
中國傳統雕塑是中國文化乃至中國哲學(宇宙世界觀)的最好表達。中國人最根本的宇宙觀是儒道同出的《易經》中所說的“一陰一陽之為道”,動靜相宜,虛實相生,是“靜而于陰同德,動而于陽同波”充滿了合規律的節奏與韻律的天人相諧(心物合一)的時空統一體。于是不同于西方雕塑講究的團塊手法,曲線與圓是中國古代雕塑的典型特征。曲線在典雅沉雄、渾摯穆雍的商周青銅器的雕刻中有著突出體現。除了用饕餮紋、回紋、鳥紋外,商周鐘鼎彝器的花紋圖案中,還雕刻著完整的飛動跳躍、婉轉流麗、琦瑋詭譎的蟲魚走獸、虎豹龍蛇,“每一個動物形象是一組飛動線紋之節奏的交織,而融合在全幅花紋的交響曲中。它們個個生動,而個個抽象化,不雕琢凹凸立體的形似,而注重飛動姿態之節奏和韻律的表現”,這些神武鷹揚、混沌矯健的“龍飛鳳舞”既體現了先民未曾從自然混沌中分離出來的雕塑體量意識,也體現了中國古代雕塑以線之起伏波蕩象征中國人宇宙生命律動之美學特征。
如果說古希臘的雕塑是西方藝術的最高體現之一而成為后世西方畫家之范本的話,那么中國古典雕塑卻相反而極具畫風(寫意性)。尤其晉唐以后雕塑受畫境影響極大,塑繪結合的方法成了中國古代雕塑的一個重要特點。被稱為“塑圣”的楊惠之不僅和“畫圣”吳道子同學,且和道子繪畫極為相通。因此中國雕塑和中國書畫相通為線的藝術,充滿了舞之意味。無論是戰國曾侯乙墓的《漆木梅花鹿》,還是中古以來的克孜爾石窟群、敦煌莫高窟或者云岡、龍門石窟壁畫上的各類浮雕飛天,還是唐代泥塑《天王像》,也無論是唐以后盛行的水月觀音體(紫竹觀音)還是明清泥塑《千手觀音》……他們都或飛舉靈動、或婀娜翩翩,就是那原本該是剛猛的唐代天王,雕塑家也不是用生硬方愣的線條塊面塑造出威武猙獰的王者或者武將之樣,相反天王那憨厚純樸、氣宇軒昂又略呈s形扭動的身軀線條象極了正欲“反胴”起舞的預備舞姿。如果說中國古代的人物雕塑還體現著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的端莊,眾多佛像也還表現著慈悲為懷的莊嚴(甚至顯出些許凝滯“呆滯”)的話,那么他們的生命情態就隱秘充分而遷想妙得地體現在衣飾線紋上。各類飄灑飛天自不必說,即使世俗題材諸如原位于龍門賓陽中洞,現藏美國納爾遜博物館的北魏《皇后禮佛圖》浮雕,那顧盼有情的人物個個服帶飄逸,若細柳扶風,舒緩優美如長袖起舞,其線條之美足以和吳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相媲美。
曲線的完滿狀態是圓。因此中國古代無論是動物雕像、佛像及人物雕塑都總體地體現為圓之造型。如漢代大型儀衛紀念性石雕雖體量巨大,但手法簡單,多采用“循石造型”的手法,渾圓沉雄。即使東漢《馬踏飛燕》中強調馬之三足凌空、饒騰萬里的飛奔動勢亦不忘卻馬之渾圓的體態美。
圓之狀態是中國哲學“天人合一”,即人與宇宙相諧和的親切體己的家園般的深切回歸。這是因為中國人對始基的追問沒有在西哲“形上”(神)與“形下”(科學)兩個向度上深究發展,而是追問、彌綸、玄虛在形上形下之間,充滿了柔韌不息圓之回環的綿綿智慧。
如果說現代的西方人在主客二分、空間外求、邏輯與秩序的對象化思維方式即在“人類中心主義”的霸權中飽受惡果、“無家可歸”的時候(患了“實癥”之病),中國天人相諧、虛實相間的高妙哲學就是他們陶洗心靈、去除霸氣驕奢的一劑解執良藥,從而使建立在這樣哲學基礎上的中國文化當然包括中國雕塑文化就對他們具有著永恒的魅力,也對今天的我們同樣生效。
于是我們才能理解現代西方美術大師一雕塑大師譬如馬約爾、布德爾、布朗庫西、巴拉赫、亨利·摩爾、阿爾希平克、畢加索、馬蒂斯、米洛們對東方藝術資源的汲取和借鑒。這些雕塑家與同時代的藝術家們一樣,他們所遭遇的時代是機器文明高度發達卻也是以分裂的心靈、異化的人生和對世界大戰的恐懼為代價的時代,是對歷史理性有著普遍懷疑、道德至上發生深刻動搖的非理性時代,是斯賓格勒所說的“西方沒落”的時代,是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的時代,是海德格爾所言“存在被遺忘”的時代,也是西美爾、列奧·斯特勞斯、法蘭克福學派、雅斯貝爾斯、哈貝馬斯等現代哲學家懷疑啟蒙理性的合法性的時代,這是“現代性”悖論叢生的時代。這種懷疑批判性使他們在藝術手法上不約而同地在努力擺脫模仿現實的西方寫實性、團塊性、直線性傳統,不約而同地表現性、抽象性、簡約性、曲線性(圓)起來,這是現代西方哲人和藝術家發現看重東方文化的時代。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進一步理解后現代藝術思潮—后現代雕塑中諸如極少主義、激浪派藝術、大地藝術、物派藝術等對西方傳統價值的解構及其對東方藝術的特別看重。其中日本的物派藝術是“全球化”行進中亞洲藝術出現的一個重要運動。這一流派的出現昭告了東方藝術不僅被西方人看好,也被東方人自己所珍視。物派藝術是對于明治時代以來介紹到東方的西方藝術的懷疑,他們大量使用現成品或者自然界中的物體,充分轉換了東方的自然觀和園林藝術,他們希望恢復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那種真實人生感悟體驗的關系樣態。物派藝術實際上是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和東方禪學方式的結合,試圖為現代社會的藝術注入東方色彩。這是東方文化(以中國文化為母體)給世界貢獻的極富家園意識的美學生態活力之一種表現。
2.重審中國古代人物雕塑之憾:主體人之缺失
如果說中國天人和諧宇宙觀的空靈性(“道”無體無形,惚兮恍兮)決定了中國古代藝術家不愿滯于物而求虛靈傳神之趣以“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話,“滯于物與象”的雕塑在古代中國看似遠不及古希臘發達就不難理解了。同時要看到的是,像一枚錢幣的兩面,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除了有圓舞一般的家園意識與柔韌不息的綿綿智慧之外,還有著封閉環抱退守現世。不具超越意識,“人沒于天”的負面效應。于是,和西方雕塑史上人始終是主體不同,中國古代雕塑多動物像、佛像,卻鮮見紀念性人物雕像。想必這與中國人以“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從而自古視雕刻為“小技”密切相關。中國古代雕塑者地位極為低下,被視為“百工”、“匠人”。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卻鮮見雕塑家的記載,雕塑史論則幾近于空白。帝王愿留畫像卻不屑于用雕塑留影,“士”執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T268evEyNrDjPTHpV6eWPQKj2iOnoUuH+bMoiyJQNQk=以期名垂千古,閑暇失意可寄情于書畫琴棋,卻側目以雕刻小技,更不屑用此小技為自己塑像。于是浩浩幾千年的雕塑歷史少有帝王百官也幾乎沒有文人雅士的塑影留存,當然也少有以正劇的形式為普通勞動者塑像,秦始皇兵馬俑的人物塑像雖萬馬千軍,氣勢雄壯,但作為陪葬作為被驅使的人,其呆滯僵化之體態面貌也就必然地缺失了作為人之主體的創造性活力。
當然,中國古代雕塑也有人物像,但終究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間藝人(說唱藝人、戲俑、舞俑、樂伎、雜劇人物),仕女、媒婆、太監、俳優、相撲、樵夫、武夫之類(王者王建、士李陽冰像是極少的特例),這在世界雕塑史上都是一個特殊的現象。面對這一現象,與其說是主體性的人成為了退守狀態,不如說被塑者成了“被看”把玩的對象。這種病態塑風想必同文人士大夫“寒梅瘦影”的病態文風一畫風以及同纏足—纖弓為妙的病態舞風一樣都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糟粕。這種培養著獻媚圖寵的奴隸人格和俳優習氣的自輕自賤,正是“西方中心論者”為了驗證他們的強大優勢所想要看的豐富而扭曲的東方。
于是當代中國雕塑的發展必須擯棄糟粕,繼承真正優秀的傳統精髓,同時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汲取人性健康的外民族的營養。古代人的缺憾恰為現代人提供了演練的平臺。“五四”以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雕塑家們(著名的如劉開渠、滑田友、李金發、滕白也、王朝聞、王臨乙、周輕鼎、傅天仇、潘鶴等)向西方學習、向蘇俄學習,中西融合、中西交匯,創造了大量類別多樣的人物雕像(以及其它題材的雕塑作品)。雕塑的主體人物一躍而為領袖、英雄、戰士和陽剛健朗的勞動民眾……這里雖然有著由西方的啟蒙運動而來更由我們自身為民族民主的救亡任務與激情理想而來的“宏大敘事”所帶來的藝術為政治服務、個體擔當全人類使命而無真正個體存在走向了“假、大、空”之類的負面性效果,但是這一輩雕塑家們的努力卻開天辟地使中國的雕塑史尤其是人物雕塑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當代的雕塑家們更是各顯神通,在痛定思痛“宏大敘事”(“文革”藝術以及上推前17年的藝術)之弊病后,當代雕塑家們(著名的有錢邵武、曹春生、曾成鋼、吳為山、隋建國、陳云崗、殷曉峰、張偉、瞿廣慈、李向群、洪濤、袁源、張琨等)塑造了眾多紀念性人物雕像,為文化精英塑像,為普通人塑像,為雕塑者自己塑像,充分彰顯了被“宏大敘事”(體制性訴求的“烏托邦”式理想)淹沒壓抑了的個體人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此基礎上,當代的雕塑家們也重新本真地來體察民族、集體、曾經的革命這樣的大話題。塑一己的愛恨情懷當然是還人性本然的一個途徑,但不流于虛妄的民族國家的使命擔當,更是人文知識分子(雕塑家是其中一種)的社會良心之體現。但新的時代有新時代的問題與困惑,譬如市場化而來的焦慮浮躁與草率創作,后工業化一后現代化而來的在雕塑界也長期存在的戲謔、解構,潑皮、玩世、平面化的虛無主義現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都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在現代社會日益需要增長的公民意識面前的攔路虎。于是人性的高貴尊嚴,終極價值的意識與擔當,都是當代雕塑人需要深刻認識的。于是西方雕塑中以人為本的光榮傳統就需要我們格外關注。
3.重看西方雕塑中注重人之光榮傳統
西人持有現象本體二分卻又期望神人合一的世界觀。西哲由此發展出了兩條思路。當他們把世界起源的始基元素當作實體研究并尋找它們之間的聯系即結構安排時,發展出了形下科學,并發展了“和諧、數量、秩序”的美學觀念;當他們認為一切是上帝所造的時候,則發展了形上神學一思辨哲學。前者造就了崇尚秩序、理性、靜穆的雕塑之美,后者成就了“道成肉身”的基督教神學色彩的雕塑風格。前者的美可以古希臘、羅馬雕塑為范本并經文藝復興發揚光大。后者則由“道成肉身”的觀念打破了希伯來宗教中“不可制作偶像”的絕對戒律,創立了一整套基督教的圖像志和象征主義,不僅創造了中世紀的雕塑作品,也同樣成為文藝復興及啟蒙時代的雕塑不可或缺的內容。
顯然,文藝復興是這兩條路向的連接和關節點。一方面,人在新時代頌揚自己“人文主義思想”的時候復活再生了古希臘、羅馬的美之法則;另一方面,在打破人是上帝的奴仆這類中世紀禁錮的同時,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們卻并沒有去掉理性、神性(本體)超越的一維,他們革除的是教皇,卻沒有革掉作為信仰的心中上帝(這也是以后啟蒙主義者所堅持的信條)。因此,政教分離后的新教倫理、人性啟蒙及內在不缺的價值評判標準的神性維度都深遠影響了西方的近現代史,包括西方近現代的雕塑史。于是文藝復興及啟蒙時代的雕塑作品當然地令我們深刻回想起古希臘、羅馬偉大而美麗的雕塑榮光:無論是古希臘那些陽剛偉岸的男性裸體,還是美侖美奐如春天般氣息的女神雕像都是明顯范例性的。尤其那一系列直立男性裸體“不僅代表著體育競技的高超技能,而且代表著戰爭的獻身精神和公民品行、道德的整一性,性感的合意性,個人的拯救以及不朽性。在這些軀體中,銘刻著事件,灌注著精神,流露著欲望,承載著神性。”這就是希臘美術中“英雄般裸體”的傳統。
這種人之尊嚴的光榮傳統不僅僅為古希臘藝術所有,也為西方其后各個時代(除中世紀)所有,它是貫穿西方文化一西方雕塑的主題和紅線。無論是米開朗基羅手拿投石袋準備和敵人決一死戰的《大衛》、還是率領六十萬猶太人為擺脫法老的殘酷統治,從埃及出走,尋求自由的《摩西》;還是羅丹那“拿破侖用劍做不到的,我的筆要能做到”的《巴爾扎克》、還是凝重沉思而深邃智慧的《思想者》,高歌猛進、意氣風發的呂德的《馬賽曲》……都是這一傳統的杰出代表作。這種人之尊嚴的光榮傳統,這種獻身精神、公民品行、道德承擔、美學崇高的風范都是當下的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里,在公民意識的建設中需要深刻汲取的營養。
當然這種傳統不能無限制地膨脹式發展,這一傳統是西人本體、現象二分,在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也改造人自身的對象化思路中,人勇往直前所展現的崇高美。但是人如果以無限度地征服攫取的強力姿態向世界進發,又會失去神性敬畏,破壞世界的整一性,同時戕害人自身。于是陽光偉岸的光榮裸體就會淪為西方現代雕塑家賈科梅蒂手下那如線一樣拉長如燒焦抽縮了一般無奈迷茫又如干裂秋風狀瘦骨嶙峋的干枯人物。失去神性也就意味著人成了被放逐而迷失人性家園的孤獨者。這是西方現代藝術一現代雕塑所真切表達的中心議題。
因此西方雕塑中人之尊嚴的光榮傳統需要和中國哲學的天人和諧、家園意識以及儒家人世的“士之擔當”、道禪“出世”式澄澈飄逸之思想相互參照補充(這當然不是硬性嫁接,而是需要充分融合,現代轉換)。只有基于人性健康的褒有各種文化精髓而超越于他們各自文化弊端的審美標準,才應是“全球化”視野中人類共享的價值尊嚴。
4.近觀東方雕塑一尤其是印度雕塑給我們的啟示
如前述,“全球化”的歷程不是文化一體化的歷程,也就不僅僅只是中西碰撞(而跟著西方人跑)的事情。中西之外還有亞洲、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東方國家我們以前多注意了日本,現在東亞其他國家,以及東南亞、南亞、西亞各國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尤其是南亞的印度,這個與中國齊名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雄強國度是絕不容忽視的。印度的國徽,是阿育王時代的著名雕塑《薩爾納特獅子柱頭》,四只背靠背蹲踞、向四方張口怒吼的連體雄獅,巨大雄偉,威猛雄厚,常任俠先生對這個雕像的解釋是“東方雄獅作大力吼”。
印度佛教美術與中國佛像雕塑、繪畫傳統與之淵源關系是中外美術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千余年前,佛教東土而來,佛教宣傳最為普及而易懂的手段就是佛教繪畫和佛教雕塑,這是在東晉十六國時期迅速發展起來的。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有陸路和海路兩條線路,印度來華僧人走海路較少,多走陸路。沿著陸路,開鑿石窟塑繪宣傳佛教,頂禮膜拜者不絕如縷,克孜爾石窟(新疆)、炳靈寺石窟(甘肅)、敦煌石窟(甘肅)、麥積山石窟(甘肅)、云岡石窟(山西)、龍門石窟(河南)等,就留下了豐富的佛教藝術的遺存。這些建筑、雕塑和壁畫成為人們供奉與膜拜的對象,是當時各階層民眾都能夠接觸到的群眾性畫廊和藝術博物館。特別是敦煌莫高窟,成為我們了解中國佛教藝術的“百科全書”。也是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交流的見證。
除了佛教,印度本土還曾興起印度教和耆那教,也曾受過波斯、希臘、羅馬、穆斯林文化的深刻影響,但印度文化卻始終保持著印度本土傳統精神的延續性和統一性(呈現為多樣統一)。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中國佛教影響巨大的印度笈多時代,既是佛教鼎盛的時代,也是印度教日益昌盛的時代。印度藝術就異常復雜卻又鮮活無比。印度教不僅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密教的某些教義,而且更吸收了吠陀雅利安人的自然崇拜文化,還特別吸收了印度土著達羅毗荼人的生殖崇拜文化。于是佛教崇尚祝思內省,安寧靜穆;印度教卻崇尚蓬勃旺盛的既具創造精神也富破壞性的生命活力。于是包羅萬象的印度文化就具有了特別的矛盾性:既虔信宗教又眷戀世俗,既追求解脫又執著人生,既崇仰精神又沉迷肉體,既樂生又苦行,既禁欲又縱欲,最抽象的形而上學往往以最具體的自然主義形式來象征……
這是印度美術的靈魂、信仰與生命活力之所在。這對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弊端有著特別的意義。在佛教初來之際,對于儒道,佛教多采取迎合而調和的態度,儒道則在思想過濾、清理、改鑄、揚棄與吸收中與佛抗衡。譬如在印度笈多雕刻的兩大樣式中,中國人取馬圖拉樣式的“濕衣佛像”而不取薩爾納特樣式的“裸體佛像”,中國佛畫一浮雕把印度佛教中妖嬈、嫵媚、豐乳肥臀、感性肉欲的裸體藥叉女變成了敦煌壁畫—浮雕中端莊飄逸而典雅著裝的飛天伎樂天,即使同一題材同一題目構圖也相仿的畫中魔女,印度的魔女全裸或半裸,誘惑太子,極盡艷情之態(譬如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窟壁畫《降魔圖》),而中國的魔女卻全都裝上了衣服,斯文了許多(譬如敦煌石窟254窟《降魔女》),想必就是儒家“禮”與“仁”之倫理思想和“文質彬彬”之美學理想,以及道家“心齋”、“坐忘”對佛教繪畫、雕塑過濾乃至融合之表現。
儒道思想有著特別的智慧與優長被全世界人民所喜愛,但儒道思想也有著特別的局限甚至弊端性阻礙抑制著人性—個性的健康發展,從而延緩著中國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大踏步前進,于是,那洋溢著鮮活生命力與創造力的印度文化——印度雕塑對我們就是一道亮麗啟示的風景線。無論是印度雕刻中那渾樸天真卻豐乳肥臀,活潑搖曳,浪漫多姿,風情萬種,畢顯性之活力與青春熱情的生殖精靈代表的“藥叉女”系列,還是維護宇宙秩序作為保護之神卻率性野性、昂首向天,雄姿勃發,充滿了威猛陽剛,也充滿了渾樸天真的“毗濕奴”系列,也無論是既能跳輕柔軟舞又能跳狂放健舞而以雷霆萬鈞之力感天震地的濕婆系列,也無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赤裸裸的性愛雕刻“卡朱拉霍式雕刻”大大方方地展現在陽光下……都與儒家“發乎情,止乎禮”之思想,也與道家“望峰息心,窺谷忘返”的后退哲學形成了鮮明對照,這些健康美麗的印度雕刻對于中國文化一中國雕塑來說是極為寶貴重要的后備資源之一。
一千多年前,作為東方民族,中華文明曾經和印度文明攜手共進,兩個泱泱文明古國相互滋養,共同為世界創造一養護輝煌燦爛的東方文化做出了自己莫大的貢獻,今天我們又都走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同情遭遇現代性進程中的諸多尷尬,因此更加需要互相關注。不僅對印度文明如此,對亞洲各國文化我們都應給予極大的關注和友好交流。這應該是在后殖民時代,東方人聯合起來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抵抗”,這是東方文化的真正聲音。在當代語境中,我們所說的抵抗和船堅利炮的殖民時代的抵抗含義不同,準確地說,我們今天的“抵抗”指的是提倡東西方之間的真正平等對話和交流,那么誰代表東方,誰代表中國自己的聲音在世界上發聲,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似乎代表東方發言的當代后殖民理論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籍的亞洲人:愛德華·賽義德,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佳婭特麗·C·斯皮瓦克,生于加爾各答的印度人。霍米·巴巴,是在印度成長起來的波斯人后裔。周蕾則是美籍中國人……他們因為第三世界血緣在西方世界處于邊緣地位,因此能深切感受并揭露文化帝國主義的霸權與西方中心論,并進而想為臣屬的文化重新“命名”。但作為“夾縫人”,他們一方面想融入西方卻又處于劣勢的邊緣與無根的漂流狀態,但對東方他們又有著西方人的優越感。事實上,他們在批判殖民文化的同時卻不幸地自身也被殖民化了。他們和許多一去不回的文化“香蕉人”一樣并不能真正代表東方發言。因此讓東方發聲而不成其為驗證西方強大霸權的“他者”形象以倡導東西方真正對話的東方代表不應該是他們,而應是真正東方本土的聲音。這些聲音才能使東方各民族的文化成為世界多元文化并存中之重要存在,中國文化亦是這多元之中的重要一維。
責任編輯: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