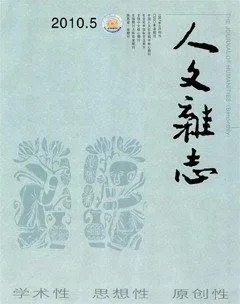宋朝開國史與士人的記憶及改造
內容提要 更真實的宋朝開國史,與宋代文獻記載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距離,其中北宋中葉以來士人描述的“崇文”氣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宋太祖雖然采取了許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轉以往長期失衡的文武關系,以穩定秩序,卻并未造就具有時代特征的“崇文”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開始落實的“崇文抑武”治國方略,到北宋中葉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氣象。由此直至南宋,主流的士人群體在追憶本朝開國史時,有意識地描述并改造了當時的政治狀態,賦予一種“崇文”的氣象。其實,這一現象乃是當時價值評判下選擇歷史記憶的結果,并得到國家的認同。
關鍵詞 宋朝開國史 崇文 世人 記憶 改造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0)05-0135-05
中國歷史進入宋代,在諸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從文明及文化的角度而言,更創造了異常燦爛的一面。如現代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的評價。但這種歷史變遷,絕非宋朝開國就立竿見影,而是在延續與轉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不過,在一些宋人的筆下,似乎本朝自誕生后就斬斷了過去,顯現出全新的面貌,其中后世看到的宋朝突出的“崇文”氣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一
人類的歷史記載,從來都是在后世不斷追述與放大的過程中延續的,尤其是本時代人眼中的歷史更是如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些士人的筆墨來看,宋朝的開國歲月就覆蓋了許多富有情感而不免夸張的色彩。
趙匡胤結束武夫長期亂政世道,開創了三百多年的基業,尤其是宋朝以后很長時期內呈現出高度的“崇文”氣象,因此在本朝士人心中必然籠罩著神圣的光環。那末在宋太祖開國時期,是否完全采取了有關舉措并形成了“崇文”的氣象呢?
更符合歷史真相的是,宋太祖在位期間,采取的有關舉措及其成效包括:
首先,通過一系列收兵權、削藩鎮舉措,結束了以往的武人政治,為恢復文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地位創造了條件;
其二,在中樞機關逐步恢復文臣應有的角色。在宋太祖朝,除保留前朝宰相范質、王溥及魏仁溥外,先后任用趙普、薛居正、沈義倫、呂余慶及盧多遜等人為宰執,恢復其行政權力,同時防范樞密使對行政的干預,其中親信趙普更深受信任,“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
其三,陸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行政。宋太祖稱帝后,不斷從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方任職,逐漸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部將,“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闞代為守臣”;
其四,注意保護文臣,免遭武夫加害。如:建國之始,悍將王彥升以索酒為名敲詐宰相王溥。宋太祖立即將這位功臣干將逐出京師又如:武將德州刺史郭貴被調離本地,國子監丞梁夢升接任知德州后,對郭氏族人的違法牟利活動予以懲治。郭貴便通過宋太祖親信武官史硅告狀:“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但趙匡胤不僅沒有治梁夢升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繼續令其留任;
其五,恢復儒學的地位。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圣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贊文,并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孔廟。建隆三年(962),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糾正了以往孔廟失去祀禮和不受重視的狀況;
其六,開始重視科舉制度。在宋太祖朝,不僅重視科舉取士的制度,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制度,錄取人數較以往有所擴大。
最后,鼓勵官員讀書。據記載,“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若)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史”。宋太祖還公開要求武臣學習儒經,所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揆諸上述舉措,不難發現的確有崇文的內容,但若描述成具有時代特征的氣象,則顯然失之于夸張。事實上,這些舉措的實質仍在于一方面調整以往嚴重失衡的文武關系,力圖使文官武將隊伍回歸各自正常的位置;另一方面,則在落實“可以馬上打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政治規則,以盡快結束戰亂,確保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統治。因此,其所采取措施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將過低的文臣地位提升,以制衡超強的武臣勢力,同時提倡儒學中的君臣大義和綱常思想。如元人評說:“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當然,要說有所不同的話,則主要在于迅速瓦解了軍功集團,使得這一傳統影響王朝前期政治的勢力消失,為科舉官僚隊伍的發展清除了障礙,并與以后“崇文”氣象的產生存在一定的關聯。
必須指出的是,趙匡胤畢竟脫胎于五代,出身行伍,又處于統一四方之時,故無論是感情上還是現實中都不可能蔑視武將和軍隊,收奪將帥兵權并不意味著貶低其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做到以儒立國。現存《宋會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記述了趙宋王朝“崇文”的無數事例,但涉及到宋太祖朝的具體內容卻非常有限。
有諸多事實表明,宋初將帥即使遇事無理,也常受到天子的偏袒。典型例證如:大將慕容延釗平荊湖期間,縱容部將搶掠,擔負監軍職責的樞密副使李處耘予以懲治。慕容氏控訴于太祖,結果貴為樞密副使的李處耘被貶官至死。又如:開寶四年(971),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坐與兵馬部署何繼筠不協,為所構,太祖惡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這種情形到以后的統治時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宋人還記載:“舊制,每命將帥出征,還,勞宴于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為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由此細節可見,宋太祖并非一味親近文士。因此,武將經濟待遇普遍高于文臣,節度使俸祿更優于宰相。如朱熹所說:“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
還值得一提的是,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詔修建代表武人精神的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如時人所云:“締創武祠,蓋所以勸激武臣。”并多次幸臨武成王廟,其中在乾德元年(963),就先后三次率臣下親臨武成王廟。其次數超過了文廟。
宋太祖經歷了五代亂世,切身感受最深的是武夫擁兵對皇權的威脅,而對文臣士人則并不擔憂。趙匡胤就直率地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還有這樣的記載:開寶六年(973),吳越王向宰相趙普私賄黃金,恰被太祖碰見,“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由此可見,宋太祖對書生也不免心存輕視。
因此,在宋太祖朝,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尚未成為執掌朝政的核心力量。就當時的宰執大臣構成來看,宰相共六人,其中短暫保留的前朝遺老三人,兩人有科舉背景;本朝提拔者三人,只有一人屬科舉出身。樞密使共有四人,其中三人為武官,其余皆非科舉出身者;參知政事和樞密副使共九人,科舉出身者僅有三人。由此可見其統治核心的主體并非科舉出身文臣。故而。有宋人指出:“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還是朱熹評說的符合實情:“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
二
宋朝“崇文”路線發展的軌跡,應大致始于第二代的宋太宗朝后期。自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后,宋朝不再走傳統的漢唐發展之路,出于極端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守內虛外”,統治重心轉向內部建設。為防范武將勢力對皇權的威脅,加大了對其壓制和鉗制的力度。清人王船山針對宋太宗朝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同時,進一步重用文臣力量,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的地位遂不斷獲得提升。
宋太宗在位期間,從事的崇文活動明顯增多,如率領群臣三謁文宣王廟,以示對儒學的尊重,而對武成王廟僅光顧過一次;宋太宗即位初便親自操持科考,錄取五百多人,不僅人數大大超過以往,又超等任官,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這就清楚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傾向與決心。此后,科舉得到空前發展,大批舉子進人官僚隊伍。宋太宗后期,王禹僻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以至于科舉出身的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主張;宋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態度。此外,宋太宗還率先垂范,“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甚至苦練翰墨,并為臣下饋贈御筆字幅。因此贏得了文臣的好感。李防有“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表達了士大夫對當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時代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得到發展,并基本確立其在國家政治各個層面中的重要地位。應當承認,宋太宗朝后期是“崇文”氣象開始萌生的重要時期。
再歷經宋真宗朝至仁宗時代的統治,科舉出身的文臣已成為執政的主體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科舉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可以說,至北宋中葉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國的局面,幾乎當時各方面的重要職責皆由文官承擔,如時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于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甚至在中央軍事機要決策的樞密院和在外軍事統軍體系中,文臣也逐漸成為主宰者。至此,朝政發展的方向確已鞏固于文治路線,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氣象。
如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在幸國子監時對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滿意,并稱:“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宋人曹彥約對此評說道:“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于景德二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訓已及此,則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影響所至,官場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時的一道詔書曰:“頃者嘗詔方州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故范祖禹認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友。”
但到北宋中葉才真正出現的“崇文”氣象,主導朝政的文官士大夫并不滿足,基于現實的需要,不僅要堅持高揚“崇文”旗幟,堅定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決心,而且從諸多方面宣揚其由來已久的精神,以至于追溯到開國時代。宋真宗在位期間遂深受這種主流意識的影響,親自撰著《崇儒術論》,公開宣稱:“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后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浸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圣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即為太祖皇帝時代渲染上崇尚斯文的色彩。
宋哲CjQfL/c/XwTwSB8Tqdl4Xg+KU0O8UjCVr6RmFt5q2wQ=宗朝,范祖禹在經筵期間,曾向皇帝進呈《帝學》一書。從《帝學》講授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士人推動儒家思想文化建設的巨大努力及成效。范祖禹說:“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主無不好學故也。”其中將本朝開國以來皇帝都描述為崇文好儒之君。如對太祖幸臨國子監并拜謁孔廟的舉動,評說道:“儒學復振,是自此始,所以啟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宋太祖鼓動臣子讀書,其目的本是要求他們遵守儒家綱常規范,但范氏進一步引申道:“太祖皇帝之時,天下未一,方務戰勝,而欲令武臣讀書,夫武臣猶使之讀書,而況于文臣其可以不學乎?”并與“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進行了強烈的對比。除他之外,還有人也認為:“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雍,真儒有光有赫。”但宋初許多右武的事實俱在,于是文臣劉安世委婉地辯解道:“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在北宋滅亡之際,宋欽宗也標榜:“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于士無負。”
南宋時,文人士大夫對開國史的追憶就更為夸張。如陳亮上書宋孝宗時言:“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于前代。”在此便宣揚宋朝“以儒立國”的開國原則,而掩飾了當時的歷史真相。朝臣周必大則稱:“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周氏將太祖朝定性為“文治興”的時代,也屬于士人有意識的過分描述。還有如吳淵所說:“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為最上’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
宋代的“崇文”氣象,實在是真宗朝至北宋中葉以后發生的事情,與其朝開國史相距甚遠。但無論是以后的宋朝帝王,還是許多朝野士人,都將此氣象追溯到宋初,則反映著歷史記憶中包含的有選擇的失憶傾向。還是王安石清醒,他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在此將“以文持之”視為真宗朝才出現的事實。歐陽修撰文回憶稱:“大宋之興,于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蘇轍參加仁宗朝制科考試時,在試卷中也承認:“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劃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遠過于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都道出了更接近史實的評說。
三
宋代士人作為時代及其變遷的記錄者,在官方編修機構中編纂了本朝歷史,使得其開國史被或多或少地描述為“崇文”氣象,宋太祖也因此獲得高度的贊美。其實這些光環,很大程度上是本朝士大夫不斷有意識選擇而不斷添加的結果。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士人在自己所寫的詩文、野史及筆記小說中,對開國史也不斷附加上自己的理解。
從宋代的有關記載來看,北宋中葉以來一部分士人對本朝開國史的追憶,尤其是描述的“崇文”氣象,其實是在包含歷史記憶的過程中,有目的選擇、并逐漸放大的產物。顯然,這體現出宋代主流士大夫自身的價值評判。其很大程度上修正記憶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疏離了真實的歷史,卻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正如研究宋朝“祖宗之法”的學者所指出:“‘祖宗之法’并非祖宗行為舉止與創制措施原原本本的反映,而是經過士大夫篩選、寄寓著士大夫理念、有賴于士大夫們整合闡發而被認定為‘祖宗之制’的。”
眾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后果。如宋太宗所說:“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數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割據局面愈演愈烈。長期存在的這種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響十分深遠。西方學者也指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著政治狀態,并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此期間,不僅皇權式微,割據政權帝王的威信掃地,而且文武之間的關系嚴重失衡,文官集團受到武將群體的壓制,地位淪落,仰承鼻息,縱然是宰相也要受制于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清代史家即評說道:士人生于此時,纏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正因為如此,文教荒蕪,當時社會上還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所謂:“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宋朝再一次通過兵變而建立。因此,出于對唐末五代亂政的恐懼,文官士大夫群體在強烈的自保意識下,堅定地支持皇權壯大,積極協助統治者實施一系列的“抑武”舉措,并期望朝廷復興儒教。于是,宋太祖基于自身統治需要而初步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自然得到他們的擁護和歌頌。
宋太宗統治后期,以科舉出身為主體的士大夫已重新獲得重視,逐漸成為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但是當門閥世族消亡之后,使得累世公卿、富貴長存的局面一去不返,這就決定了士大夫階層必須更緊密地尋求與專制皇權的結合。為了防止朝政偏離“崇文抑武”方略,導致武力因素再度猖獗,并最終危及自身的利益,他們必然更堅決地支持宋朝走“崇文”之路。
宋真宗朝以降,文官士大夫終于完全成為統治的主體力量,把握了朝政命脈,以至于還向皇帝表達了朝廷“與士大夫共天下”的自信,崇文氣象自然出現。至此,士人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現實中,都不能允許否定“祟文”路線,更不愿看到軍功集團勢力復辟。因此,他們不僅在現實中堅持既定方針,同時也是出于現實的需要,尋找并夸大開國時代的有關事例,以便宣稱“崇文”氣象一貫存在的合理性。
歷史的記憶就這樣延續,多少附加著后世的理解和想象。現實遠離過去,但在國家認同的背景下總能修正過去的歷史影像。
責任編輯: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