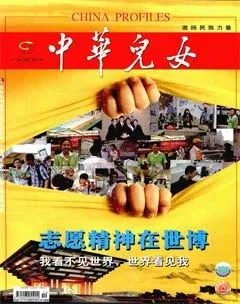李少紅:我需要有質量的交鋒
新版《紅樓夢》近來話題不斷,導演李少紅也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向來以剛毅示人、被媒體稱為“女強人”的她,竟然在發布會上情緒失控,哭了起來。
“我很少落淚,但那次在現場看到一些劇組幕后工作的花絮,我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工作狀態時的樣子,想到拍攝的過程,很多感慨……”
勇氣
從2002年新版《紅樓夢》立項之日開始,有關的爭論聲便不絕于耳。
李少紅把自己形容為“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播種機”。誰都知道,拍《紅樓夢》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誰碰都有可能頂上“玷污經典”的罵名,這個名字中帶“紅”的女人,偏就是在風口浪尖上頂住了壓力,接下了這塊燙手的“山芋”。“接力棒最終交到我的手中,我就一定要盡我所能把它拍好,呈現給廣大熱愛《紅樓夢》的觀眾。”
其實,早在1984年,謝鐵驪在導演電影版《紅樓夢》時,就找來李少紅做副導演。當時的李少紅負責選演員的工作。她詳詳細細地把《紅樓夢》通讀了一遍,邊看邊做筆記,以求選出的演員能最大限度符合原著。結果在電影將要開機之際卻懷孕了,李少紅只好放棄做了一半的工作,專心待產。
新版《紅樓夢》一經接手,李少紅的創作欲望迅速被點燃了。“《紅樓夢》巨大的藝術魅力就像無邊大海中翻卷起的漩渦、狂瀾,無論是巨輪還是扁舟,每一艘靠近它的船只,都不可避免地被吸納吞沒。”
李少紅花了大量時間搜集資料,請教各方“紅學”專家。劇中,從一窗一紗,到人物行住坐臥的尊卑次序,隨便拎出一個細節都能說出歷史根據和講究。為了符合原著,劇組幾乎是“一邊查、一邊拍、一邊改的”,大家生怕走錯一步,有些場景甚至因為一個道具的差錯而返工重拍了多遍。
李少紅按照自己所要達到的拍攝效果給擔任制片的李小婉列出了一個清單,當李小婉按照這個清單算出預算額度時,立刻驚呆了——1.18億!她足足用了好幾天來面對和消化這個數字。但是,李少紅決心已定,要么就不拍,要拍就拍出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之作。
1.18億,這對制片人李小婉來說是一個讓她頭痛的巨大挑戰。投資方只給了4500萬,若要達到李少紅提出的藝術效果,她就必須解決其余的資金。
資金的威脅幾乎是《紅樓夢》拍攝中最艱難的事。難過的不只是李小婉,還有每天身處片場的李少紅。有時候,兩個人會在電話兩邊同時沉默,說不出一句話。“我是花錢的,別人是去找錢的。我幫不上忙,心里很內疚。”李少紅說,“她在馬路邊上站著的感受比我要難過很多,這個過程很煎熬的。”
2009年1月,春節即將來臨,此時的《紅樓夢》劇組已經5個月沒有發工資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個消息不脛而走,被媒體曝了光,讓很多本來愿意投資的企業也因此望而卻步。“小婉為找錢奔波在各地。我盯著監視器的同時盯著手機。主任口袋里只剩下幾十塊錢,場工自己墊錢給大家買水。可拍攝現場依然熱火朝天地搶進度,看不出來任何危機。這幅景象激勵著我和小婉,那段時間我倆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一定要想辦法拍下去。”
叛逆
李少紅的影視劇經常被觀眾贊為“唯美”的畫卷。它們都有著精美的畫面,考究的服裝和詩化的語言,而這些影視劇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女性。從為愛情一意孤行的太平公主,到孤傲而丟失了愛情的秋儀,再到那個心中始終拒絕長大的寶貝,在這些女人身上,都能看到李少紅的影子,都有李少紅給予的情感。作為第五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少紅的風格,可以說與她的生活經歷和成長環境關聯很大。
李少紅14歲那年,她有了一個弟弟。這年冬天,她離家出走,因為她覺得自己被父母冷落了。再也不想回家的她決定去當兵,父母擰不過她。“我記得我拿著一個帆布旅行包上火車,看到爸爸站在車窗下,開始還保持鎮靜,讓我路上小心旅行包,到了來電報。我心里也很硬,在我看來,我爸和我媽已經不再愛我了,他們的情感完全被我弟弟占據了,我和弟弟相差14歲,我已經懂得了嫉妒”。
李少紅就是用這種“殘酷”的方式引起父母的注意,“現在想來很幼稚,當火車開動,我爸爸隨車窗行走的腳步越來越快,我使勁咬住嘴唇……那一幕永生難忘!后來很多年,我知道爸爸回去第二天就滿嘴起大泡,連續3天到永定路郵局門口轉到天黑,想發電報讓我回來。我的離家讓他們痛不欲生。”
李少紅被分到一個男兵連,參加野營拉練,每天山地行軍九十多里,摸爬滾打直到夏天,女兵們幾乎都忘記了自己的性別特征。李少紅說:“那個年代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或許就是由于這些特殊的經歷,讓李少紅有了特殊的內心敏感,她才會在以后的作品中,有意無意地去追尋那些被丟失的少女時代。
當那些敏感和自卑的成長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腦海中反而越來越清晰時,李少紅也逐漸形成了一種以主觀的女性視覺來感受歷史的獨特的影視風格——這種嘗試是大膽的,甚至也包含著女性特有的任性。
風格
李少紅的母親是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李少紅少不了耳濡目染。年少的她對“導演”的全部印象來自母親,小時候并沒覺著有何特別。家里有一些電影理論的書,都被父母裝起來,塞在床下,她就偷著看。李少紅經常用書里中外電影的名字和同學猜字,她經常立于不敗之地。
在那個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紅懵懵懂懂、平平淡淡地度過了自己的少女時代,然而,內心并不安分的她卻一直在尋找“出走”的機會。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的考場中,當李少紅一氣將15分鐘的長詩《周總理辦公室的燈光》朗誦完畢,全場寂靜無聲時,她知道自己成功了。從此,電影就成了她出入夢想的途徑。
1982年,李少紅被分配到北京電視制片廠,導演生涯正式開始了。談及導演生涯,李少紅感慨萬千:“我覺得當導演這件事和我的生命本身就有關系似的,很容易就迷上了”。
1980年代末的影壇盛行“黃土地情結”,又或者是“男人把女人扛在肩上”的故事,而她卻饒有興致地塑造了一個孤獨怪異的殺手、兩個接受改造卻始終找不到歸屬感的妓女,還有追求不到愛情自殺了的繁漪,以及頗有些職業女性苦悶的武則天等角色。
身為女導演,李少紅覺得自己有許多感情優勢。所謂女人是感性動物,男人是理性動物,女人以感性的視角介入以男性為主體的影視藝術,應該既有艱難,又有優勢。在李少紅執導的影視作品里,人們總是能夠明晰地看到她對女性意識的強調和一種個人化的、女性化的對于社會、對于人生和對于女性自身的認識。
正因為如此,她才能在《血色清晨》中將異國作品與中國情境完美融合,講述了深刻的現代中國寓言;又能在《桔子紅了》中以古典唯美的筆觸書寫幽幽情殤……李少紅的“女人味”是從她大氣、爽朗的舉止中透出來的,正是這種內斂的“女人味”,成就了她的事業。
但是,處于工作狀態中的李少紅卻有著男人一般的狠勁。一位與她合作過的演員說她是那種為了電影可以犧牲一切的人。曾經在一個很危險的拍攝現場,李少紅囑咐大家千萬小心別跑別摔倒,因為周圍全是工廠里的電鋸、切割機;結果她自己忙起來卻忘了,跑來跑去指導各部門工作,一下子摔倒了。她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轉身又跑走了。
當時現場所有的人都傻眼了,誰也不敢吭聲。因為她摔倒的地方,正好有一根從地面豎起來的鋼管,離她的頭也就5厘米!
對話
《中華兒女》:新版《紅樓夢》熱播之下也伴隨著很多爭議,你怎么看?
李少紅:作為一部藝術作品,我已經完成了。而一百個人心目中便有一百個《紅樓夢》,并不等于是你拍好了,它就達到了每個人心目中的《紅樓夢》。任何的褒貶,我想都要寬容對待吧。時間和作品自身是有說服力的。
《中華兒女》:自己那么執著的東西,別人不一定從這個層面來理解,你覺得窩火嗎?
李少紅:不會吧,不是所有的人吧,我覺得這種真誠和價值是會被承認的。而且就目前來看,也不是一種聲音一邊倒的,但是我覺得需要有質量的交鋒。因為你是認真的,你需要你的對手也認真,我覺得這才能夠對得上話,有對話基礎。如果是都不認真,我覺得沒必要去對話。
《中華兒女》:記得你曾經說過,導演不是女人該選擇的職業?
李少紅:它是被男性規定了的有性別的職業吧,所以每個人介紹你的時候,都會前面加兩個字——女性,這其實是某種暗示,暗示就是說,好像你做了本來不是你做的事情。
《中華兒女》:大家都在說“李少紅風格”、“李少紅烙印”,比如光、色彩、氣氛營造等,你是不是也在刻意的為《紅樓夢》打上這樣的風格印記?
李少紅:什么是我的“烙印”?是“唯美”嗎?要我接拍的時候,投資方就這么說,《紅樓夢》的內容沒有多大發揮空間,能發揮的地方就是拍得美拍得好看。我牢記住這句話,下的最大工夫就在影像語言和影像藝術的品質上,能夠立體表現出小說中的文學寓意和曹雪芹描寫的夢幻意境。
《中華兒女》:能介紹一下你使用特技的想法,以及特技團隊的背景嗎?
李少紅:《紅樓夢》的特效最難的并不是神話開篇,是繪景。因為美術上的要求很高。特效做的逼真相對比做的很有美術感要容易。神話開篇的難度在設計上,也就是什么樣的形象構思,靠創意取勝。凹晶溪館的天和背景的群山換了又換,在虛實之間的分寸要拿捏得非常準確才行。我們的特效團隊是目前國內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