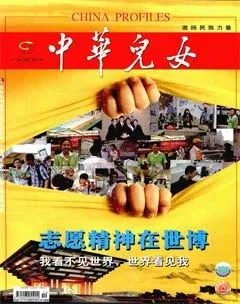欒俊學 帶著正義奔向新聞現(xiàn)場
聽欒俊學講個人經(jīng)歷,好像在聽一部跌宕起伏的廣播劇,主題是正義。
從進入《遼沈晚報》體育部做記者至今,欒俊學先后任要聞部社會新聞戰(zhàn)線記者、首席記者、要聞部主任、特別記者調查部主任、編委,職位在變,激情和使命感從未偏離。
夢想從電大起步
欒俊學,“50后”,那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記憶是上山下鄉(xiāng)當知青,他也不例外。初中畢業(yè)下鄉(xiāng),文學夢只能擱淺。1979年回到家鄉(xiāng)沈陽,他又陰差陽錯進了技校,畢竟學技術才是那個年代大家認為最安全的選擇。但是當時風靡一時的文選講座,給欒俊學帶來了莫大的樂趣。
1982年,已經(jīng)在沈陽重工機械廠上班的欒俊學,看到了沈陽電大開辦中文班在招生,他二話不說拔腿跑去報名,終于在電大圓了自己的文學夢。沈陽電大創(chuàng)建于1960年,“文革”10年也遭到停辦的命運。1979年,云開霧散、知識重新回歸的大環(huán)境下,沈陽電大恢復招生。欒俊學則是沈陽電大中文系第一批學員。
那是人們對知識無比狂熱的年代,被耽誤的一代人拼命學習,被剝奪教育權太久的教師們也恨不能一下子把知識全都倒給學生。欒俊學記得很清楚,當時沈陽電大為他們請來的都是遼寧大學中文系等的骨干力量,他還記得他們的名字——王春榮、高凱征等等。
1985年,欒俊學經(jīng)過一番苦讀,終于順利地從沈陽電大畢業(yè)。“開始半工半讀,很苦,到后來一年半,是脫產(chǎn)學習。”不過這種刻苦也在此時開始有了收獲,欒俊學被調任廠里宣傳部,創(chuàng)辦了沈陽重工機械廠廠報《沈重報》,還當上了《遼寧日報》的通訊員。他經(jīng)過仔細觀察、親自體驗之后寫出來的《公交車乘客眾生相》、《房改沉思錄》等一系列的文章,不但見報,而且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憽杩W被電大重新點燃的熱情在這里徹底燃燒起來。
到1991年離開沈陽重工機械廠,欒俊學在工廠摸爬滾打整整6年。在他看來,這是他終生難忘的一段時光。如果說當年沈陽電大老師在各自專業(yè)領域的建樹,激發(fā)了欒俊學如饑似渴的學習熱情;他們對學生的熱情,再次點燃了欒俊學心里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夢想;那么工廠的歷練,則讓欒俊學的職業(yè)生涯從此打上了“百姓民生”的烙印。
記者要耐得住寂寞,禁得住誘惑
長期以來,欒俊學在特稿部。這是一個報社里最有激情的部門,面對壓力和危險最多,也面對誘惑最多。欒俊學說,首先自己要頂住。
不止一次,他在進行監(jiān)督報道采訪的時候就會接到各種電話,有求情的、有恐嚇的,無一例外被他回絕。有個涉黑團伙曾經(jīng)放出話來,“20萬買欒俊學一條胳膊。”他知道了這件事,沒有說什么,轉身奔出門,投向另一個采訪中。
《禽獸教師為何課堂施暴兩年》系列報道,在當年引起國內(nèi)很大震動。這個被多家媒體關注過卻石沉大海的案子,最終在欒俊學筆下見報。罪惡終于在陽光下無處遁形。“當初是沈陽市蘇家屯區(qū)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向我披露了一些內(nèi)幕:一所小學的教師把班里6個女生全部強奸猥褻,而且獸行持續(xù)了兩年多。”欒俊學聽完,立即報選題、出發(fā)采訪。
那時教師程世俊已經(jīng)被關了6個月,案件毫無進展,被害學生家長到處寫投訴材料,卻一直無人關注。案發(fā)后當?shù)匾恍┎块T對此事也一直遮遮掩掩,特別是學校主管部門得知記者去采訪,便四處找人說情。“記得去那個村小學校采訪時,學校大門緊閉,我們就開著車在村里轉,我們?nèi)ゲ稍L老師,多數(shù)都搖頭,我們再追就點頭,就是不多說一句話。”在一個受害小女孩家中,小女孩的爺爺舉著一疊曾經(jīng)來采訪過的媒體記者名片把欒俊學趕出門,最后看著欒俊學在村子里四處奔波采訪,才又半信半疑地跟他把過程講了一遍,反復問“你能報道出來嗎?你能報道出來嗎?”欒俊學一邊保證著,一邊心酸……
當這篇報道見報的那天,欒俊學接到這個老人的電話:“欒記者,我們是想把這稿發(fā)出去,可是你別因為我們把自己飯碗丟了。”記者不應寫君子所不當言者,欒俊學恪守著這樣的職業(yè)天條。而他那些冒著危險做出來的輿論監(jiān)督報道,充滿道德與非道德的較量,表現(xiàn)出兩種人格的對撞。
2009年,第十個記者節(jié)來臨之際,欒俊學捧起長江韜奮新聞獎,他說,希望“讓榮譽純潔心靈”。
保持職業(yè)意識,激情依舊在
欒俊學是《遼沈晚報》的元老。從1993年《遼沈晚報》創(chuàng)刊至今,他就一直拼在一線。很多原來跟他并肩作戰(zhàn)的兄弟甚至學生,現(xiàn)在在職務上都不輸于他,甚至成了他的頂頭上司,欒俊學從不嫉妒,他最愛的還是背起背包,奔赴一線。這些年來,他得到的榮譽更是讓人驚嘆,可是他從來都是把它們當成已經(jīng)翻過的一頁,默默打包塵封,不讓自己負重前行。
在《遼沈晚報》,欒俊學最先做體育報道。為了寫好第一手資料,他數(shù)年如一日,每天都騎著自行車去遼寧體育運動技術學院,與運動員們打成一片。在北京采訪期間,由于資金緊張,他只能住在國家體育局的地下室招待所,但是他以苦為樂,克服了生活條件的簡陋,臥薪嘗膽。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先后采訪了當時做運動員后來成為遼寧乒乓球男隊主教練的于沈潼,剛剛調入國家隊的王楠、戴國紅等許多遼寧籍的國家隊運動員,此外剛回國家隊做教練不久的蔡振華,陸麗、高敏、伏明霞、鄧亞萍、王濤、鄭海霞、李小雙、李永波、李亞光、等等一大批如日中天的教練員和運動員也都成了他采訪的座上賓,經(jīng)過他不屑的努力,欒俊學終于在體育新聞界闖下了一片天地。
2000年11月20日,位于沈陽和平大街的瑪莉藍大廈17樓發(fā)生入室搶劫案。欒俊學接到線索后立即趕往現(xiàn)場,并進入了與歹徒一墻之隔的室內(nèi)。此時挾持人質的兩名歹徒聲稱身上有炸藥,現(xiàn)場異常緊張,警方調來了防暴大隊,防暴警員告訴他現(xiàn)場存在危險,但是為了采寫現(xiàn)場新聞,他依然堅守樓內(nèi)22小時,期間還為公安局擬寫了針對歹徒的勸降書。
當晚他在樓內(nèi)寫出了2000字的文字稿發(fā)回報社,次日他和樓外記者聯(lián)合采寫的《兩狂徒持槍與警方對峙》充分展現(xiàn)了沈陽警方解救人質的全過程,在全國引起轟動。
而他三次到安徽,配合公安機關破獲假幣販賣案件的故事,早已成為欒俊學最著名的橋段之一。2004年,他借此一役當選中央電視臺“中國記者風云人物”。
欒俊學曾經(jīng)說過:“輿論監(jiān)督報道中,面對的是更多的困難,所以我們要執(zhí)著,要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我們還要面臨一些失敗,不是所有的采訪都能獲得成功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堅持,堅持靠什么,就是我們對工作的激情。”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欒俊學每天睡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傳呼機調到震動狀態(tài)壓到自己枕頭底下,有突發(fā)新聞要采訪的時候,不至于吵到家人。直到今天,他已經(jīng)是部門主任、編委,還會像二十年前一樣,以最快的速度沖向現(xiàn)場、沖進一線,心中只想著身后的讀者,卻往往忘記了家人。
2008年12月,欒俊學新聞作品集《白紙黑字》問世。清華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建明為這本書寫下這樣的文字:“媒體與新聞道德的功力來自記者的正義,記者的正義感是新聞業(yè)的靈魂,而二者都是由記者的道德成就的。它證實媒體是一項公共事業(yè),承擔著大眾的信托,成為良知的捍衛(wèi)者。記者明思明論,正確公平,是新聞業(yè)的基礎。記者只能寫他心中信以為真的事,艱難地搜尋真相,面對歹徒臨危不懼,《白紙黑字》正是這些美德的積淀。”
“就一個稱職的記者而言,他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社會公正的守望者,而絕不是一個旁觀者。”在遼寧電視臺請他做節(jié)目時,欒俊學說過這樣一句話:“正義只有遲到,不會永遠不到。”觀眾席響起一片掌聲。其實,他每一天都在路上,帶著正義奔向每一個需要他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