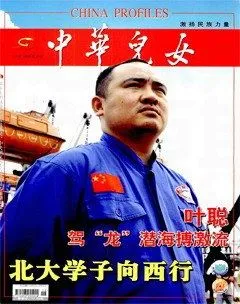樊錦詩“敦煌女兒”的牽腸掛肚
在敦煌這個古遠而神奇的地方,樊錦詩從大學畢業到現在,度過了近50個春秋輪回。樊錦詩說她喜歡晚上出來走走,因為沒有了白天的嘈雜和喧囂,夜晚的莫高窟像個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靜美。“一種魅力,一種極大的吸引力在吸引著你,讓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來。現在對我來說,這還上升到了一種使命感。”
齊耳短發,渾身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裝待發……這是矗立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尊雕塑,名曰《青春》。
瘦小的身材,樸素的穿著,花白的頭發,匆匆的腳步,勞碌的身影……這是有“敦煌的女兒”之譽的中國十大女杰(之一)樊錦詩。
一般人很難將塑造于20世紀60年代的青春倩影與年過古稀、不施粉黛的著名敦煌學家、石窟考古專家、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專家樊錦詩聯系在一起。其實,《青春》雕塑的原型就是當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直奔祖國大西北的樊錦詩。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的青澀女孩如今已是滿頭華發,不變的是報國志、赤子情。對這位青春交給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傳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兒”來說,敦煌就是家,割不斷、離不開的家!
與“墻壁上的博物館”一見鐘情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開鑿于公元4至14世紀,由于其壁畫及彩塑藝術的宏富輝煌和內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墻壁上的博物館”等稱譽。
在敦煌這個古遠而神奇的地方,樊錦詩從大學畢業到現在,度過了近50個春秋輪回。樊錦詩說她喜歡晚上出來走走,因為沒有了白天的嘈雜和喧囂,夜晚的莫高窟像個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靜美。“一種魅力,一種極大的吸引力在吸引著你,讓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來。現在對我來說,這還上升到了一種使命感。”
樊錦詩出生在北京,成長于上海,“上面兩個姐姐,下面兩個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戰亂年代的她,從小體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兒麻痹癥,這種疾病導致她的腿腳不如常人那么靈便。“父親是個工程師,畢業于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專業,曾在北京大學當過兩年講師。父親對藝術的喜愛也感染了我。小時候的我不愛說話,很靦腆。最大的快樂就是去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
1958年,20歲的樊錦詩考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大學期間,著名考古學家閻文儒教授的“石窟藝術”課是樊錦詩最喜歡的課程之一。大學里,樊錦詩就特別關注光彩奪目的莫高窟,熱烈地向往著敦煌的神秘寶藏。
1962年的一次實習機會,使她得以來到了這個魂牽夢繞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內涵深深打動,全然忘記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記了用馬廄改建的簡陋宿舍,忘記了苦澀、令人腹瀉的飲用河水。“一見鐘情”的她鉆進冰涼孤寂的莫高窟感覺就像鉆進了故宮博物館,覺得新鮮而充滿了樂趣,她為敦煌藝術而自豪,為自己有機會直接接觸敦煌這份偉大的人類歷史文化遺產而欣慰……
鑒于樊錦詩在實習期間的突出表現,她被當時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先生所器重。同時,樊錦詩為常書鴻的事跡所感動、敬仰:“當時,我常想:這地方,他怎么能呆幾十年呀?沒有電,沒有飲用水,晚上上廁所都要去很遠的地方。根本沒有娛樂,與世隔絕,平時來個人都會覺得新鮮,信息也不通,報紙一來一大摞,起碼都是一個月以前的。一部《列寧1918》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還披著軍大衣看。我在大城市長大,確實沒有想過要在那里干一輩子。”
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報效祖國、服從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響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價值觀。研究所去學校協商要人,我們四個實習生全要。學校當時只答應給兩個,我是其中之一。”盡管學校已決定她留校工作,但她毅然放棄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了西域大漠深處的敦煌。
雖說對大西北惡劣的自然環境早有心理準備,但當她真正住進莫高窟旁邊的破廟里之后,才確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通訊困難……
“本來以為敦煌那么漂亮一個地方,肯定是窗明幾凈,那些專家們肯定都很氣派。結果都穿著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個個都跟土老帽似的。”樊錦詩坦陳:“說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那是假話。和北京相比,簡直就不是一個世界,到處是蒼涼的黃沙。”
樊錦詩來到所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和其他幾位同事撰寫敦煌第一部考古調查報告。三年后草稿剛剛完成,“文革”撲面而來,研究工作被迫擱淺。
“文革”以后,歲月倏忽,人已中年。這時候,要離開敦煌純粹就是為了孩子,為了家庭。但女人又是異常感性的,“十幾年磨合,我早已習慣了大西北,愛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護石窟當成了一份終生的事業”。
令“敦煌女兒”牽腸掛肚的石窟
1998年,60歲的樊錦詩被任命為敦煌研究院院長。“這是整個世界的寶藏,擔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縮。”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個棘手的難題——為發展地方經濟,相關部門計劃將敦煌與某旅游公司捆綁上市。全面商業化的操作與保護的矛盾讓她憂心忡忡,寢食難安:敦煌是國家的財產、人類的財產,堅決不能拿去做買賣,捆綁上市是有風險的。為此,樊錦詩四處奔走,跑遍了相關部門,向人們講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現狀,反復強調保護的重要性。當時樊錦詩堅決不同意,“硬是把壓力都頂了回去”。
一場將敦煌捆綁上市的風波終于平息了,日漸消瘦的她卻又有了新的思考,她開始進行游客承載量的研究,希望在滿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長期處于疲勞狀態,文物保護與開放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來恒定的小氣候環境,我們的試驗監測數據顯示,40個人進入洞窟參觀半小時,洞窟內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氣相對濕度上升10%,空氣溫度升高4攝氏度。二氧化碳長時間滯留窟內以及窟內相對濕度增加,空氣溫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蝕壁畫。”
樊錦詩和她的研究集體一直在努力尋找一條科學的途徑,來化解文物保護與開發的矛盾。樊錦詩說,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石窟“保重身體”,盡量老得慢一些,爭取讓它再活1000年。
面對游客迅猛增加帶來的挑戰,敦煌研究院開始開展大量卓有成效的保護工作,順利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從研究、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具有權威性、強制性和約束力的保護措施。同時,敦煌研究院還開展了洞窟游客承載量的研究,尋找著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載量的科學數據,建立了洞窟旅游開放標準,實施輪流開放、參觀預約和預報制度,控制進窟參觀人數。“文物就像人的胃,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飯。文化遺產的開發利用必須建立在以保護為主的基礎上,進行科學、適度的利用。”
樊錦詩積極探索解決旅游人數大量增加與石窟保護之間矛盾的解決辦法,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關于建設莫高窟游客服務中心的建議》,被全國政協列為重點提案,得到溫家寶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目前,提案的各項建設得到實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專門從事研發敦煌石窟文物數字化的部門。在樊錦詩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漸退化,何況有1000多年歷史的石窟、壁畫。“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畫等珍貴文物,我們得想辦法把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來。‘數字敦煌’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樊錦詩憧憬,“數字敦煌”讓千年敦煌成為“不朽”遺產。
的確,今日的敦煌,已不僅是一個光彩奪目的藝術殿堂、一個世人向往的美麗地方,不僅是一處文物、一座寶藏、一門學問,還是一種價值、一個品牌、一種語言,甚至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一種象征。為了人類的敦煌,為了實現敦煌夢,樊錦詩扎根大漠、嘔心瀝血!
OK!樊錦詩亦錦、亦詩!一段華麗而又樸素的錦緞,一首值得咀嚼、回味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