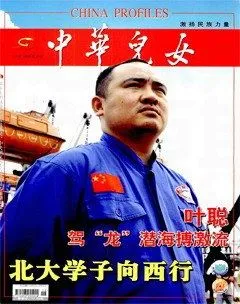陳育寧 激情揮灑大西北
“人的一生,大約就是在這樣的搏擊中前進,我們的事業也是在這種不斷克服困難和解決矛盾中前進。我想這就是人生的追求,這樣的人生是充實的。”
——陳育寧
無可非議,陳育寧是一位學者型領導。陳育寧說,他最喜歡別人叫他“陳老師”,他說這讓他覺得親切。在寧夏大學學生們的眼中,已經不再把陳育寧看作校長,而是把他視為一個可以傾吐心扉的知心朋友。
陳育寧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此后10多年,他一直扎根于西部基層。在風沙撲面的鄂爾多斯,在廣闊的內蒙古草原,都留下了他奮斗的足跡和不倦的思索。
20世紀80年代初期,陳育寧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從此由一個策馬奔波的基層干部轉變為潛心書齋的學者。1987年,陳育寧被調回到他的出生地——寧夏,既做過研究員、教授,也當過自治區人民政府的辦公廳主任、銀川市的市委書記、寧夏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鄂爾多斯——永遠的牽掛
陳育寧在北方民族歷史和文化、蒙古史、西夏史、回族歷史與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學術建樹,在國內學術界深受肯定和贊譽,“鄂爾多斯學”更是傾注了他的心血,他在“鄂爾多斯學”醞釀、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而陳育寧與鄂爾多斯究竟有著怎樣的淵源?這要從他一段不凡的經歷說起。1968年夏天的北大燕園對陳育寧來說是美麗的,同時也是無情的,因為他即將畢業,離開他學習和生活了6年的母校,奔赴內蒙古“接受再教育”。
陳育寧出身在一個普通的小職員家庭,家境貧寒,是祖祖輩輩當中的第一個大學生。1962年,他以寧夏的高考文科“狀元”頭銜只身進京,跨進莊嚴的高等學府。他至今記得,當年離家時,身上穿的是父親脫下來的一件超長、半舊的中山裝,里面則是母親的襯衣。
1968年,陳育寧來到內蒙古最貧窮的伊克昭盟,這里靠近荒漠,隨時面臨會被大風卷入黃河的危險,衣食簡陋,生活清苦,其艱辛可想而知,在這里,陳育寧一干就是10年。
所幸的是,在這艱苦的歲月里,陳育寧有夫人一直陪伴。陳育寧的夫人湯曉芳與他是北大的同學,畢業后,湯曉芳被分配回老家上海。然而,湯曉芳卻毅然舍棄都市的繁華,冒著撲面的風沙,來到荒涼的鄂爾多斯與陳育寧共命運。二人風雨同舟走過了幾十年,夫婦有共同的事業,在他們的“小書齋”一起討論學術問題,相互修改文章,共同完成課題。“小書齋也是我和妻子醞釀討論構思論文的地方,我們出版的幾本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大都是在這個小書齋里寫出來的。”
這10年間,出于學習歷史專業的偏愛,陳育寧對“鄂爾多斯”這個好聽又上口的名字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草原給了陳育寧開闊的胸襟和視野,也給了他研究學術的機遇。陳育寧說,他的鄂爾多斯情結在少年時就開始萌芽了。
“我少年時看過電影《鄂爾多斯風暴》,看過《鄂爾多斯舞》,鄂爾多斯給我留下了深刻又神秘的印象,既然有機會置身其地,就一定要弄個明白。我到檔案館、文化館查閱資料,向當地的蒙古族同胞詢問了解。”常年深入草原牧區考察調研,他受到鄂爾多斯淳樸民風的熏陶,此后不管走到哪里,職務怎樣升遷,他都難忘與蒙古族牧民結下的深情厚誼。
許多年后,陳育寧問自己,“為什么鄂爾多斯有著如此強烈的吸引力?這里是一座金山嗎?這是一處優美的田園嗎?不是,荒涼和貧瘠曾是這片土地的特征。說到底就是一個‘情’字,構成了巨大的凝聚人心的力量,這種無形的力量把人們緊緊地連在一起,鼓勵著人們為之奉獻,為之犧牲,這種精神傳至一代又一代,形成一種強大的傳統。”
陳育寧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激情揮灑的歲月,言語間滿是深情與懷念。“鄂爾多斯有最真誠的人情,和最能表達這種感情的形式,當撼動人心的鄂爾多斯敬酒歌唱起的時候,當朋友把斟滿美酒的銀碗和哈達高高舉起的時候,你會覺得,雜念和虛偽會得到凈化,豪邁和真情會充滿心中。我至今還收藏著許多鄂爾多斯蒙古族民歌的磁帶,隔一段時間總要在那讓人心蕩不已的歌聲中陶醉一番”。陳育寧笑著說,就連地地道道的老上海湯曉芳,現在都和他一樣保留著當年喝奶茶、吃炒米、吃手扒肉的習慣。
風雨幾十載,陳育寧無論走到哪里,他的生活,已經與鄂爾多斯不能分離,他的散文集《永遠的牽掛》,就是這份情感的深情表達。
“一介書生”的三次角色轉變
1995年6月5日的《光明日報》登載一則消息,標題是“民族史專家當上市委書記”。消息說:“寧夏各界近日以濃厚的興趣傳遞、議論著一條新聞:著名民族史學專家陳育寧研究員出任銀川市委書記。”在介紹了陳育寧的學術經歷后又說,“兩年前,他從社科院院長的崗位上調任自治區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這次職務的變動,使他再次成為新聞人物。”是的,這的確是一次角色大轉換。
有句話叫“風箏情結”,比喻離鄉在外多年的人,就好像風箏,不管它飛得多么高,多么遠,但總有一根線牽動著它,最終又把它收回來。1987年,陳育寧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地方寧夏,鄉情和親情都激勵著他,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在這片土地上成就一番事業。當時陳育寧的父親看到兒子回來非常高興,寫得一手漂亮書法的老父親抄錄了唐朝詩人賀知章的一首詩送給他:“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他在寧夏曾先后擔任過許多重要的行政職務。從學術單位的領導人到主管一方的“父母官”,陳育寧干一行、愛一行,也鉆一行。他在寧夏社會科學院擔任過院長,在寧夏大學擔任過黨委書記兼校長,在這兩個寧夏的最高研究機構和最高學府,他都干得有聲有色。
在陳育寧“知天命”之年,他出任銀川市委書記。一個地區的發展變化,總是和這個地區領導者的素質、能力、人品分不開。市委書記是一個政治角色,他必須通過在政治舞臺上的表演來體現自己的價值,實現自己的愿望。陳育寧在銀川市6年,那是銀川市經濟和文化面貌發生重大變化的6年。
這6年,是寧夏最好的發展時期,銀川市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發展的成績可以用一系列經濟指標的增長和百分比等數據來說明,除了這些實實在在的數據外,更有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從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切地感受到了銀川的變化和發展。
2001年,陳育寧迎來他個人角色的再次轉變,這一次,他擔任的是寧夏大學的校長兼黨委書記。此后,寧夏大學由西部偏遠地區的一所普通的綜合院校一躍成為“211”院校,這其中,傾注了陳育寧無數的心血和智慧。2007年,陳育寧無可爭議地當選“2007年中國十大教育英才”。這一榮譽,正是對他在寧夏高教戰線上所取得輝煌業績的最好褒獎。
在評委會給陳育寧的頒獎詞中寫道:“他扎根西部,為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傾注心血,他正確處理規模與質量,教學與科研,加快發展與規范管理,全面提高與重點突破,發展目標與發展過程的關系,他是有區域特色、有較高水平、較高質量的大學的、確保學校可持續發展的民族史學家。”
陳育寧做什么像什么,當然和他的睿智有關,他是一名善于研究和學習的學者型領導。幾十年來,陳育寧一直保持著“剪報”的習慣,“我訂閱了很多報紙,平時我總是把對自己有用的知識、信息都剪下來,做成‘剪報’,供自己‘充電’,即使再忙也不放過學習的機會。”關注、支持“鄂爾多斯學”,是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后,投入精力較多的一件事。
如今,他已先后從寧夏政協副主席和寧夏大學黨委書記職位上卸任,當年的“小陳”和“小湯”轉眼變成了老字輩。當記者問及:幾十年來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他思索片刻回答:“簡單概括就是:名聲要好,水平要高。人的一生,大約就是在這樣的搏擊中前進,我們的事業也是在這種不斷克服困難和解決矛盾中前進。我想這就是人生的追求,這樣的人生是充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