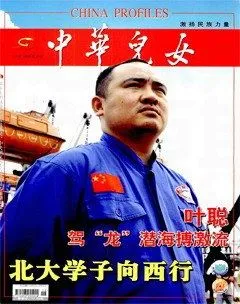李強 被收藏改變的人生
一張張清晰的黑白照片重現了當年日寇瘋狂蹂躪南京城的場景,一本本泛黃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抗戰時期的腥風血雨……李強,這位山東聊城民間收藏家歷經二十多年艱辛,收藏了大約三十多萬件日寇侵略中國的相關史料和物證。
民間抗戰收藏第一人
走進李強的藏品倉庫,首入眼簾的是一排排井然有序的貨架,一件件擺放整齊的物品;在常人看來,這是只有公共博物館庫房才有的景觀,但在這里真實再現。
斑駁生銹的刀鞘,閃著寒光的刺刀、指揮刀,猙獰丑陋的防毒面具,冰冷堅硬的鋼盔,上面還有一個個槍眼,殘破襤褸的軍服,成堆成捆的傳單、戰時良民證、選票、防化服、各軍兵種培訓教材,還有各種軍用器皿:望遠鏡、救護包、徽章、證書、貨幣,甚至彈殼、彈箱、皮帶扣、留聲機、日式手提式保險箱、顯微鏡、子彈扣……總之涵蓋了一切抗戰時期所使用的物體。
“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串串故事,驚心動魄,刀光劍影,血淚交迸。”李強說。1970年代初出生的李強烙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歷史使命感。
李強的收藏癖好與家庭和成長經歷有關。李強出生在農村,爺爺曾是一名地下共產黨員,但當時家人并不知情,直到后來的一天晚上,一群日軍在村里一名“皇協”的帶領下將爺爺抓走后,家人才知道爺爺早就秘密參加了革命。當時日軍抓住爺爺后并不執行槍決,而是活埋。在活埋前,爺爺拼命反抗,日軍就用槍托將他頭部打得血肉模糊,但頭腦清醒的爺爺就勢裝死,在填埋過程中,趁日軍不注意時逃跑了;隨后,日軍馬上進行追殺,并不斷在他身后開槍,其中一顆子彈從頭皮擦過,逃跑成功的爺爺命雖留下,但頭上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
這個被爺爺講了無數次的故事也深深印在了李強的腦海里,如同爺爺頭上的那道疤痕。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模糊的歷史使命感的萌動就變成了對抗戰時期舊物的收藏沖動。這位抗戰軍人的后代便開始了收集抗戰文物,考證大量資料史籍,一發不可收拾。
“80年代初,村里有些家存有一些當時日軍侵略時遺留下的木桶、鐵桶、帆布袋子等,因為當時日軍侵占這里時,村里的人都不敢在家里住,躲藏在地里、樹林或溝里,日軍進村后有時就住在老百姓家里,走后會遺留些東西,鄉親們知道我喜歡收藏,那個年代,他們也都是免費送給我。”
隨著國內收藏市場越來越火,能在國內搜集到的抗戰文物也越來越有限。李強因收藏而結交了很多日本籍朋友,朋友們經常帶他去日本跳蚤市場,或者看到這方面的資料后,用相機拍下來,再通過網絡給李強傳過去,如果李強感覺可以就會讓朋友代買下來。“基本上在日本回購得多,而且主要是以史料性為主。從照片、小物件、刊物、寫真片、寫真畫報和字畫等等,那個年代報刊全部是以宣揚軍國主義為體裁,涵蓋了很多場戰役。”最讓李強感動的是上海的一位朋友,從日本給他寄來兩張抗戰時期關東軍的兩張布告和傳單。“因為傳單和布告的再生性很小,所以很珍貴。”李強激動地說。
這些藏品中,有一只木質的日本軍用藥械箱,里面有一些小玻璃瓶,瓶內有藥品殘留物,箱內還有一些手術刀具,箱子蓋上有“藥劑行李”的字樣。“據原來的藏家稱,這只箱子是當年侵華日軍731部隊使用過的。”
在李強心目中,他收集到的日本人所拍的上萬張反映二戰時期日軍侵華史實的老照片,在所有藏品中顯得尤其珍貴。這些已然發黃的照片都被放在一個個大相冊里,其中有兩本相冊的封皮上分別寫有“支那事變紀念”和“滿洲派遣紀念”的字樣。
30余萬件二戰時期日軍侵華物證的積累,也意味著大把時間、精力和財力的投入。雖然此類物品并不能像古玩字畫一樣“保值增值”,但要想從別人手里拿過來,必須得花大把的“銀子”。另外,在搞收藏初期,李強的舉動還曾引起家人和朋友的不解。
據李強周圍的朋友介紹,他幾乎沒有任何有錢人的喜好:不打高爾夫、不打牌、不講吃穿,也不追逐女人。他的喜好就是他收藏的“寶貝”。
盡管如此,李強覺得,做這件事情是很值得、很有意義的。“一個國家絕不能忘記自己的歷史,尤其是屈辱史、血淚史。如果忘了歷史,這個國家就沒什么希望了。”倉庫里每新添一個“成員”,李強都會仔細研究與其相關的史料,并存檔登記。閑暇之時,他帶著孩子在每一件藏品前默默駐足,與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對話”,接受愛國思想的洗禮。“對我和孩子來說,這是一個學習、了解二戰時期日軍侵華史的過程。作為一名中國人,經歷這個過程很重要!”李強說。
隨著在生意上的發展,李強的藏品涉及的門類也越來越寬,與百年來中國歷史有關的文物皆在他搜羅之列。由于抗戰文物收藏比較齊全,他因此被譽為“民間抗戰文物收藏第一人”。
民間手工造車第一人
在收藏的過程中,李強看了很多與抗戰時期相關的書籍和影視,但在看電視劇時經常會發現一些貽笑大方的穿幫鏡頭,“解放前的戲用的是解放后的上海760轎車,很多抗戰片里日軍開的竟然是東風車,日本人只會用日產,還有就是五十鈴貨車和轎車,吉普用的就是95式吉普。”
“我們平時欣賞戲劇、觀電影、看電視,除了欣賞其故事情節,演員的表演藝術,風景布景,那就是還要看到劇中出現的大量道具。道具都有靈性的,豐富多彩,很有講究,并在整個劇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強說起這些穿幫鏡頭時無奈地搖頭。
2007年4月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造成世界經濟的衰退,嚴重影響了李強所從事的紡織業。勞動力成本增加,行業所屬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市場的無序競爭等現狀,都擺在企業管理者李強面前,如何在經濟海嘯中順勢而上,從危機中蛻變,從危機中奮起,成為他每天要思考的最直接的問題。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后,李強決定利用自己的收藏,將企業逐步向文化方面轉型。
首先他想到的就是道具,“因為我有實物,最起碼做出來的道具給人的感覺是真實的;而且觀眾看后就會認為是那個年代的,有時光倒流之感。”
2007年底,李強在美麗的江北水城——聊城,成立了聊城古轅道具車制造有限公司,它是目前全國唯一一家集生產、銷售、來樣加工、收藏、克隆、維修、租賃、收購老爺車等為一體的綜合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最大的一家老爺車、道具車生產基地,所有產品均采用純手工制造。
第一次做的是輛美軍威利斯吉普。“當初首選做這款車,因為它是二戰時的軍用越野車,應該是首屈一指的代表車型,為美軍及其盟軍在戰場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戰后又成為民用越野車領域里的主力。由于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也裝配了大量威利斯吉普及道奇、中卡、中吉普,所以國內目前還遺留有一少部分,已經成為老爺車收藏者競相追逐的對象。”
當時他手里只有些平面圖型。“看到的都是車子的一面,內部構造沒法看到。說實話真的挺難,沒辦法,只能照貓畫虎。”李強說。
無奈之下,李強只能走遍汽車市場,反復觀察。他多次跑到全國各地,購買汽車模型、發動機、車前懸掛必備品……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后,他便帶領工人在車間里叮叮當當地造起來。
在他的帶領下,工人們經過近半年時間,按1:1的比例總算造出來了這輛車。該車除了發動機、電瓶、變速箱等無法手工加工的部件外,整個流線型車身、前后保險杠、方向盤、儀表盤、坐椅、車燈、喇叭,都經過了手工制作和改造。
這幾年的“造車”生涯中最讓李強難忘的是仿制慈禧太后當年的御用汽車——杜利埃老爺車,這個“中國頭號古董車”是1895年慈禧66歲壽辰,袁世凱投其所好,花1萬兩白銀買下為其賀壽的,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輛汽車。
為了再現這輛具有歷史價值的名車,李強按照歷史資料仿制了一輛。該車造成后不久,一家博物館得知這一消息后即刻表示愿拿出180萬元購買,然而被李強委婉拒絕。
“像我做的汽車,不僅可以做道具、能駕駛,同時也有收藏價值,并能增值。但我不喜歡賣。我們不是批量生產,每款最多也就做三四輛,純手工,很費時費力。即使做道具現在也是起步階段,主要以出租為主。”
經過三年的努力和探索,在他的帶領下,共開發了30款車型(如勞斯萊斯、道奇系列、福特T系列、托馬斯飛翔、奧茲莫比爾、大眾82、奔馳500K等世界名車),共做了八十多輛車,“這個數量在國內可以說首屈一指了”。隨著在圈內名氣越來越大,李強的愛車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尤其是影視制片人和導演。包括《建國大業》這樣的大片在內,至今他做的道具已在上百部影視劇中使用。“我們在橫店影視城里設立的分公司的制作定單早已排到了明年!”李強自豪地說。
一切緣于收藏
如果不搞收藏,李強仍然是個優秀的企業家,在他身上能感受到堅強的意志、腳踏實地的干勁和雷厲風行的作風。
李強是山東冠縣人,大學畢業后便到企業工作,從基層做起,短短幾年,便成為企業主要負責人之一,在他的帶領下,企業至今一直是縣納稅大戶。由于他熱心社會慈善事業,積極支持公益事業,也因此獲得過聊城十大杰出青年、優秀企業家等榮譽稱號,并當選為聊城市青聯委員、聊城市人大代表等職務。
談及他的成功之道時,李強說:“收藏改變了我的人生。不僅是知識方面的積累,主要是思想境界方面。其實愛國主義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說教,像我做企業的,愛國主義是我們企業文化的核心與精髓,應該把愛國主義主題教育與培育企業文化、企業精神相結合。比如說我們組織員工進行企業精神大討論,讓大家領悟到‘負重拼搏、團結進取、務實求精、自強自立’的企業精神,其實與中華民族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民族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通過討論,員工們形成共識:對企業職工而言,立足崗位,敬業奉獻就是愛國,愛崗敬業精神就是愛國主義在企業的升華。”
去年李強并購了當地一家醫院,并同時啟動三年前成立的“大愛慈善基金會”,該基金會主要用于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開展多種形式的醫療救助工程。
開業不久,醫院便接治三例因家庭貧困看不起病的患者,治療期間的所有費用全免。其中一名患者出院后給李強送來一面錦旗,李強得知后馬上讓工作人員給患者送去50元錢。“本來經濟就困難,再花30元做面錦旗,太浪費了,感謝之心有就可以。我辦醫院的目的不是純營利,我做醫院既讓患者感覺是醫院,同時也讓他們感覺是寺院。”李強說。
李強還依托醫院辦了一本《大愛文摘》的內部刊物,每期專門開辟一個欄目,介紹他的抗戰藏品,宣傳愛國主義,受到員工及社會讀者的一致好評。
近年來,隨著李強藏品日漸增多,他在圈內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一些慕名而來的收藏家帶著巨款造訪李強,想將他的抗戰文物收購,都被李強婉言謝絕了。還有日本人提出更為優厚的條件回購他收藏的史料,李強“連談都不談”。在他看來,這一件件浸透自己心血的藏品,寄托了自己的心愿,又豈是金錢所能衡量的。再者,一件件藏品都像跟隨自己多年的老友,又怎能輕易舍棄?
“我這人做事認真,性格太有棱角,朋友評價我‘劍走偏鋒,特立獨行’。所謂人生的‘四碗面’——世面、場面、情面、臉面,我都‘吃’過了,名利、物欲等現在都不太去想。目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個愛國主義基地,把我收藏的侵華物證放在展覽室,向社會開放,供后人參觀。我發自內心地想用我的藏品‘說話’,去告慰先靈,警示后人,咱們的傷痕還沒有愈合,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應警鐘長鳴,勿忘國恥!”李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