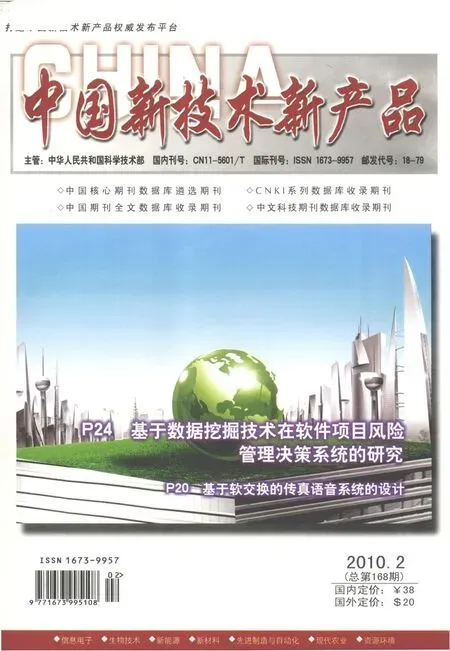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張鳳波
(賓縣滿井鎮農村經濟管理中心,黑龍江 賓縣 150404)
1 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改革30年以來,農產品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且隨著加入WTO,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和市場開放成為不可避免的大趨勢,農民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競爭,不僅受到資源與市場的雙重約束,而且在直接面對統一的大市場時,還愈來愈受到小規模分散化生產所形成的較低的組織化程度的嚴重制約,以致難以準確把握必要的市場信息,生產經營活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確定性,而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有效對接的重要途徑就是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通過外部市場的內部化,不僅表現為外部收益的內部化,實現了規模經濟,而且還表現為將市場風險和不確定性等外部成本內部化,有效地降低了交易費用。世界農業發展史也表明,農村合作經濟不僅構成了當代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發展重要的組織基礎,而且已成為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標志。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2004年中央1號文件進一步提出了鼓勵發展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具體政策,理論界同樣也是對農民合作組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進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討,并對中國農民合作組織的未來發展充滿樂觀。
2 信用缺失是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最大障礙
2.1 信任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存在的最基礎的資源要素
合作組織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有效的組織形式,主要原因就是將外部成本的內部化,有節約交易成本的利益驅動。信任度與合作績效相輔相成,信任度越高則合作績效越明顯。而目前農村政府信用、社會信用缺失造成的負效應,或增大了農民的交易成本,或讓農民從歷史的博弈經驗中得到不信任的結論,從而抵消了這種組織形式帶來的交易成本的節約,農民的內心不能支持這種合作機制,導致了合作組織在目前信用狀況下的舉步維艱。
2.2 合作組織變異的歷史,使農民不相信合作能帶來效益的機制
合作社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并不是什么新鮮的名詞,早在1956年,我國就有96.3%的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各地也都建立了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化運動從保留農民個人對生產資料股權的初級合作社,發展到廢止私人所有權的高級合作社,當時合作社的實質其實成為一種剝奪農民入社與退社的自主權,對私有財產進行集體無差別占有的集體經濟形式,而后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制度,更是使合作社變異成為一種管理農民的政府機構,這種變異對農民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所以現在的農民受過去合作化運動陰影影響,心有余悸,“恐合”心理嚴重,認為合作化就是集體化,就是剝奪他們私有財產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門在推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往往無視農民的意愿和權利,甚至不惜采取強制的手段“逼合”,農民對此更是非常反感,并由此產生“排合”意識,這就進一步加大了合作化的難度。這種農民對政府政策及行為的不信任,也是基于中國農村發展歷史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障礙因素。
2.3 社會整體的信用缺失,使農民與合作組織管理者之間不信任
中國目前整個社會信用缺失現象十分嚴重,農村亦無可避免,企業與農戶之間存在合同協議履約難,股份合作分紅兌現難的現象比比皆是,據統計,目前農產品商品合同履約率不到20%。而目前由于《合作社法》的缺失,對合作組織的法人地位,以及組織內部的產權形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都沒有原則性的界定和保護,一些以企業或大戶支撐、由企業或大戶主導和控制的合作社就有可能不再是服務小農戶的機構,而成為企業、大戶損害農民利益的手段,因此,合作組織中出現的大戶吃小戶的現象屢見不鮮,而因商販哄抬收購價導致社員不履行合作協議的事情也很常見。這種種的前車之鑒更加深了農戶與合作組織管理者之間的不信任,即使有嚴密的內部管理制度,這種不信任依然會使合作組織的運作成本很高,從而導致合作績效的低下,甚至組織的解體,同時也使更多的農民從歷史重復博弈的經驗中得到不信任的結論,因此而喪失了加入合作組織的積極性,阻止了合作組織的快速發展。
3 面對農村當前低信任度的社會結構,合作組織應首先利用家族信用關系起步
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農民由“不信任”轉為“信任”,亦不是很快就能達到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在社會信用缺失的現狀下,農村的家族信用正取而代之,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信用程度高,信息失真小。因此,在農村當前狀況下,發展合作組織,應該充分利用家族信用關系起步,這樣能使合作組織的資金、勞動力以更低的交易費用取得,同時維持組織運轉的監督成本也會低,這也是目前突破“囚徒困境”的一條捷徑。
在東西方社會制度結構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正如費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一文中所論述的,西方社會是團體格局的社會結構,是以個人為本位的,在這種團體格局下,首先假定了團體的存在,強調個人的獨立和平等,是個人主義的社會結構,因而家庭的概念和含義較為簡單,這種家庭以生育為主要功能,是暫時性的。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及家族利益和聲譽遠遠高于其他組織。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差序格局的,人與人關系的親疏遠近是以自我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圓束,與別人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薄,也愈推愈遠。這種社會格局下家的概念具有極大的伸縮性,可以根據需要沿著差序向外擴大。因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家在結構上是一個氏族,它不僅僅限于生育功能,而是一個事業組織,而且這個意義上的家不僅僅限于親子所構成的小組合,而是依著需要擴大的、長期的、連續性的動態之家。正是因為中國傳統倫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所有的關系都是自己的關系。因而,人們之間的社會信任也以家族主義和泛家族主義為衡量標準,形成了對家族內部的高信任度和對外人的低信任度。人際信任可分為一般信任與特殊信任,所謂一般信任是指對一般人的信任,特殊信任是對有共同經歷、相互熟悉或有特殊關系的人的信任。特殊信任限制了一般信任的發展,而一般信任是構成一國社會資本的主要因素。
如果說企業的成功取決于管理之道,而管理的核心是在企業中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建立在家族血緣、親緣關系基礎上的家族性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企業利益就是家族利益,家族成員就是企業員工,員工在心理上對企業高度認同,互有歸屬感。這一層親情的黏合劑容易使員工與領導之間更為融洽,思想上更容易相通,行動上更趨一致,從而大大降低了協調成本。家族成員之間長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深厚感情和默契關系,也有助于化解企業內部的矛盾,使決策能夠迅速貫徹。不過家族信用仍然有它的局限性,特別是當組織規模很大時,家族成員很難再滿足組織的需要,因此不能死守住家族信用,最終依然有賴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
[1]李紅兵.山東省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問題研究[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
[2]李昆.重釋農業合作社存在與發展的內在動因[J].農業經濟,2004,(1).
[3]盧現祥.論華人企業的家族式管理[J].華東經濟管理,2000,(1).
[4]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