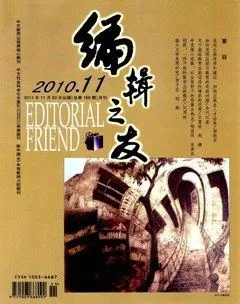對《出版活動與編輯活動的思考》一文的回答
2010年第6期《編輯之友》有篇文章論及本人發表于年初的《試論出版活動與編輯活動的關系》一文(以下簡稱《試論》),作者文章其名《出版活動與編輯活動的思考》(以下簡稱《思考》),該文不長,其內容通篇除了批判本人的《試論》一文而外,并沒見到此君有什么關于出版活動或編輯活動“思考”方面的立論,更兼該文所持邏輯推理或對常識的掌握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本來不打算回應,奈何其文直以本人姓名做題,謂之“商榷”,不予回應看來也不妥當,如此,就做如下回應。
作為編輯學理論研究,有必要首先明確本學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因此編輯或出版概念的探討一直是編輯學理論的熱點。將編輯概念定義為對他人作品展開的社會活動,這是本人關于編輯學立論的基礎,關于這一編輯概念,較完整的闡述見于《中國編輯》創刊號(《中國編輯》,2002.1.),在那篇文章中,筆者提出了認定編輯活動的5個本質特征,其中一個關鍵點便是編輯活動只針對他人作品展開,這不僅是為了明確編輯學的研究對象,也是為了避免“兩種編輯”的是非所致。筆者有關于編輯概念的推出并非空穴來風,實在也有一個長期思考和學習比較的過程,相關的思考和對編輯概念的推導,見于歷年來本人發表的文章中。在這里我既不想,也不可能將這20多年來的理論思考于此一一展示,如果《思考》作者想要了解得更多些,不妨先去讀讀20年來的《編輯之友》《編輯學刊》《出版科學》以及《中國編輯》等相關雜志,希望此君日后發表言論時,最好對所駁斥的言論先做些深入了解,不要那么浮躁,不要那么急切為好。
《思考》作者提出,筆者簡化的“出版活動”概念——“‘將作品通過不同方式向公眾傳播’,這句話很大,似乎真的包容了一切。‘不同方式’,有形的書刊、圖畫、音像制品等方式統統包含在里面,無形的廣播、影視、網絡、手機短信也盡收囊中,是否將未來發展到意識流等看不見摸不著的虛無縹緲的方式也包含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意識流”,也不知道此君所說“虛無縹緲的方式”指的是什么,從何而來,放在這里是何居心,可本人所說的“不同方式”包括書報刊畫、音像影視以至廣播、網絡、手機短信,那是理所當然的,有何不可?他們本來就是編輯活動所必要依據的載體,何錯之有?《思考》作者隨后提出:“如此看來,這個定義不僅是大的問題,而且已經變得模棱兩可、捉摸不定了。”此說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筆者的概念怎么個“模棱兩可”了?是誰與誰“兩可”了?所以,筆者也就終于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讓此君“捉摸不定”了。
在提出了上述莫名其妙的“模棱兩可”和“捉摸不定”后,《思考》作者引據《現代漢語詞典》對“定義”的定義:“對于一種事物的本質特征或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確切而簡要的說明。”繼而提出:“顯然,《試論》給出的‘出版’新定義違背了‘確切’原則,新定義雖大卻無實際意義。”筆者反復誦讀本人的文章,再反觀《思考》作者的“論文”,實在看不出鄙人所見有什么地方“顯然”違背了“確切”原則,難道就是《思考》作者所說的什么“意識流”或是“虛無縹緲的方式”?鄙人的《試論》中何曾提出過什么“意識流”?又不知從何而來的“虛無縹緲”?那本是《思考》作者自己強加于人的東西,自是荒誕不經,《思考》作者自己把自己的荒誕批駁一番,算是什么意思?
《思考》作者對筆者給“編輯”一詞的定義也有意見,說什么:“似乎對自己作品的選擇、審讀和加工就不叫編輯活動了。”對此,筆者不禁要大聲說,“沒錯!”筆者歷來就是這么主張的,有何不可?對此筆者從來就沒有掩飾過,有什么“似乎”不似乎的!《思考》作者接著說,“對于作者自己在傳播作品過程中行使的編輯職能的活動,是否也應該算作編輯活動呢?”對此,筆者又不禁要大聲說,“不算!”這也是筆者歷來主張的,并在《試論》一文中早已闡明備至,難道《思考》作者看不明白?作者對自己作品的“選擇、審讀和加工”,那本是作者所從事的編著、編纂等著作活動,而不是編輯學所涉及的“為人作嫁”的編輯活動。《思考》作者自己全無立論,對別人的批評既不是基于深入了解、準確掌握,也不是建立于符合邏輯的推理之上,不是具體或準確地指出別人的錯謬,而是:“顯然,這一定義片面化了,人為地割裂了編輯活動的內涵……”云云。筆者不幸,又墜入五里霧中,真不知道此君根據什么認為筆者的編輯定義“片面化”,又不知是哪方面片面了?筆者的觀點又“割裂了”“編輯活動”的什么“內涵”?
在論及筆者提出的“出版”比“編輯”概念大時,《思考》作者提出,“我們都知道,說到兩個或多個概念進行比較的時候,前提是它們是可比較的,也就是他們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上位詞跟下位詞的關系。比如,‘人’比‘男人’和‘女人’大,因為“人”是“男人”和“女人”的上位詞;但是“男人”和“女人”能比較嗎?顯然,二者沒有上下位關系,無法比較。”看來,此君認為“出版”和“編輯”是“男人”和“女人”的關系,因此是無法或不應該進行比較的。
先不說“出版”是否可以與“編輯”進行比較,單就此君的所謂“前提”和“二者沒有上下位關系”即“無法比較”的說法就已十分荒謬,難道就沒有或不可以進行同級間的對比?“男人”和“女人”為什么就不能比較?誰規定的比較就只能在“上下位”之間進行?筆者所持“出版”概念比“編輯”概念大的觀點,來自于筆者認為編輯活動必需要借助于出版活動來實現,而完成出版活動客觀上不必需有編輯活動參與,出版活動包括了有編輯活動和沒有編輯活動參與的兩類,從而有出版活動概念比編輯活動大之說;筆者更論及出版活動的產生應當早于編輯活動,因而提出編輯活動應當從屬于出版活動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在比較中產生的,如此,將出版活動比之于編輯活動有何不可?
繼之,《思考》作者又對筆者提出的“出版活動客觀上并不必需編輯活動參與”的認識發表議論,說什么“如果強化出版活動而弱化甚至忽視編輯活動,‘無錯不成書’將成為鐵律。”還引《出版管理條例》“肯定了出版活動中編輯活動的地位。”好像筆者主張出版活動中不應有編輯活動存在,或者,有心要“弱化”或“忽視”編輯活動的重要性。看來此君邏輯思維能力實在有限,他完全分不清客觀與主觀的區別,或者是別有用心也未可知。
筆者實在忍不住要說,《思考》作者的文章簡直不能看,其對本人所持觀點說的是什么都沒搞清楚就一個“顯然”接一個“顯然”、再一個“顯然”,全然沒有邏輯推理,既不建立自己的立論,又不邏輯推理別人如何的不合理,也不知是如何使其說法得以“顯然”的,似乎只要有主張、就“顯然”,不需推理就能駁論,真是荒誕。
本人所持編輯學理論或觀點,均立足于編輯活動必須是“對他人作品而展開”的基本點,任何離開了這一前提對本人觀點的批判或指責都是無理的。事實上,這位《思考》的作者也承認,“如果編輯活動摒棄了作者行使的編輯職能,那么《試論》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好吧,在此,我愿意再次重申,我所論及的編輯活動,就是只涉及非作者本人的、對他人作品而展開的那種編輯活動。因此,《思考》作者撇開這一基點而按照自己理解展開的后續批駁自然也是毫無道理的。
出于好心,我很想告訴這位《思考》作者,今天已經遠不同于20年前,這些年來國內學者已經發表了大量的編輯學相關文章,編輯學理論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或進展,作為后來者,最好多讀點相關的書尤其是編輯學期刊,對有關理論有了起碼的了解后再發議論較好,不要那么浮躁,讓人覺得你淺薄。
最后想告訴這位“期刊編輯工作的新手”,理論探討本是平等的,也無甚高深,無需“斗膽”,只要符合邏輯,言之有理,直述可也;其次想告訴這位閣下,好歹你也算個編輯,本人健在,尚不敢被恭稱作“先哲”,日后再做文章,恐怕還是查好字典再下手為好,以免貽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