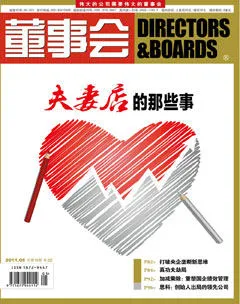陳曉兵敗治理規則
董事會否決股東大會決議這樣的情況是極其罕見的,因為這已經涉嫌違反公司法。敢于違反公司法的人,能說是敗于“天命”嗎?
2011年3月9日,在國美董事局主席職位上打拼了三年多的陳曉黯然離開了國美總部所在地北京鵬潤大廈,至此,持續了七個月之久、轟轟烈烈的“國美內戰”——“黃陳之爭”,終于以陳曉的黯然離職畫上了句號。
對于陳曉的去職,很多人認為,陳曉敗于“天命”,輸在不懂“民情”:在中國這個重視傳統道德而沒有太多現代商業傳統的社會,陳曉一開始就背負著道德的十字架在戰斗,情何以堪? 筆者認為,這種理解完全不懂現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規范,陳曉不是敗于“天命”,不是輸在“民情”,而是輸在不懂現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規則。
現代公司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所有者不直接經營公司,經營權交給職業經理人。所有者為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經理人侵害,會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即董事會來監督職業經理人。但所有者與代理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代理人也存在著欺騙所有者的道德風險,于是就有公司重大決策,比如董事任免、公司合并、章程修改、經理層股票期權計劃等,由股東(大會)來決定的制度安排,尤其對于董事,股東都會要求他們對自己必須盡忠誠義務。這種制度設置的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現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規范,各國公司法在這方面的規定是大同小異的。之所以要如此保護股東利益,是因為股東在整個公司構架中可能處于最不利的地位。
這里不妨列幾個陳曉背離公司治理基本規范的例子:
例一,2009年5月11日,在國美年度股東大會上,機構投資者貝恩資本提出的三位非執行董事的任命沒有通過。當晚,董事會主席陳曉主導的國美電器董事會緊急召開董事局會議,以“投票結果并沒有真正反映大部分股東的意愿”為由,否決了股東投票,重新委任3名前任董事加入董事會。了解公司治理發展史的人想必都很清楚,董事會否決股東大會決議這樣的情況是極其罕見的,因為這已涉嫌違反公司法。敢于違反公司法的人,能說是敗于“天命”嗎?之前黃光裕時代有股東大會對董事會任命董事的授權,但這種授權本身就是違反公司法的,陳曉不能將錯就錯,更何況貝恩資本進入國美是附有極苛刻條件的。
例二,2009年7月7日,陳曉主導的董事會推出“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獲得股權激勵的經理人員包括分公司總經理、大區總經理,以及集團總部各中心總監、副總監以上級別,共有105人。如此規模龐大的股權激勵計劃,董事會是無權決策的,決策權只能屬于股東大會,因為股權激勵屬于分配股東利益之重大事項。即使有股東大會的授權,這種授權也是錯誤的,因為該項股權激勵涉及范圍太大,而真正意義上的股權激勵是一項“激勵性”而非“福利性”的制度安排,故而它只會授予CEO等極個別高層經理人。如此大規模的股權激勵,無疑與股東利益相悖。這就無怪乎黃光裕家族質疑陳曉之行為是在“慷股東之慨,盲目給部分管理人員期權,變相收買人心”了。
例三,陳曉完全不理會(可能根本不懂)CEO和董事會主席的重大區別。陳曉在擔任董事會主席之前是國美CEO,如果他不做董事會主席,而仍是CEO,那么他在擔任董事會主席之后的很多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CEO代表的利益主體就是自己,他當然要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問題恰恰在于,他辭去了CEO而擔任了董事會主席,此時作為董事,而且作為董事會的召集人,他代表的利益主體就不是自己,而是代表以股東為核心的各利益相關者了,他所謀求的應該是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為什么現代公司治理強調董事會主席(董事長)和CEO(總經理)要分開了。然而,陳曉的所作所為卻完全不像董事會主席所為,卻更像CEO所為(當然,CEO也不能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