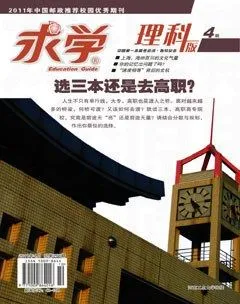我與《求學》的青春歲月
從高中時閱讀《求學》雜志,到大學時為《求學》投稿,到榮幸受邀參加《求學》第二屆作者筆會,再到與《求學》各位編輯成為朋友……《求學》一路給予了我眾多非常精彩的記憶,讓我深感與《求學》結緣的幸運。
南寧,是我與《求學》的第一緣分之地。在那次南寧筆會上,我見到了來自各地的專家和優秀學子,并熟識了敬業的《求學》編輯。幾天的相處中,從討論會到聯歡會,從飯桌到海邊,讓我這個不喜關注外在世界而且話不多的悶人,也被感染得熱烈起來,與大家結下了難忘友誼。還記得在北海夜幕下的沙灘上,聽著風變換著性格,看見水變化著顏色,迎著幾米高的浪墻迎頭撲下來,在人群懼這英雄般氣勢而逐漸退到淺水區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卻手拉著手,往更深的地方走去,無所顧忌地歡笑著,暢快著呼喊這青春友誼。
北京,是我與《求學》的另一緣分之地。在參加完筆會后,我很快就研究生畢業,在北京某單位工作。那次北海之行,有北京名校的學生參與,所以我們算是熟識了,并隨后在北京屢次聚會,在他們身上我學習到了很多。《求學》考研版編輯部也位于北京,而我工作的一部分涉及到出版業務,通過當面與電話請教主編等人,讓我這個外行人心中明晰了思路,之后得到迅速提升,因此感激非常。又聽聞幾位筆會朋友也來到北京工作,有進入央視的,有進入銀行的;之后,幾位熟識的《求學》編輯調入北京,我為大家能再次相聚而深感興奮。
話說,一日聽聞兩編輯派駐京城,乃電話致以深切關懷,并建議小酌一杯,才能體現吾等于新時代之光輝友誼。隨后左轉巷,右進廊,直撲一麻辣名店。三人歡欣鼓舞,把酒各問東西,共話革命友誼,閑話且不細表。
酒酣耳熱之際,我乃大膽請求探訪編輯部,乃獲準許。于是按捺心中激動,速去也。是夜,月色黑風聲高,昏黃路燈也撲棱撲棱閃著詭異光芒;行人投來似疑眼神,隨即又匆忙沉默走過;路邊攤主有氣無力叫賣著,聲音幾乎若干世紀般遙遠。吾等三人一閃而過,奔上大樓,在搖曳樹影中摸索至某暗門旁,掏出一把尖物,仔細一看才知是鑰匙。打開門,按開燈,忽眼前大亮,嗬,好一個溫馨編輯部!
只見編輯部分兩室,皆鋪甚有品質之暗紅木地板。外室靠門處立一暗紅色書架,上列眾多相關書籍及各種雜志;中擺一靛黃木合板桌,隨意陳放些翻開雜志。從靠窗處起,于墻兩邊分列若干電腦桌椅,上有工作電腦及個人私物。乃入內室,且見立柜及另外兩列電腦桌,案上厚重文稿透漏日常繁忙。
看著各位編輯的工作地方,想著當年心中的神圣雜志,今日終得有緣一見其根據地,慨嘆不已。作為被高考影響甚大的一員,深知高三(高中)幾乎是已有人生中最枯燥和最沉重的一段,雖然對比于日后大學和社會生活還是很簡單,但不可否認它是人生重要的分水嶺。《求學》,作為最知名和最受歡迎的高考雜志,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學子的成長。
和兩位編輯的交談中,得知近年來《求學》在內容風格上勇于變革,例如狀元訪談等欄目深受高中生歡迎,我心中為其發展和成長感到很高興。我也結合自己的學習和工作經驗給出了部分建議,希望能給《求學》的發展增添一份火。
離去之前,看見某桌上有一家庭照片,三人細觀而后稱嘆其工作之余不忘家庭。可我想,《求學》最令人感動之處不也是如此嗎?她時刻記掛每個讀者,她努力讓每篇文章都細致吻合讀者需求,正是這種溫情和責任鑄就了她今日作為高中學子良師益友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