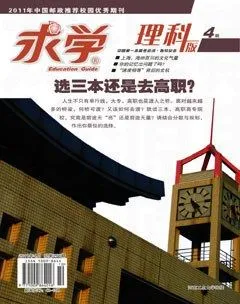天津大學(xué)——兩代人的天大情懷
1988年夏秋之交,我收到了天津大學(xué)的入學(xué)通知書,通知書上寫著學(xué)校的簡介:“天津大學(xué)的前身是北洋大學(xué),是我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學(xué),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的開端。天津大學(xué)是中共中央首批確定的16所國家重點大學(xué)之一……”
當(dāng)時,我的心情無比的激動,為自己能躋身于渤海邊的這所百年名校就學(xué)而深感榮幸。
踏入天津大學(xué)校園后,我深為這所大學(xué)的美麗而震撼。水,最能體現(xiàn)一個地方的性靈。這里的湖水之多,至少是北方高校之最。開學(xué)時是初秋時節(jié),湖中油油的水草,搖曳著秋光,令人心曠神怡。
天大有四個湖,分別名曰:“敬業(yè)”、“青年”、“友誼”、“愛晚”。除了“愛晚”尚有古韻遺風(fēng),其他三湖的名字都給人一種質(zhì)樸向上之感。雖然青年湖面積最大,但我一直認為敬業(yè)湖才是天大的四湖之首。薪火相傳的天大精神,從來都無關(guān)風(fēng)月,就如同“敬業(yè)”兩個字,質(zhì)樸而深沉。瀲滟的湖光,映照著湖畔諸多的苦讀身影,清風(fēng)徐來,伴隨著書聲瑯瑯。敬業(yè)湖被天大圖書館和北洋廣場,及各專業(yè)教學(xué)樓包圍,路過敬業(yè)湖的人都在匆匆地趕去實驗室,或去教室,或去查閱書籍資料,仿佛無心于敬業(yè)湖的景色。其實正是這些醉心于學(xué)問的人,浸潤了敬業(yè)湖的風(fēng)骨,蘊涵了天大孜孜不倦之精神。
白天的課余時間,我喜歡在湖畔讀書。湖水清且漣漪,致我學(xué)海無央。常常想,老校友徐志摩(曾是北洋大學(xué)法科生)筆下《再別康橋》中的康河,也該和眼前的湖景一樣迷人吧。當(dāng)晚霞在西天燃盡、夜幕降臨后,我就戀戀不舍地離開湖邊,背上書包進入圖書館的閱覽室讀書了。四年的大學(xué)生活,都是這么過來的。那年月,讀了多少書啊,至今為當(dāng)年沒有虛度光陰而欣慰和自豪。
在湖邊,我的讀書生涯分為兩大底色,一是苦讀,這個是主色調(diào)。二是樂讀,這個是調(diào)劑性的。所謂樂讀,就是快樂地讀書,一書在手,聯(lián)想翩翩,精鶩八極,心游萬仞。有時端坐于湖邊的長椅上,將書展放于膝上,風(fēng)吹哪一頁,就看哪一頁,不亦快哉!人生如斯,夫復(fù)何求?
當(dāng)時我們系給我們授課的老師,大都是學(xué)富五車的學(xué)者教授。
古漢語老師是施向東教授,他在古漢語尤其是音韻學(xué)方面造詣很深,其著作《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與唐初中原方音》曾獲得首屆王力語言學(xué)獎。施向東教授授課時一絲不茍之嚴謹,對我影響很深。
古代文學(xué)老師是羅德榮教授,他專注于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兼任中國金瓶梅學(xué)會理事、中國水滸學(xué)會理事、天津市紅樓夢文化研究會秘書長等學(xué)術(shù)職務(wù),發(fā)表論文、論著約140萬字。羅德榮教授講課從不說教,喜歡結(jié)合現(xiàn)實語境闡述古典作品。記得當(dāng)時他給我們講晚唐詩人許渾的《謝亭送別》:“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fēng)雨下西樓。”這首詩時,說他大學(xué)剛畢業(yè)時曾遭遇人生之不幸,被下放到一所很偏僻的農(nóng)村中學(xué)去教書,人生況味無以名狀,常有“滿天風(fēng)雨下西樓”之感。一下子就讓我們加深了對這首詩的理解。現(xiàn)在我每遇到人生不如意之事,頭腦中就會冒出羅老師講的這首詩來。
美學(xué)老師是潘克明教授,他是國內(nèi)曹禺戲劇研究的權(quán)威人士之一,曾出版專著《曹禺研究五十年》等。潘克明教授講課風(fēng)趣幽默,課堂上常常引發(fā)爆笑,使我們在愉悅中不知不覺地就掌握了很多知識。
給我們影響頗深的老師還有幾位,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教育家梅貽琦曾說:大學(xué)之大,并非有大樓也,乃有大師也。能在這些卓有建樹的老師的門下得以求學(xué),實乃人生一大幸事。
就在大一那一年,也就是我18歲的那年冬天,我突然覺得自己真正長大了。
一個風(fēng)雪后的清晨,我站在學(xué)校的青年湖邊,迎著凜冽的寒風(fēng),對幾個同學(xué)說:“我要去看看香山。”
同學(xué)們都極力反對。說要去也應(yīng)在深秋去啊,那時香山的景色最美。
為什么非要選擇在深秋?為什么不能選擇在冬季?我執(zhí)意要去看看冬日的香山,看看風(fēng)雪中是楓樹是怎樣的一種風(fēng)采。或許這是一種更美的風(fēng)景,它能讓人體味無窮的真實……
就這樣,我?guī)Я艘槐竞C魍摹独先伺c海》,一個人去了香山。站在冷風(fēng)呼嘯、殘葉飄零的山坳里,我突然意識到,人生百味,皆須我們?nèi)テ穱L。任何悔恨和失落,最終都將隨著時間的流逝消融在你的生命里,就像那殘落的樹葉終將融進大地,變成養(yǎng)料,滋潤著每一棵成長的大樹一樣。
此時,我又仔細地翻看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深為主人公的精神所感動。它告訴了我,失敗與成功并無界限,生命的意義在于無止境的奮斗之中。
那年冬天,學(xué)校廣播里老在播放著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是誰在車上憂郁地低聲唱,唱歌的是那趕車的人。我很喜歡聽這首歌,常常為馬車夫苦中作樂的精神所感動。確實,一年四季,誰能總生活在多姿多彩、果實累累的秋季?既然無法避免,那就讓我們?nèi)ビ赂业赜语L(fēng)雪,在颼颼冬風(fēng)中去塑一楨冷冷的風(fēng)景。
正是從那時起,我突然覺得自己的人生觀初步確立:向著目標(biāo),風(fēng)雨兼程。無論有多少風(fēng)雨,在風(fēng)雨中高舉自己的旗!
而今我已年屆不惑,但于母校天大形成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始終在指導(dǎo)著我,母校的光輝也始終溫暖著我,照亮了我的前程,使我有了頑強的意志與磐石般堅韌的毅力,能夠從容克服困難,一直行走在柳暗花明的歲月長堤,無限美好的人生正向我展開……
在我畢業(yè)告別天大校園整整十八年后的2010年7月,我17歲的兒子又考入了天大。一晃十八年,父子成校友!而且,我當(dāng)年所讀的人文系,正是兒子現(xiàn)在上的文法學(xué)院的前身。
兒子的專業(yè)是法學(xué),天大法學(xué)的歷史可上溯到前身北洋大學(xué)的法科。北洋法科是北洋大學(xué)1895年初創(chuàng)時期即設(shè)立的4個專業(yè)之一,有“近代中國的第一個法律教育機構(gòu)之稱”。1903年北洋大學(xué)堂法科課程中設(shè)置“法律學(xué)原理”一課,被視為中國現(xiàn)代抽象法學(xué)理論專業(yè)教學(xué)和研究的開端。北洋法科培養(yǎng)出的杰出校友不勝枚舉: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廣州起義總指揮張?zhí)祝恢▽W(xué)家、大教育家趙天麟;近現(xiàn)代中國法學(xué)的奠基者、第一個擔(dān)任聯(lián)合國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的中國人、曾任民國總理的王寵惠;著名詩人徐志摩;中國的比較法學(xué)科創(chuàng)始人、著名法學(xué)家吳經(jīng)熊;曾任民國外交部常務(wù)次長、聯(lián)合國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國際法學(xué)會副會長的徐謨……在如此深厚歷史積淀的專業(yè)進行深造,我為兒子自豪與驕傲。
父子變成了學(xué)兄學(xué)弟,是人生一大幸事。母校天大是我的精神家園,它賦予了我太多的東西。想必兒子在這里學(xué)習(xí),收獲一定不會比我當(dāng)年少。曾記得,當(dāng)年我每晚上自習(xí)都要早點去教室或閱覽室,否則就很難占到座位,兒子電話中告我現(xiàn)在更是如此。歲月流逝,滄桑不改天大人的好學(xué)情懷。
天大學(xué)風(fēng)之好,在全國高校中很有名。這也是我堅持讓兒子報考我的母校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兒子學(xué)習(xí)很有積極性,對這個專業(yè)情有獨鐘,樂此不疲。他已經(jīng)開始著手寫一部關(guān)于法學(xué)普及性的書籍,已經(jīng)寫好了幾萬字,計劃大二時就要出版。他還參加了好幾個社團,在校內(nèi)十分活躍。在兒子的身上,我看到了當(dāng)年的自己。
江山代有人才出,江花江草處處鮮。但愿兒子在我們共同的母校能學(xué)到更多的東西,但愿他將來能超過他的老爸!
作者介紹:劉繼興,作家,文史學(xué)者,資深傳媒人,1992年畢業(yè)于天津大學(xué),在文、史、哲以及美學(xué)、傳播學(xué)等領(lǐng)域均有建樹。共發(fā)表各類作品600余萬字。著有《劉繼興讀史》、《魅力毛澤東》、《歷史的迷蹤:你所不了解的歷史真相》等近10部作品,即將出版的書有《民國之艱難締造》、《毛澤東軼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