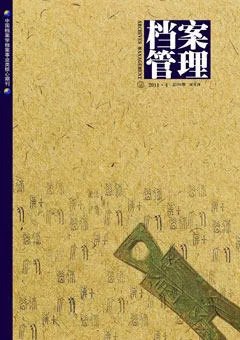《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檔案法》的影響研究綜述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頒布實施以來,其與《檔案法》之間存在著諸多“不和諧”之處,嚴重阻礙了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進程。本文對已有的關于《條例》對《檔案法》影響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并進行了適當的歸納和總結。
關鍵詞:條例;檔案法;影響;理念;制度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作為一部行政規范,要想全面貫徹執行,必須注意與相關法律法規相協調。但從現實頻頻發生的“政府信息公開案”來看,《條例》與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檔案法》并沒有做到“和平共處”。此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政府信息公開進一步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條例》對《檔案法》的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成為檔案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綜觀目前已有的討論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的立法理念和制度設計兩個方面,故筆者擬重點對這兩個方面進行綜述。
1 《條例》與《檔案法》立法理念的比較
政府信息公開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歷史潮流,是社會進步的象征,因此,在立法理念上,《條例》與《檔案法》相比,必然是前者更加先進,更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目前,檔案學界對此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以及對公民私權的維護兩個方面。蘇州大學黃南鳳、蔣衛榮認為:《條例》重在“公開”,而現行《檔案法》的立法宗旨則傾向于“管理”與“保密”,并建議《檔案法》在總的立法原則上應該體現《條例》的立法精神: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1]蕪湖職業技術學院薛春瑞認為:以開放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不僅符合信息利用的規律,也是現代社會對信息利用的需求以及實現公民知情權的需要。政府信息公開是常規,不公開是例外,這個基本原則確立本身,是一個觀念上的巨大變化。[2]黑龍江大學的焦靜指出:《條例》雖未明確表述,但實際間接肯定了“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通過對《檔案法》相關條款的分析可知其以保密、保護為原則,以開放為例外,與《條例》所追求的立法精神不相容。[3]
另一方面,在政府信息公開的環境下,一些學者還從維護公民私權的角度對《檔案法》提出了異議。安徽省濉溪縣行業辦的王永菲認為,《條例》的實質就是基于公共利益,而非某些單位或團體的利益來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以規范政務信息公開的內容范圍、程序、方式、時間,從而實現政府信息公開的規范化,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4]山東大學曾凡斌認為,《條例》對公開主體義務及公眾權利的規定充分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思想……而《檔案法》在檔案權責制度的設計上缺乏對于國家檔案館權利、義務的制衡機制,致使檔案館中以民為中心的民主思想普遍欠缺,公眾在檔案利用中并沒有享受到應有的權利。[5]
總的來看,檔案學界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檔案法》所體現的立法理念已不符合時代潮流,而應被《條例》中彰顯的新理念所取代。但筆者認為,這種“取代”的可行性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因為政府信息和檔案畢竟是兩種不同的事物,二Hm0mrl0znHzN2S017KorZ/QElzeuLi0k1MngEqjEk2g=者的區別還是十分明顯的,且檔案工作也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條例》所體現的先進理念并不一定完全適合《檔案法》。
2 《條例》與《檔案法》在制度上的沖突
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利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二者在理論基礎和實際操作層面有著內在的聯系。因此,目前,《條例》與《檔案法》在制度上的沖突主要體現在開放利用工作上,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開放時間、開放范圍、救濟措施等幾個方面。
在開放時間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檔案法》規定的30年的封閉期十分不合理。如,中山大學陳永生教授認為,待歸檔保存一定年限移交檔案館后,反倒要經歷“形成滿30年”的考察,從邏輯推理上似乎具有諷刺意義,從現實執行上似乎也存在程序矛盾;[6]安徽農業大學劉社文認為,我國對檔案開放期限的規定弊端已明顯暴露,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因而,應調整檔案開放期限,更加注重檔案的開放時效。[7]福建師范大學的羅灤、楊立人,上海大學的潘玉民更進一步提出,《檔案法》應取消對政府信息的機關檔案開放期限限制,即時向社會開放;[8]徐州市檔案局的董近東、王曉燕提出:各級國家檔案館對于進館前已經由機關檔案部門標注開放檔案,進館后應該直接向社會提供利用;對于進館前未開放的檔案,根據有關檔案開放控制的法律規定到期予以劃控,向社會開放。[9]而浙江省檔案局理明卻持不同看法,他從封閉期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目前的國際慣例兩方面,說明了檔案設置30年封閉期與政府信息公開并不矛盾,并進一步認為,政府信息公開查閱場所建設是對檔案封閉期制度的有效補充和最好保障。[10]
在開放范圍問題上,無論是主體范圍還是客體范圍,學界普遍認為,《檔案法》所規定的范圍都過于狹窄。開放檔案客體范圍狹窄的主要原因是檔案密級的限制過高。四川大學王瑋認為,一旦現行政府信息成為檔案,被確定密級,就成為國家秘密,不能對外公開;即使到期能夠對外查閱,但是可能因為許多特殊原因而不能對外公開,而且,這些理由沒有固定的標準,是一個容易產生恣意行政的漏洞。[11]薛春瑞指出,《條例》對檔案開放的范圍具有一定的沖擊作用,政府信息文件一旦歸檔后成為檔案,政府檔案是政府政務信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應和檔案開放的范圍相一致。[12]中山大學李揚新提出,檔案開放的客體范圍應該針對“法定公開”的政府文件進一步明確、擴大和細化。[13]對于檔案開放的主體而言,《檔案法》規定的檔案開放的主體范圍僅限于各級各類公共檔案館,這在強調信息公開的大環境下,顯得過于保守。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擴大檔案開放主體范圍的建議,其實質就是認為機關檔案室應納入政府信息公開主體的范疇。安徽農業大學劉社文認為,《條例》實施后,已有的法律法規僅賦予國家檔案館具有分批向社會公布檔案和開放檔案目錄的職責,沒有賦予機關檔案室開放檔案的職能,顯然是不合時宜的。[14]薛春瑞和安徽農業大學圖書館的吳文革也同樣持此觀點。
《條例》頒布實施之后,其中,有整整一章關于“監督和保障”公民信息權利的內容,與《檔案法》形成鮮明對比,因此,這一問題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四川大學王瑋指出,對申請人面對不予公開行為獲得救濟的情況沒有任何程序上的設置,這樣就造成一個結果,行政機關可以自由決定公開還是不予公開,反正沒有審查程序。[15]中山大學李揚新認為,開放保障條款中,也應該明確各類開放機構的責任主體和監督主體,規定具有開放義務的組織機構必須設立常設機構和配備足夠人員,負責延期開放檔案的清理鑒定、到期檔案的登記開放、申請開放的答復處理等工作。[16]黃南鳳、蔣衛榮認為,檔案開放制度可以適當增設“到期尚未開放檔案,可以依申請方式開放”這樣的法律規范,詳細規定申請程序、接受申請的“責任者”、答復申請的具體時間及內容、方式等。[17]
3結語
綜上所述,學界對于政府信息公開對《檔案法》的影響有著較為深入的認識,且絕大多數學者已基本達成一致:即《檔案法》應適時做出一些適當的調整,以順應政府信息公開的時代潮流。絕大多數學者都指出了《條例》與《檔案法》的不協調之處,大到立法理念,小到具體條款,應該說,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探討,也讓學界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這只是第一步,解決問題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今后,學界應在如何在實踐中化解這些不協調之處著力,從實際出發,結合檔案和檔案工作的特殊性,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爭取能夠為實踐工作提供實在的指導。
參考文獻:
[1][17]黃南鳳、蔣衛榮.從《條例》的立法理念看《檔案法》修改[J].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