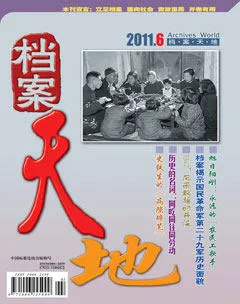傅斯年與臺灣大學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豐。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他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
在近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他不僅是歷史學家、教育家、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一生還富有傳奇色彩。尤其傅斯年在擔任臺灣大學校長期間,給他帶來很多美譽!
一、傅斯年當初去臺灣大學時徘徊不定
三個戰役后,蔣介石精銳盡失,他看敗局已定便開始著力經營臺灣。而臺灣大學校長莊長恭到任不到半年,一來感到臺灣大學人事政務難以處理,二來不愿意長期留在臺灣,乃悄然離職攜眷返回上海,讓杜聰明代理校長。國民黨當局為安定臺灣,權衡再三,決定讓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于1948年8月從美國治病回國,臨行時美國主治大夫特別叮囑其回國不要擔任繁巨行政職務,如果操勞過度,高血壓病很容易復發,后果將不堪設想。傅斯年回國不久,就開始為主持史語所及其重要文物遷臺事務而東奔西走,身體已感不堪承受。當教育部長朱家驊要其出任臺灣大學校長時,傅斯年立即嚴辭拒絕,但朱家驊并沒有改變決定,親自找傅斯年晤談,又讓傅斯年的幾位朋友輪流規勸游說,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強接受了任命,但并沒有前去上任,仍處于徘徊狀態。
1948年元旦之夜,傅斯年與胡適聚會共度歲末,兩人置酒對飲,相視凄然。一面飲酒,一面談論時局,盡管兩人都是民主人士,但與國民黨政權關系較為密切。他們目睹國民黨政權軍事慘敗,政治孤立,既痛恨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又為自己的前途命運擔憂。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戀鄉土之情頓生,思前想后,兩人都十分傷感,不禁潛然淚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時,臺灣有關人士函電交加催促其迅速上任。莊長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辦理交接手續。杜聰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別致電、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駕,蒞校主持。陳誠與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須認真考慮的,傅斯年平時辦事以干脆,有決斷著稱,這次因關系他個人后半生的前途命運,所以格外慎重。他將自己關在一個房間,三日三夜未出房門,繞室踱步,反復吟詠、書寫陶淵明《種桑長江邊》的詩句,考慮去留問題,最后決定暫且去臺灣就職,但仍懷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帶全家去臺灣,并且已買好了機票,臨時決定,把部分親屬留下,退掉了機票,對他們說:共產黨對文人還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來,臨行又把許多圖書、家產留了下來。1月19日,傅斯年只攜帶部分親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飛機去了臺灣。次日到臺灣大學就職,并繼續兼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職務。
二、傅斯年大力整頓臺灣大學的各種弊端和克服各種困難
臺灣大學歷史淵源頗深,它是日本占領臺灣時期于1928年建立的,原名日本臺北帝國大學。日本建立此學校的目的是對臺灣人進行奴化教育,所聘用的教職人員多是日本人,其管理和教育都是采用日本模式。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11月由中國接收,改名國立臺灣大學,由羅宗洛出任校長。由于日籍教師大部分撤走,師資缺乏,再加經費困難,羅宗洛任職不久辭職,其后陸志鴻、莊長恭繼任,三人任職長的不到二年,短者僅數月。臺灣大學在日本人撤退時,就是一個爛攤子,接收重建以來,校長頻繁更換,沒有得到很好治理,傅斯年就任時,學校內部管理一片混亂,外部臺灣政局動蕩,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屬大量撤往臺灣,其中許多大、中學學生被裹挾去臺,要求入學就讀的學生驟然增加,學校難以容納。傅斯年就任后決心全面整頓,其整頓和改革內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積極羅致人才,整頓教師隊伍。傅斯年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對高校中師資的地位有深刻的認識,日籍教師撤離后,臺大教師很少,又因臺灣窮僻之地,與大陸有海面相隔,局勢又不穩定,大陸學者教授一般不愿赴臺任教,故高層人才奇缺。而同時,大批軍政人員撤至臺灣,許多人官場失意,欲進入臺大任教,也有一些政府官員由于各種原因想到臺灣大學兼職,而這些人多是學無專長,僅依仗權勢或輾轉請托謀求教職。傅斯年針對這種情況,排除種種干擾,堅持以才學取人,對各種請托嚴加拒絕。他曾對各界公開聲明,聘任教師只注重學術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不考慮其他因素,堅決不接受因所謂積極反共或官場失意的賢士到臺大任職,他說:“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為忠于職守而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為臺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
由于傅斯年到任時臺灣大學師資十分缺乏,為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和學校名望,傅斯年利用仍兼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特殊條件,聘用了研究所的一些專家學者到臺灣大學教課。如著名學者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高去尋、石璋如、王叔民等都曾受聘到臺大任教。傅又利用自己在學術界的聲望從大陸各地羅致和吸收了一批知名學者,如歷史系的劉崇宏、方豪、陶希圣,中文系毛子水、屈萬里,哲學系方東美,外文系英千里、趙麗蓮,化學系錢思亮、張儀等,這些人皆學有專長,在各自的學科領域頗有建樹。再加上原有教授,臺灣大學在不長的時間內成為師資隊伍陣容整齊的綜合性大學。
其二,嚴格實行考試制度,杜絕人情,擇優錄取學生。在臺灣光復之初的幾年里,臺灣大學由于日本人撤退以后許多管理制度、章程都廢除了,新的規章制度沒有建立,所以教學管理十分混亂,招生考試馬馬虎虎,請托作弊現象嚴重,學生良莠不齊,許多學生只要考得入學資格便萬事大吉,吃喝玩樂,不認真學習,學校也不管不問。傅斯年有一個傳統的觀點,就是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一定要把好學生吸收到學校,再經過嚴格教育,使學生德才兼備,學校的責任是向社會輸送合格人才。因此,他到任后,首先從嚴格招生考試入手,把好錄取學生的關口。而做到這一點,有相當大的困難。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工商學界攜眷赴臺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學就讀,再是由于戰亂,流亡臺灣學生眾多,而臺灣大學是臺灣惟一的國立大學,自然是青年追逐的首要目標,故臺大招生的壓力很大,許多權要試圖用不正當的手段把子女送到臺大,大大增加了臺大招生、管理方面的混亂。
1949年夏季是傅斯年到任后第一次大規模招生,為保證學生質量,傅斯年在校刊公開發表文章,宣布招生辦法,他說:“這次辦理考試,在關防上必須嚴之又嚴,在標準上必須絕對依據原則,毫無例外。由前一說,出題者雖有多人,但最后決定用何一題,只有校長、教務長知道,這是任何人事前無法揣到的。印題時,當把印工和職員全部關在一樓上,斷絕交通,四周以臺北市警察看守,僅有校長與教務長可以自由出入。考題僅在考試前數點鐘付印,考試未完,監守不撤。……錄取標準決定之前,不拆密封,故無人能知任何一個人之分數及其錄取與否。”他著重聲明,自己一定秉公辦事,決不會循私舞弊,并要求大家進行監督,他說:“假如我們以任何理由,答應一個考試不及格或未經考試的進來,即是我對于一切經考試不及格而進不來者或不考試而進不來者加以極不公道之待遇,這對于大學校長一職,實在有虧職守了。奉告至親好友千萬不要向我談錄取學生事,只要把簡章買來細細的看,照樣的辦,一切全憑本領了。我毫無通融例外之辦法,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辦法,應由政府或社會予以最嚴厲制裁。”傅斯年說到做到,在錄取學生階段,又在校長辦公室門旁用毛筆赫然寫一個條幅:“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由于傅斯年制定了一系列招生制度,又帶頭嚴格執行,使1949年招生順利進行,基本上剎住了請托、說情、走后門等不正之風。
這種嚴格的招生制度,杜絕了許多弊端,對于扭轉臺灣大學校風和學風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其三,對學生嚴格管理。傅斯年采取種種措施嚴格考試錄取制度,只是保證優秀學生能夠被錄取,有求學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對學生進行教育,為學生學習創造優良的條件和環境,在這方面傅斯年也采取了許多措施。
一是修定臺灣大學“學則”,改變學生不努力學習,隨意曠課,混資格、混文憑的現象。其主要措施是實行學分制,嚴格學習期間的考試制度,杜絕各種形式的作弊行為。如規定“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一,不得補考,即令退學”。“凡曠考者以零分計,全部曠考者,自然退學”等。傅斯年說到做到,1949年第二學期結束,因成績不合格退學者多達31人。被勒令退學的學生家長有不少是有權勢者,子女被勒令退學,他們十分不滿,想方設法向學校發難,有人在省參議會上對傅斯年提出咨詢,給其施加壓力,迫其讓步,傅斯年堅決不肯讓步。
二是設置各種獎學金、助學金,為貧困學生創造學習條件。傅斯年在教育上有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教育機會均等,從早年他就一再強調貧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機會應是均等的,雖然他自己也認為這個理想在當時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應以多設獎學金的方式幫助出身貧苦的優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學的機會。他任臺灣大學校長時更是努力實現這一理想,在臺灣大學設立幾種獎學金、助學金,并做了許多具體規定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傅斯年在致學生的公開信中曾特別強調:“諸位中要想鬼混的,休想政府的幫助,其用功而有優良成績的我決不使他因為無錢而輟學。”
三是解決學生住宿問題,在傅斯年任校長以前,臺灣大學內沒有學生宿舍,個別需要住宿的同學在校外租房居住。傅斯年出任校長時,因各種情況流亡到臺灣的窮學生相當多,他們住不起校外的公寓,只好在學校內尋找棲身之處。研究室、教室乃至洗澡間,到處都住有學生,甚至臺大醫院傳染病房,也成為學生宿舍。傅斯年面對這種情況,實在是既心疼又頭痛,不解決學生住宿問題,學校簡直無法再辦下去,要解決又談何容易。傅斯年曾經聲稱:“我們辦學,應該先替學生解決其所有之困難,使他們有安心求學的環境。然后才能要求他們用心勤學。如果我們不先替他們解決困難,不讓他們有求學的安定環境,而只要求他們努力讀書,即是不近人情的。”他奔走呼吁,四處求告,終于籌集了一大筆資金,加緊建造了一批學生宿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解決了1800多名學生的住宿問題,占全校人數的60%,整個學校學生住宿問題大為緩解。
傅斯年曾在臺灣大學校刊第56期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幾個教育的理想》。其中第一個理想是崇尚“平淡無奇的教育”,在其中強調了三個原則,第一,協助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第二,加強課業。第三,提倡各種課外娛樂的運動。他概括說:“以上的話,總括起來,可以說一句笑話:‘有房子住,有書念,有好玩的東西玩。’”
三、傅斯年注意人格獨立極力爭取教育的相對獨立
傅斯年早年就主張教育獨立,強調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政府不應過多地干預。他一再強調:教育不獨立是辦不好的。他出任臺灣大學校長以后,更是積極爭取和努力堅持教育獨立,反對政府對教育過多地干預。
他任職期間,整個臺灣相當混亂,國民黨政權為了鞏固在臺灣的統治,實行白色恐怖,亂捕亂殺,稍有嫌疑,就有被逮捕屠殺的危險。對臺灣大學也是如此。傅斯年到任不久,臺灣發生了學生運動,臺灣當局大肆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傅斯年對當局不經任何手續到臺灣大學逮捕師生十分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進行交涉,要求沒有確鑿證據不能隨便到臺大捕人,即使有確鑿證據逮捕臺大師生也必須經校長批準,并且相約成為一項制度。有文字記載,蔣經國當時曾負責軍警特憲事務,他要臺大某人資料對某事調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專門寫信要求。信中說:“孟真先生道鑒:茲派員前來洽取于某有關文件,即請面交帶回,以供系考。”當時人的一些書信和回憶文章都說明,軍警憲特到臺大不能肆行無忌。傅斯年力爭此項權力是他堅持教育獨立,擺脫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項重要舉措。
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要求各機關學校實行聯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員幾人相互監督,相互保證對方思想純正,沒有染上共產思想,萬一發現聯保中有人思想不純正,保證人都要受連累。臺灣省當局也要求臺灣大學師生辦理這種手續。傅斯年出面對國民黨當局說:凡是在臺灣大學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他一個人可以保證,有問題發生,他愿意負全部責任。結果臺灣大學沒有實行聯保制度。當時有些人攻擊臺灣大學有些院長系主任是“共黨分子或親共分子”,說他們把持的院系是“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許多學生受其影響。傅斯年對此公開發表文章進行反擊,在文章中強調:“假如我對于這樣的舉動妥協了,我念這幾十年書的工夫也就完了,還談教育嗎?我不能承認臺灣大學的無罪學生有罪,有辜的學生為無辜,此之為公平。不能承認任何人有特權,此之謂公平。……寧可我受誣枉。我既為校長,不能坐視我的學生受誣枉。”傅斯年這些行為都是他教育獨立思想的外在表現。正如他去世后臺灣的一些報紙所評論:“傅斯年先生在臺大兩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但遭到最嚴重的打擊、攻訐、阻撓,種種困難的也在此。
傅斯年作為大學校長更注意自己人格的獨立,不像政府官員那樣具有嚴重依附和等級思想。有一件事很能說明他的立場和意識。1949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訪問臺灣,當時國民黨政府剛退守臺灣,迫切需要美軍的保護,因此視麥克阿瑟為太上皇。麥克阿瑟專機到達臺灣時,蔣介石親率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等政要到機場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場,傅斯年雖然去了機場,但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第二天重要報紙刊登的照片,當天在機場貴賓室就座的僅三人,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長及政要垂手恭候,三軍總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則坐在沙發上,口叼煙斗,翹著右腿,瀟灑自若。當時報紙新聞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有人曾引《后漢書》范滂評價郭林宗的語言稱贊傅斯年:“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傅斯年一生不從政,從事教育和學術,努力保持個性獨立,在某種程度代表了中國傳統中最有價值的“道統”觀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要求教育獨立,并為之努力奮斗,在當時是可貴的。
四、傅斯年身殉臺灣大學贏得了極大榮譽
傅斯年任臺大校長期間正是臺灣的非常時期,他日夜謀劃,銳意改革,統籌大政,同時處理繁巨的日常事務。其侄傅樂成回憶說:“他(傅斯年)經常每日在校辦公六小時以上,一進辦公室,便無一分鐘的休息,有時還須參加校外的集會。……他那希望臺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傅斯年的秘書那廉君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可以說傅校長這一年零十個月來,每天除去吃飯睡覺的時間外,統統是用在臺大上頭。”傅斯年久患高血壓病,本來不堪過分勞累,因此,身體不久便垮了下來。他也知道校長事務繁多,自己的身體難以勝任,曾向朱家驊訴苦說:“你把我害了,臺大的事真多,我吃不消,我的命欲斷送在臺大了。”但是說是說,做是做,面對臺灣大學百廢待興的局面,繁巨冗雜的校務,他無法偷懶休息,只好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態度奔走操勞。
1950年春,傅斯年血壓猛然增高,親友皆勸其靜養,他置若罔聞。夏天,又患了膽結石,動手術休息幾天,尚未痊愈又開始了工作。11月,教務長錢思亮赴法,傅斯年的工作更加繁忙。
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蔣夢麟主持召集的農復會會議,主要討論農業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學生出國深造問題。傅斯年想借機多保送臺大學生出國留學,在會上頻頻發言,提了許多意見和建議,據蔣夢麟回憶:會議進行兩個多小時,傅斯年講話最多。午飯后他又去省議會,列席省議會第五次會議,此次會議參議員咨詢的主要是有關教育行政的問題,多數由教育廳長陳雪屏作答。下午5時40分左右,參議員郭寶基咨詢有關臺大的問題,包括國民黨教育部從大陸運到臺灣保存在臺灣大學的教育器材的失盜和放寬臺大招生尺度問題,這些問題須由傅斯年答復。這兩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盜之事,使傅斯年相當憤怒。原來臺灣大學保存一批由大陸運出的器材,結果被臺灣大學保管股長楊如萍等人盜賣,后來被偵破,當時在社會引起一定反響。此事出在臺灣大學,一向嫉惡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要除惡務盡,清除所有敗類。現在參議員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當激動,引起突發性腦溢血,6點10分會議結束后傅斯年倒在議會大廳,經搶救無效,終于在晚上11點左右去世。
奠定學術自由風氣讓傅斯年受臺灣大學后人景仰,一如自由主義將大學視為公共領域中的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傅斯年的個人風格形成對大學的想象,在威權統治時期,他化身學術獨立的神圣性,成為臺灣抵抗政治高壓的共同榮耀。其后五十年,臺大數次校園抗爭事件,都在傅園內的傅鐘前、杜鵑花旁慷慨上演,紀念傅斯年的“傅鐘”成了臺灣大學自由校風的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