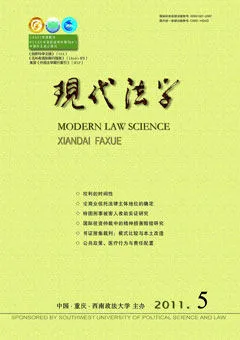刑法類推解釋如何得以進行
2011-01-01 00:00:00黃繼坤
現代法學 2011年5期

摘要:類推是重要的法學思維方法,罪刑法定允許類推解釋,但是禁止作為法律漏洞填補方法的“類推適用”。類推解釋以不法類型為指導,在三段論演繹推理的邏輯外殼下得以進行。類推解釋的關鍵在于就問題案例與概念核心中的特例進行比較,衡量它們在語義、目的上的相同點的重要程度,作出等值評價或反對解釋。類推解釋有助于解決實踐中爭議很大的存疑案件。
關鍵詞:類推解釋;類推適用;罪刑法定;形式解釋;實質解釋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i.issn.1001—2397.2011.05.07
一、問題意識
德國已故刑法學家亞圖·考夫曼指出,類推一直是人類認識包括法律認識的重要思維方法,并非單純的法律漏洞的填補方式。禁止解釋是“立法者天真的紀念碑”,如果雖然容忍法律解釋,也容忍擴張解釋,但卻禁止類推解釋,則也是一種天真。對于可允許的解釋與被禁止類推之間的實際界限完全是不可分的,這絕非只是一種高難度的區分,而是根本性質上二者無從區分。因為解釋被限定為“可能的文義”時,其實就已經處于類推之中了。他認為,“法是當為與存在的對應”,“立法是使法律理念與將來可能的生活事實調適,法律發現是使法律規范與現實的生活事實調適。但此種調適,此種同化,此種使當為與存在相對應須以如下為前提:有個能使理念或者說規范與事實當中取得一致的第三者,亦即,當為與存在之間的調和者,這個第三者就是“事物的本質”,在刑法中,“事物的本性”就是“不法類型”。黎宏教授也提出了與考夫曼相同觀點,而且指出,“廣義上講,刑法適用的過程,就是一個尋找事實和刑法規范所規定的行為類型之間的相似性的類比或者說類推的過程。”“司法的過程,簡化為一個邏輯過程而言,實際上就是法官的目光在大、小前提之間來回移動,尋找其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從而得出判決結論的類比過程。”
上述見解的核心思想在于:類推是不可能絕對禁止的法學思維方法,更不能淪為法律漏洞填補的角色;類推的過程是在“不法類型”的指導下,尋找規范與事實之間相似性的過程。
筆者對此深表贊同。但是,在承認刑法適用過程中需要類推解釋的基礎上,需要把作為刑法解釋方法的“類推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的“類推適用”加以區別;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不法類型”觀念的指導下,就如何尋找事實與規范之間的“相似性”展開深層次討論。后者就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二、概念之厘清:作為解釋方法的“類推解釋”與作為填補法律漏洞的“類推適用”
法律規范需要用語言文字表達。由于語言用語本身存在多義性、不確定性、歷史變化性,因而刑法需要解釋。更何況,法律規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法律概念,而法律概念除了數字這種單純的描述性概念之外,都是規范性概念,若不解釋,就無法將抽象的刑法規范適用于具體的生活事實。
由于刑法概念無不體現價值判斷,因而刑法解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刑法價值的限制。正義是刑法的基礎性價值。所謂正義就是平等、公平,它要求相同的相同對待,不相同的不相同對待。但是,世上并沒有完全一致的相同,也沒有絕對的不相同,因此,刑法正義價值的內容需要進行利益上的衡量、目的上的考慮,此乃刑法的功利價值或稱之為目的價值。目的價值表達的是主體的主觀愿望,即使語言文字將規范的目的明確予以規定,仍然難免在規范目的認定上存在恣意與爭議的現象。受到規范調整的人們會拷問:規范的目的是否正當,達到規范目的的手段是否適當。如果說規范的目的體現的是實質意義上的正義,那么辯證地看,實質意義上的正義也必須用形式上的正義加以制約,也即事先由立法者規定法律適用條件與法律效果,這就是法的安定性。在刑法上,就是罪刑法定主義。因此,如果說正義是刑法基礎性價值,那么合目的性與法的安定性就是正義的擴展性價值,是正義的具體內容,而且,作為實質正義的“合目的性”與作為形式正義的“法的安定性”二者之間顯然存在此消彼長的緊張關系。在解釋刑法時,如何消減二者的沖突緊張關系,是個永恒的話題。
“利益法學的奠基人菲利普·赫克形象地描述道:概念的核心、距離最近的詞義、概念的延伸使我們逐漸認識了陌生的詞。它好比黑暗中被月暈圍繞的月亮。”按照赫克的觀點,概念存在三種區域,即概念核心、概念外圍、概念之外,就一個法律概念而言,處于概念核心區域的對象或事實,顯然為該概念所涵攝;然而,處于“月暈”區域(概念外圍)的就不那么明顯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月暈”之外(概念之外)是不存在被適用的事物或對象的。因此,對于需要解釋的概念,顯然存在明顯適用的區域即概念核心與明顯排除適用的區域即概念外圍,“那些可清楚地被包攝在概念下的對象或案例,也就是所謂的‘肯定(積極)選項’,組成了概念核心。位于這個概念之外的,亦即那些明顯不會落入這個概念的情形,則是‘否定(消極)選項’。概念外圍,則是由‘中立(中性)選項’所組成;這些‘中立選項’,是指根據一般的概念界定或語言使用習慣,無法清楚確認是否應落入此概念下的情形。”處于“月暈”區域的情形是否被包攝于該概念之下,必須通過解釋加以決定,這正是解釋學中爭議最大之處。在刑法適用上,如果堅持形式主義的立場,強調罪刑法定形式的側面而忽視罪刑法定實質的側面,強調法的安定性而忽視法的合目的性,就會將大量處于“月暈”區域的情形排除在概念之外。在黑板上隨手畫的一個圓圈,孩子們有的說是“月亮”、有的說是“鐵環”、“有的說是餅子”……;對于一個玻璃瓶,若不描述它是用來裝“酒”、裝“水”等這些用途的話,則這個玻璃瓶所存在的形式毫無意義可言。因此,刑法解釋不能無視用語的規范目的,而依照規范目的作出的解釋也必須受到用語本身形式上的約束,需要針對具體案情,在二者之間權衡、取舍。
在刑法解釋上,既然某個情形處于“月暈”區域,那么將這種情形涵攝于有待適用的“概念”或“規范”之下,不會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因為這個所謂的“月暈”區域其實處于“用語可能的含義”之中。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確定處于“月暈”這個模糊地帶情形的性質到底更多地接近于概念核心還是更多地背離概念核心而向著概念之外伸展,因為無論是文理解釋還是目的論解釋,都有不能權衡“法的安定性”與“法的合目的性”得出更為妥當的結論的可能性。為了得出妥當的結論,必須采取“類比推理”即類推解釋。
具體而言,“我們把中立選項拿來和那些可清楚被包攝到法律中的案例(也就是肯定選項)相比,或者是以之來和那些明顯不能包攝到法律中的案例(也就是否定選項)相比。用來比較相關案例的著眼點,就是法律的意義與目的。如果中立選項在此觀點下和某個肯定選項相似,那么這就支持我們對于這個法律概念作出較寬松的解釋,把中立選項也一起含括進來。相反,如果在這個觀點下,中立選項是和否定選項相似,那么這就是一個支持縮減解釋的論據,也就是我們應該將這個概念解釋成不包含這個中立選項。”如果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則需要擴張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此為擴張解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將《刑法》第341條中的“出售”解釋為“包括以出賣和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就是擴大解釋。如果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就需要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此乃縮小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將《刑法》第111條規定的“情報”限定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即為此例。
根據上述論斷,可以將作為解釋方法的類推與罪刑法定主義所禁止的類推區別開來。如果把概念適用于明顯處于概念之外的事物或者對象,是罪刑法定主義所禁止的類推即類推適用,正如學界所指出的那樣,所謂“類推適用,系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以為適用。”而中立選項居于概念“可能的語義”范圍內,因此,罪刑法定主義并不反對通過類比解釋的方法確立存有爭議的中立選項是否為該概念所涵攝。
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乃禁止通過法官造法的方式填補法律漏洞。這條原則的根本含義在于,“司法無權通過造法的途徑,創造——諸如為了平等之故——犯罪行為的新的事實構成。”因此,只有通過創設新的不法類型才能納入刑法規制的問題案件才真正存在法律漏洞,反之,凡是沒有創設新的不法類型,而是能夠通過解釋的方法加以處理的所謂的“法律漏洞”,即使存在爭議,也不是真正的法律漏洞。人們通常理解的“法律漏洞”不僅包括那些居于概念之外而不能歸攝于不法類型以至于在法律里根本找不到解決辦法的案件,而且包括由于被立法者看到過,或者未被立法者徹底看到過,以至于被認為在法律里難以找到解決辦法的問題案件。但是,在法律解釋中,探尋立法者的意思而不是法律自身存在的客觀意義并不妥當,因此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法律漏洞”并非都是“真正的法律漏洞”。如果為了填補法律漏洞,把居于概念之外的事實或對象按照類似的不法類型處理的,屬于實質上創設了新的不法類型,為罪刑法定主義所禁止。對此,張明楷教授指出,“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的類推解釋,是指解釋者明知刑法沒有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但以該行為具有危害性、行為人具有人身危險l生等為由,將該行為比照刑法分則的相似條文定罪量刑。換言之,罪刑法定所禁止的類推解釋,是指超出了通過解釋可以得到的刑法規范規定的內容,因而是制定新的刑法規范的一種方法。……概言之,所謂禁止類推解釋,實際上禁止的是‘法無明文規定也處罰’的思維(觀念)與做法。”張教授所稱的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的類推解釋其實就是本文所稱的“類推適用”。
在我國當前刑法學語境下,作為解釋方法的類推與罪刑法定所禁止的類推適用還沒有得到有效區分。只要看到刑法適用中類推解釋的字眼,就自然聯想到“罪刑法定禁止類推”這一鐵則,如有學者針對考夫曼《類推與“事物的本質”——兼論類型理論》一書評述道:“類推與罪刑法定原則是直接對立的,而考夫曼竟然為類推張目,這是令人震驚的。”之所以如此結論,就是因為學者們采取了不同的“類推解釋”的概念。張明楷教授承認作為刑法解釋方法的“類推”,但同時又提出存在“罪刑法定原則禁止的類推解釋”,就是在不同的意義下使用了“類推解釋”的概念。
基于此,本文主張將作為刑法解釋方法的“類推解釋”與作為填補法律漏洞的“類推適用”加以區別。
三、類推解釋的重點在于“相同性”的判斷
在制定法中,法律適用的過程是形式上的三段論演繹推理過程,但是,形式上的三段論演繹推理得不出法律裁判結論。“一個三段論不管表面上看起來多么具有邏輯性,實際上它不過是大小前提及大小前提的邏輯關系而已。雖然有效性在法律推理中是必需的,但就法律推理本身而言,有效性的重要程度是微末的。關鍵性的問題是:(1)識別一個權威性的大前提;(2)明確表述一個真實的小前提;以及(3)推出一個可靠的結論。”三段論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邏輯形式,而是取決于推理的內容及大小前提的真實性,而這種真實性取決于作為小前提的法律事實如何歸納、決定于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如何構建與解釋。因此,就刑法適用而言,就是要(1)識別一個有可能適用的不法類型及法律后果作為大前提;(2)認定問題案件的具體事實,即小前提;(3)判斷小前提與大前提之間的“相同性”的重要程度,并得出結論。
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司法者或法律人會基于因為長期訓練而取得的法感情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案件進行事實歸納而形成可能適用某一不法類型的預判,然后在可能適用的不法類型的觀念指導下,尋找問題案件與不法類型之間的“相同性”,這種相同性的判斷過程就是構成要件符合性的積極判斷與是否存在違法性、有責性阻卻事由的消極判斷過程。如果這種相同性能夠得到確認,則作出適用作為大前提的不法類型及其法律后果的規定,并作出裁判。如果不能形成這種“相同性”判斷,則作出不適用大前提的“反對推論”,并重新尋找可能適用的刑法規范。因此,刑法適用過程,就是“目光在規范與事實之間往返流轉的過程”。
這個被稱之為“詮釋學循環”的過程其實是在三段論的演繹推理的邏輯學外殼下進行的“類推解釋”過程,考夫曼、黎宏教授認為,“不法類型”就是類推中的“中點”,亦即比較的標準。不過,問題案件與“不法類型”之間的相同性究竟該如何得以確認呢?因為問題案件是現實發生的具體事實,而“不法類型”是抽象的觀念形象,現實與觀念、具體與抽象是否真的符合,只有將問題案件與不法類型中沒有疑問的特例加以比較,并在價值上加以衡量,才能得出結論。因此,雖然“不法類型”是問題案件與規范之間“相同性”判斷的基點,但是在問題案件與不法類型之間仍然需要比較二者的“相同點”與“不相同點”,對二者的重要程度進行衡量并作為判斷標準。
在判例法中,類比推理在形式上要求3個步驟:“(1)識別一個權威性的基點或判例;(2)在判例和一個問題案件間識別事實上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以及(3)判斷是事實上的相同點還是不同點更為重要,并因此決定是依照判例還是區別判例。”這種類比推理的結構在制定法類推解釋中仍然適用,具體而言,類推解釋的具體結構表現為:(1)以可能適用的不法類型的觀念指導為指導,把沒有爭議的案例作為比較的基點(可以將其稱為基準案例);(2)在問題案例與基準案例之間,尋找事實上的相同點和不同點;(3)判斷事實上的相同點與不同點的重要程度。
在一般的情況下,由于問題案件與“不法類型”之間的相同性能夠得到直接判斷,就會忽視這種類比解釋的過程,但是疑難案件就非如此了。例如,攜帶匕首搶奪的,顯然符合“攜帶兇器搶奪的,成立搶劫罪”這一不法類型,對于攜帶手槍搶奪的,我們也會不假思索地得出同樣的結論,這是因為無論是匕首還是手槍,均明顯為“兇器”這一概念的核心意思所涵攝。然而,攜帶帶有艾滋病病毒的注射器搶奪的,是不是攜帶兇器搶奪,就不能直接做出判斷,而是需要對兇器這一規范概念加以解釋,對“帶有艾滋病病毒的注射器”是否為“兇器”這一規范概念所涵攝進行判斷。具體而言,要把攜帶帶有艾滋病病毒的注射器與攜帶匕首或攜帶手槍等基準案例進行比較,尋找它們之間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并就相同點與不同點的重要程度進行比較、衡量、判斷,并得出結論,這個比較判斷的過程就是類推解釋。
在不法類型的指導之下,為了合理地運用類推,對存在爭議的問題案例到底是否能被涵攝于不法類型之下作為合理的判斷,必須充分說明理由。對于存疑情形,如果只是極其原則地宣稱“在司法活動中,當實質理性與形式理性發生沖突的時候”,“應當采取形式合理性而放棄實質合理性”,將其排除在不法類型之外,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堅守法的獨立價值,才能通過法律實現社會正義。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犧牲了個案公正,使個別犯罪人員逍遙法外;但法律本身的獨立價值得以確認,法治的原則得以堅持,這就有可能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公正。”以形式理由優于實質理性作為立論的基礎,理由并不充分,因為只有作為立論基礎的前提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可靠性,才能推出妥當結論,而這一論斷中的前提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對于證據充分、事實清楚的需要予以司法評價的行為,既然能夠認定不把這種情形作為犯罪處理,就會使犯罪人逍遙法外,那么就不能將其排除在“不法類型”的規制范圍之外,因為根據“相同的情況相同處理”的基本公平理念,以后凡是與此相同的案件都必須將“犯罪人”至于“外網”之外,因此,必須有更充分的理由對存疑情形作出判斷。
這種說理過程,應該在一種抗辯式的、沒有“非此即彼”的情緒化的機制下進行,爭辯的雙方基于各自立場,提出不同觀點,彼此加以比較、分析、辯駁。這種通過辯論得出結論的過程,其實就是在不法類型的指導下對法律規范所進行的類比解釋、類比推理的過程。在類推過程中,經由辯駁,使得問題案件與基準案例之間的相同點與不相同點更加清晰明了。如果說具有特征X、Y、A或X、Y、Z、A的問題案例與不法類型中具有特征X、Y、Z的典型基準案例之間是相同的,那么這意味著問題案例中的特征A與基準案例中的特征z沒有區別,在價值上可以“等值處理”,或者問題案例中的多余的特征A與基準案例相比,其價值可以忽略不計,在刑法上不必評價。至于為什么可以等值處理,同樣需要通過比較、衡量,然后予以充分說明。如果得出問題案例與基準案例不同的結論,則需要通過比較A與z的區別是如此之大,以致不能等值處理,或者問題案件中的多余的特征A對行為的性質、對不法類型的影響很大,以至于在原則上不能忽略不計,而必須予以刑法上的考量。
在通常情況下,判斷某種差異或不同點不具有原則上的重要性,不僅需要在形式上進行語義上的比較,而且需要在實質上予以目的上的衡量。一方面要把類推解釋的結論控制在“用語可能的含義”之內,以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另一方面要從規范的目的出發,對存在分歧的概念在“用語可能的含義”內進行實質解釋方能得出結論。詳言之,在這個類推解釋的過程中:(1)如果存疑情形明顯處于“概念外圍”,則必須排除在涵攝之外;(2)因為存疑情形是否處于“用語可能的含義”內可能存在分歧,所以需要將存疑情形與明顯處于概念之外的特例或具體事例進行比較,如果能夠得出相同結論,則將其排除在涵攝之外;(3)將存疑情形與概念核心中的(多個)特例或具體事例比較,即將問題案件與(多個)基準案件進行類比,對彼此之間的相同性與不同性的重要性進行衡量,若作出具有相同性的判斷,則經過上述層層排查之后所得出的結論不會違反罪刑法定禁止類推適用的要求,如果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則必須對上述推理過程提出更加有力的反對論證。
四、作出類推解釋“相同性”判斷需要考慮的因素
通過類推解釋得出結論,需要進行全方位的比較,文義、體系、歷史等各方面都必須加以考慮。但是文義始終是解釋的出發點,而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目的”。
(一)優先從可能的語義上加以比較
1、通奸屬于破壞軍婚罪中的同居嗎?
從詞義的角度看,“通奸”明顯處于“同居”概念外圍,但是既然提出了“通奸可能被涵攝于破壞軍婚罪中的同居概念”的判斷,就需要在詞義上進一步比較說明。
“通奸”是與“強奸”相對的概念,“通奸”意指男女雙方基于合意而發生性關系,而“強奸”則意指男女某方違背對方的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通奸”帶有貶義,帶有不應該在婚姻之外與非配偶發生性關系的道德評價。
在1994年國務院頒布實行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之前,凡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男女雙方即使沒有履行結婚登記手續,但是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成立事實婚姻,也受法律保護;而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頒布實施之后,建立合法的婚姻關系必須履行結婚登記為要件,沒有履行結婚登記手續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在法律上被評價為“非法同居”。在此之外,還存在婚姻關系之外的男女雙方在不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情況,亦即一般意義的“同居”。將上述情況加以比較,可以發現,一般意義上的“同居”的特點在于:男女雙方不是夫妻也沒有以夫妻名義相稱,而且在較長時間內共同居住、共同生活,且發生性關系。
關于通奸的典型事例即問題案例如,甲男與軍人的配偶的乙女,勾搭成奸,發生了一次性關系,然后彼此分開。關于同居的典型案例即基準案例如,A男與軍人的配偶B女,勾搭成奸,不以夫妻名義,在較長時間內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將問題案例與基準案例加以比較,不難發現,二者的相同點僅僅在于:甲與乙發生了性關系,A與B也發生了性關系。二者的不同點在于:與問題案例不同,在基準案例中存在A與B在較長時間內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事實。
但是,關于“同居”的基準案例中,發生性關系既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假如A與B在共同居住、共同生活過程中,雙方對性是如此看重,以至于彼此約定只有在B離婚而與A再婚之后,才可以發生實質的性交關系,但是不排除采取性交之外的其它方法滿足性欲的,顯然也是“破壞軍婚罪”中的“同居”。
因此,可能成立破壞軍婚罪中的“通奸”與典型的“同居”之間可能存在的相同點并非必然存在,這意味著“通奸”與“同居”之間從根本上是不相同的,僅僅與軍人配偶發生性關系的“通奸”行為不能與基準案例中的“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可能發生性交”的行為一樣,等值評價為破壞軍婚罪中的“同居”。
2、在互聯網上傳播的淫穢信息是淫穢物品嗎?在互聯網上裸聊牟利的是否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在互聯網中傳播的淫穢書刊、影片、圖片、視頻動畫等淫穢信息是否我國刑法中的“淫穢物品”呢?
在概念核心意義上,“物品”意味著有體物,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許多固有的觀念必然受到影響并得以改變,我們也可以感覺到把在互聯網中傳播的“淫穢書刊、影片、圖片、視頻動畫”等認定為淫穢物品似乎并無不妥,因此,可以初步判斷這些淫穢信息處于“淫穢物品”“可能的語義”內,但是到底這種淫穢信息是否可以為刑法中的“淫穢物品”所涵攝,則需要進一步的比較、判斷。
問題案例:甲將存在電腦中的淫穢電影,掛在互聯網上供人下載的,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嗎?
基準案例:乙傳播淫穢電影光盤,情節嚴重,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
將二者比較,可以發現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二者的外在存在形式不同,前者為計算機技術上的數據文件,而后者即淫穢光盤外在表現為一種有體物,可以看得見、摸得著,但同時也可以意識到,淫穢光盤的具體內容也是以計算機技術中的數據文件的形式儲存在光盤之中的。因此,二者的相異點其實只是儲存形式上的不同。二者的相同點在于:都具有誨淫性,而且這種具有誨淫性的內容都能夠傳播、轉移。這種相同點足以將問題案例中的“淫穢電影文件”與基準案例中的“淫穢電影光盤”等值判斷為“淫穢物品”,或者說二者儲存形式上的不相同對“傳播淫穢物品罪”的不法類型上的判斷并無影響。
《刑法》第367條規定,“淫穢物品,是指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2000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第3條第(5)項規定,“在互聯網上建立淫穢網站、網頁,提供淫穢站點鏈接服務,或者傳播淫穢書刊、影片、音像、圖片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將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的淫穢信息認定為“淫穢物品”是有法律依據的。
但是,在互聯網上裸聊牟利的,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嗎?
如果A以牟利為目的,傳播淫穢光盤,顯然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假如B女在互聯網里,與他人裸聊,收取費用的,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嗎?很顯然,二者都向他人傳遞了淫穢信息,這是相同點。不同點在于,前者的淫穢信息的具體內容儲存在光盤之中,通過光盤這一載體淫穢信息得以固定、存在,而就后者而言,雖然在裸聊的過程中,裸聊的雙方均受到性的刺激、獲得性欲滿足,但是這種淫穢信息是即時存在的、并沒有一定媒介作為載體固定下來。究竟是相同點重要還是不同點更重要呢?假如C在互聯網里,設置鏈接,將儲存在自己電腦里的淫穢電影文件掛在網上,供他人下載,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如果C收取費用,可以判斷為主觀上具有牟利的目的,則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在這種場合下,我們認為放置在互聯網上的淫穢文件,與傳統的光盤、錄像帶等為載體的淫穢電影等,只是淫穢電影等的儲存方式不同,二者都為“淫穢物品”所涵攝。將C與B相比,二者的相同點仍然向他人傳遞了淫穢信息,不同點仍然是C案里的淫穢信息的內容是有載體的,以數據文件的形式存在互聯網服務器電腦的硬盤上,而B案中的淫穢信息是即時的,沒有被固定下來,一旦B女穿了衣服,所有帶給裸聊對方的淫穢信息立即消失,不復存在。
如果這種傳遞即時性的淫穢信息,收取費用的行為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那么D女與他人不是在互聯網上,而是直接面對面的裸聊,收取費用的,也應該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因為二者之間除了利用互聯網將裸聊的雙方從浩瀚人海拉近之外,再無任何區別。在這種思路上繼續推理,則會得出以下結論:組織進行淫穢表演的,成立組織淫穢表演罪,而實施淫穢表演的演員,如果以牟利為目的,則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沒有以牟利為目的的,則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狂熱的球迷沖入中超球場上裸奔的,也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諸如此類。但是,上述行為從來都不認為成立此種犯罪。
因此,淫穢信息借助某種介質被固定下來成為判斷其為“淫穢物品”所涵攝的關鍵。相應地,互聯網上裸聊牟利的,不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在互聯網上裸聊的,也不成立傳播淫穢物品罪。
3、組織或者強迫男性向同性提供性服務的,成立組織或者強迫賣淫罪嗎?
《刑法》規定,“組織他人賣淫或者強迫他人賣淫的,成立組織或者強迫賣淫罪”。對于問題案例,需要判斷的是男性是否涵攝于不法類型中的“他人”,以及以牟利為目的,男性向男性提供滿足其性欲的服務行為是否屬于“賣淫”。在通常情況下所發生的基準案例表現為以牟利為目的,組織或者強迫女性向男性提供滿足其性欲的行為。將問題案例與基準案例相比,相同點“以營利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提供性服務”。不同點在于:在基準案例中,提供性交服務的是女性,接受性交服務的是男性,而在問題案例中,提供性交服務的是男性,接受性交服務的也是男性。但是,如果男性以牟利為目的,向女性提供性交服務的,與通常情況下的基準案例相比,只是出賣性交服務的主體由女性變成了男性,其余的沒有什么不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會認為這是賣淫。能否承認男性向男性以金錢作為代價而提供性交服務的,也是賣淫呢?人們之所以提出“男性向男性以金錢作為代價而提供性交服務的,是否屬于賣淫”的疑問,是因為人們普遍的價值觀念,仍然沉浸在賣淫只能是男女之間才能發生的茍且之事的迷思中,而沒有意識到社會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變化,沒有意識到社會現實中存在“同性戀”這一非主流的性愛生活。只要認識到同性之間也可以發生性交如肛交,就會認識到“組織或者強迫男性向同性提供性服務的,同樣成立組織或者強迫賣淫罪”。其實,從語義解釋上得出這種結論毫無疑問,沒有任何理由將“男性”排除在不法類型中“他人”之外,沒有理由認為“男性以牟利為目的,向女性提供性交服務的,不是賣淫”,也沒有理由認為“男性以牟利為目的,向男性提供性交服務的,不是賣淫”,同樣地,組織或強迫女性向女性提供性交服務的,也成立組織賣淫罪或強迫賣淫罪。
(二)從規范目的上加以實質分析
1、未領取結婚證,一男兩女(或一女兩男)同時舉行婚禮,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成立重婚罪嗎?
根據《刑法》規定,所謂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刑法解釋,必須考慮刑法用語在法律體系中的意義。我國《婚姻法》第8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因為我國實行結婚登記制度,沒有履行結婚登記手續而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被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所以,從語義上看,結婚就是履行結婚登記手續,取得結婚證,配偶就是取得結婚證的彼此的對方。
但是,這種從法律體系上考查所得出的結論,并不妥當,因為這種結論沒有從歷史的角度考查“事實婚姻”,在法律制度中的意義。一般而言,事實婚姻是指男女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周圍群眾也認為其是夫妻關系的一種實際婚姻狀況。我國自古在婚姻制度上,遵父母之命,采媒妁之言,沒有結婚登記,只需舉行一定結婚儀式,即確立了是夫妻關系。雖然建國以來,于1950年頒布實施的舊《婚姻法》規定了結婚登記制度,但是對于事實婚姻,國家仍然承認其效力,將其與登記婚姻同等對待。亦即,成立重婚罪包括四種情況:“登記婚姻”+“登記婚姻”;“登記婚姻”+“事實婚姻”;“事實婚姻”+“登記婚姻”;“事實婚姻”+“事實婚姻”。但是,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頒布了新《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其中第24條規定:“符合結婚條件的是當事人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其婚姻關系無效,不受法律保護。”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5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8條規定補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條例》公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條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條例》公布實施以后,男女雙方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
因此,1994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是認定所謂“事實婚姻”的分水嶺,《條例》實施之前事實婚姻仍為國家承認、保護,而《條例》實施之后的所謂的“事實婚姻”,國家不承認其效力,確認其是非法同居關系。這一點對于解釋重婚罪的構成要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即只有建立登記婚姻的,才是“有配偶”,在事實婚姻中,非法同居的男女雙方都不是對方的配偶。因此,涉嫌成立重婚罪的只有兩種情況,“登記婚姻”+“登記婚姻”、“登記婚姻”+“事實婚姻”。就成立重婚罪無需贅言,而則需考查重婚罪的規范目的方能得出結論。
在重婚罪的規范目的上,主要有兩種觀點,重婚罪的客體是國家規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重婚罪的客體是重婚行為所侵害的而為刑法所保護的權益即重婚行為所涉及的婚姻關系中無辜的一方的人身權利。按照第一種觀點,重婚罪的規范目的是保護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按照第二種觀點,重婚罪的規范目的是保護合法婚姻關系中受害方的一夫一妻制的配偶權。無論采取哪種觀點,都成立重婚罪。
對于“未領取結婚證,三人同時舉行婚禮,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生育孩子的”,按照第一種觀點,這種行為顯然侵犯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進而將“有配偶”解釋為事實婚姻中的男女也是彼此的配偶,而同時舉行婚禮形成兩個事實婚姻的,也是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的行為,成立重婚罪。例如吳學斌教授指出,事實上,無論前后是兩個事實婚姻,還是其中之一的是事實婚姻,都在實質上是對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一種挑釁和違反,同時也與社會公認的正義與公平價值相沖突。《刑法》第258條的“有配偶”,當然包括事實婚姻上的配偶。
但是這一結論并不正確。因為將問題案例與基準案例相比,存在的惟一相同點在于:它們都侵犯了一夫一妻婚姻制度,除此之外,存在太多的不同點:在基準案例中,存在兩個婚姻關系的重合,前一個婚姻關系是受法律保護的登記婚姻(但是1994年新《婚姻登記條例》生效之前的事實婚姻也受保護),后一個無論是登記婚姻還是事實婚姻,均不受法律保護;而在問題案例中,兩個所謂的事實婚姻都不受法律保護;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只有登記婚姻中的重婚者的配偶才能成為重婚案中的自訴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沒有控訴重婚罪的職權,而在問題案例中,同時舉行婚禮的一男二女中無人具備自訴人的資格;在基準案例中,重婚行為侵犯了合法婚姻關系中受害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配偶權,而在問題案例中,三人都是“受益人”,而非一夫一妻制度下配偶權被侵犯的受害人。而且一旦承認問題案例成立重婚罪,那么就必須放棄所有從法律體系上、語義上得出的關于“有配偶”、“結婚”、“事實婚姻”等的基本含義。不同點如此之多、如此重要以至于難以得出問題案例成立重婚罪的結論。
陳興良教授認為,由于采取了“法律實質主義的思維方法,從重婚罪的本質特征是破壞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發,推導出事實婚姻破壞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具有了重婚罪的本質特征,因而在實質上構成了重婚罪。通過這一實質推理,將一個本來不具備重婚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予以入罪。”本文認為,之所以得出問題案例成立重婚罪的結論,是因為確立了錯誤的重婚罪的規范目的,而不是在解釋刑法時考慮規范的目的的思維方法有問題。由于重婚罪規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因而重婚罪保護的只能是合法婚姻關系中受害人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配偶權,而不是倫理道德上的一夫一妻制度。采取刑罰的手段推行一夫一妻制度,將沒有受害人的所謂侵害一夫一妻制度的行為也納入刑法規制,手段不具有適當性。
因此,在類推解釋時,不能無視語義解釋中的體系解釋、歷史解釋,在以規范目的為比較點時,需謹慎審視規范目的本身一定是正義的、理性的,而且實現規范目的的手段本身必須具有適當性。
2、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員,槍支被搶、被盜之后沒有報告,結果被他人利用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構成《刑法》第129條所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告罪嗎?
《刑法》第129條規定,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員,丟失槍支不及時報告,造成嚴重后果的,成立丟失槍支不報罪。在一般的語義上,“丟失”是指“遺失”。在基準案例中,警察甲在上班途中,不小心將公務用槍丟失在地上,不及時報告,被行為人乙撿到后,槍殺多人。在問題案例中,警察A的公務用槍被劫匪B使用暴力劫走,槍支處于失控狀態,但是A沒有及時報告,B使用搶劫來的槍支打死多人。將二者相比,相同點表現為:甲與A二人的公務用槍均因某種原因處于失控狀態;都沒有及時報告;都造成了嚴重后果。不同處僅僅在于造成槍支失去控制的原因不同,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員對于保證槍支安全負有重要職責,在基準案例中,犯罪人甲對槍支失去控制本身具有過錯,而在問題案例中,A對槍支失控本身沒有過錯,那么這點不同足以成為A不成立犯罪的理由嗎?本罪的規范目的在于要求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員,在槍支失去控制之后,必須及時報告,以便有關部門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因此,本罪的實行行為是不及時報告槍支失去控制的事實,“造成嚴重后果”是提高違法性程度、限制處罰范圍的構成要件要素。就本罪的不法類型而言,槍支失去控制的原因不是構成要件要素,對于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沒有影響,因此,無論何種槍支失控的原因,都可與一般意義上的“遺失”等值判斷為《刑法》第129條所規定的“丟失”。
總之,刑法適用不是純粹的邏輯運用過程,而是在三段論演繹推理的外殼下所進行的類推解釋,尋找問題案例與不法類型之間的相同性的過程。在運用類推解釋時,需要在不法類型的指導下,首先就問題案例與不法類型中的典型特例進行語義上的比較,從而將類推解釋控制在“可能的語義”范圍之內。然后考慮法律概念本身所蘊含的價值判斷,考慮法律規范本身的目的、意義,因為法律規范由法律概念組成,不是單義的文字堆砌,不考查規范的目的、意義,就無法就類推解釋的重點即相同點進行衡量與判斷。耶林在背棄概念法學之時,曾經這樣說道:不能出于對邏輯的崇拜而把法學抬高為某種數學,這種崇拜是建立在對法的本質錯誤認識基礎之上的迷途,因為“并非生活為概念而存在,而是概念為生活而存在。”
(三)文義解釋與目的解釋發生沖突時的權衡與取舍
在概念用語可能的語義范圍內,進行規范的目的上的比較,得出適用規范結論的,符合罪刑法定主義;若明顯超出用語的可能含義,仍然得出適用規范結論的,是罪刑法定主義所禁止的類推適用。但是,根據規范目的,必須得出有罪的結論時,就必須在文義解釋與目的解釋之間,或在法的安定性與法的合目的性之間進行權衡、取舍,如果目的上的相同點的重要程度遠遠高于文義上的不相同點,則應該擴大解釋用語含義,得出適用規范的解釋結論。
在羅馬的第一部法典,即十二木表法中,曾經有過這樣的規定:
四腳動物的所有權人就該四腳動物出于其獸性對他人所引起之損害,負賠償損害責任。
在迦太基被摧毀后,第一支鴕鳥被當做戰利品出現在羅馬。因為這只鴕鳥也相當狂野,可能出于獸性而使他人遭受損害。于是便出現這樣一個問題:上述規定是否可以適用于一頭兩只腳的動物基于獸性而使他人遭受損害的情形呢?
基準案例:一頭四腳動物(如牛)出于獸性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的所有權人應負賠償責任。
問題案例:一只兩只腳的動物(如鴕鳥)出于獸性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的所有權人應負賠償責任嗎?
相同點:鴕鳥與牛都有獸性,都能造成他人損害。
不同點:鴕鳥只有兩只腳,而牛有四只腳。
很顯然,從規范的目的來看,相同點重要,能夠得出適用該規范的結論。但是從用語的語義來看,鴕鳥只有兩只腳,怎么也不可能成為“四腳動物”,二者根本就是不同的,只能采取不能適用該法規的“反對解釋”。可見,該規范存在法律漏洞。若將該規范適用于鴕鳥出于獸性而致人損害的情形,是通過“類推適用”彌補法律漏洞。
我國《刑法》第263條規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加重處罰(法定刑升格)。問題在于,真正的軍警人員顯示具有軍警人員身份搶劫的,也是“冒充軍警人員搶劫”,從而適用升格的法定刑。
很顯然,既不是軍人又不是警察的A,冒充軍人或警察搶劫的,加重處罰;軍人B冒充警察搶劫的,也應加重處罰;警察C冒充軍人搶劫的,同樣應該加重處罰。
那么問題案例中,具有軍警身份的D,顯示其身份搶劫的,也應加重處罰嗎?
如果將問題案例與上述特例加以比較,我們發現相同點有兩點:(1)由于軍警人員都受過嚴格訓練,而且有可能持有槍支,如果被害人反抗可能會遭受嚴重人身傷害,因而行為人的軍警人員身份給被害人造成極大的恐怖心理,使犯罪更容易得逞;(2)都嚴重損害國家機關的形象。不同點在于:在問題案例中,D具有軍警人員的身份,而在基準案例中,A不具有這種身份,B、C則是假冒了另外一種身份。可是,為什么軍人B假冒警察、警察C假冒軍人搶劫要加重處罰,惟獨對顯示真正軍警身份的D是否加重處罰提出疑問呢?一切都是“冒充”這個用語惹的禍。
很顯然,如果重視規范目的,重視經過比較所得出的“相同點”,那么就應該對D加重處罰;但是如果重視“冒充”的核心意義是“假冒”,則只能作出反對解釋,對D不能加重處罰。張明楷教授基于實質解釋論的立場,認為:“從實質上說,軍警人員顯示其真正身份搶劫比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更具有提升法定刑的理由。刑法使用的是‘冒充’一詞,給人印象是排除了真正的軍警人員顯示真實身份搶劫的情形。但是,刑法也有條文使用了‘假冒’一詞,故或許可以認為,冒充不等于假冒。換言之,‘冒充’包括假冒與充當,其實質是使被害人得知行為人為軍警人員,故軍警人員顯示其身份搶劫的,應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而以陳興良教授為代表的形式解釋論則堅持認為,應該把軍警人員顯示真實身份搶劫排除在冒充軍警人員搶劫之外,否則就是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
但是,將顯示真實軍警人員搶劫的行為人加重處罰,并不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也不侵犯國民樸素的正義感。相反的,如果假冒軍警搶劫的,被加重處罰,最高可判處死刑,而真正的軍警顯示其身份搶劫的,卻沒有加重處罰,最高只判處10年有期徒刑的話,則不僅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而且蹂躪國民的公平正義觀念、引發國民對刑法的正當性的質疑。在現代中國,本來就存在法律信仰危機,如果司法者面對這種非此即彼的難題,斷然作出不加重處罰的決定,恐怕會進一步挑動公眾愈發脆弱的神經。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慎重比較分析:相同點如此重要,以至于不相同點可以忽略不計;不得不綜合考量:是否具有很大的加重處罰的必要性、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是否侵犯普遍的正義觀念、是否激化社會矛盾……。
由于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適用,但允許擴大解釋,因此,“真正的軍警人員顯示其身份搶劫的,也加重處罰”不是類推適用,而是由于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而采取的擴大解釋,即在通常語義上,“冒充”意指“假冒”,但是“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中的“冒充”包括“假冒”與“充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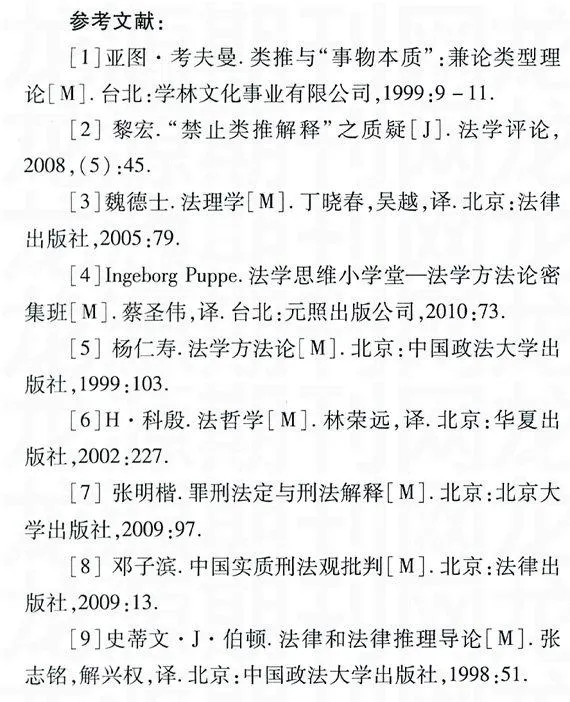
<img src="https://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mlaw/mlaw201105/mlaw20110507-2-l.jpg?auth_key=1736838619-1167240649-0-665c2c6aa47bc6f67d1fe4d6d3d914f4" hspace="15" vspace="5" 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