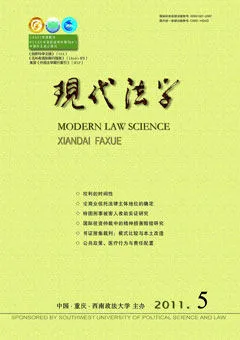多元化適用: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選擇路徑
2011-01-01 00:00:00包冰鋒
現(xiàn)代法學(xué) 2011年5期

摘要:法律效果是構(gòu)建證明妨礙制度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訴訟實(shí)務(wù)操作的多樣化和訴訟理論見解的不統(tǒng)一導(dǎo)致關(guān)于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討論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根據(jù)多元化觀點(diǎn),不宜采取劃一性的方式制裁妨礙者,法院應(yīng)當(dāng)本著誠實(shí)信用原則,仔細(xì)斟酌妨礙者的主觀心態(tài)、實(shí)施方式、可歸責(zé)程度及被妨礙證據(jù)的重要性等因素,在結(jié)合其他證據(jù)的基礎(chǔ)上采取自由心證的方式對事實(shí)作出認(rèn)定。法院可以選擇推定舉證人的主張為真實(shí)、或者直接認(rèn)定妨礙者擬制自認(rèn),或者針對該等事實(shí)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甚至在必要時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或者采取罰款、拘留或直接強(qiáng)制等強(qiáng)制措施。
關(guān)鍵詞:民事訴訟;證明妨礙;法律效果
中圖分類號:DF7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DOI:10.3969/i.issn.1001—2397.2011.05.09
一、問題的提出
正如美國法學(xué)家博登海默所言:“一個法律制度,如果沒有可強(qiáng)制實(shí)施的懲罰手段,就會被證明無力限制非合作的、反社會的和犯罪的因素,從而也就不能實(shí)現(xiàn)其在社會中維持秩序與正義的基本職能”。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強(qiáng)制力、沒有制裁效果的法律就是“一把不燃燒的火,一縷不發(fā)亮的光。”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妨礙行為是指當(dāng)事人或第三人在訴訟中或訴訟外,以故意或過失的作為或不作為,致使對方當(dāng)事人陷入證明困難或證明不能的行為。為了維護(hù)正常的訴訟秩序,法律必須對證明妨礙的行為施加一定的制裁法律效果。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選擇實(shí)與證明妨礙制度的法理基礎(chǔ)息息相關(guān)。為了實(shí)現(xiàn)確保當(dāng)事人的司法保障請求權(quán),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有機(jī)會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確定案件事實(shí)為何。而民事訴訟程序原則上是依循辯論主義進(jìn)行,那么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享有公平接近、使用證據(jù)的機(jī)會。因而,當(dāng)事人或第三人不得以毀棄、滅失、隱匿證據(jù)等方式,侵害對方當(dāng)事人的證明權(quán)以致其應(yīng)享有的司法保障請求權(quán)無法獲得實(shí)現(xiàn)。如果當(dāng)事人或第三人果真實(shí)施了證明妨礙行為,那么應(yīng)當(dāng)課以何種法律效果以保障對方當(dāng)事人的司法保障請求權(quán),是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最根本問題。
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妨礙行為導(dǎo)致案件事實(shí)無法查明,這不但侵害了當(dāng)事人的實(shí)體利益和程序利益,而且也嚴(yán)重?cái)_亂了訴訟程序的正常進(jìn)行。因此,諸多國家和地區(qū)均對實(shí)施證明妨礙的行為人課以不利的法律效果以示懲戒。此外,證明妨礙理論發(fā)展至今,學(xué)界也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各種學(xué)說。也正因?yàn)榉尚Ч菢?gòu)建證明妨礙制度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所以學(xué)者之間對此問題向來有爭執(zhí),眾說紛紜。訴訟實(shí)務(wù)操作的多樣化和訴訟理論見解的不統(tǒng)一導(dǎo)致關(guān)于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討論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換言之,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彈性化與類型化是日后發(fā)展的重要方向。
二、證明妨礙法律效果各學(xué)說之考察
(一)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
1、學(xué)說概覽
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也有學(xué)者稱之為證明責(zé)任倒置說。有學(xué)者認(rèn)為,“民事訴訟中證明責(zé)任的倒置有其特定的含義,是指按照法律要件分類說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分配證明責(zé)任后,對依此分配結(jié)果原本應(yīng)當(dāng)由一方當(dāng)事人對某法律要件事實(shí)存在負(fù)證明責(zé)任,轉(zhuǎn)由另一方當(dāng)事人就不存在該事實(shí)負(fù)證明責(zé)任。”但是,目前祖國大陸學(xué)者對于證明責(zé)任倒置這一說法爭議頗大,而且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qū)基本不采用證明責(zé)任倒置的說法。因此,本文采用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的用語。
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認(rèn)為,有證明妨礙的情況發(fā)生時,應(yīng)當(dāng)將舉證者所主張的事實(shí)的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于妨礙者;將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于妨礙者,妨礙者即陷于有受敗訴判決的危險,藉此可以防止證明妨礙的情況發(fā)生。其立論的依據(jù),有基于期待可能性衡量者,有基于刑罰的考慮觀點(diǎn)的,有以損害賠償請求權(quán)作為立論基礎(chǔ)的,也有以危險領(lǐng)域說作為理由的。但持不同意見者認(rèn)為,如果采用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則顯然缺乏彈性,基于故意與過失行為在效果上等同視之,似有失衡與不妥。尤其采用此見解,一般將導(dǎo)致不負(fù)證明責(zé)任的一方當(dāng)事人敗訴,實(shí)應(yīng)持較為謹(jǐn)慎的態(tài)度。而且德國法明文規(guī)定的文書證明的妨礙在效果上也似不如此見解般的強(qiáng)烈取向。
從歷史演進(jìn)上來看,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首先被提出者即為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其目的是想通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方式達(dá)到回復(fù)原狀或者回復(fù)到證據(jù)沒有被毀損、滅失的情形的效果。而且對實(shí)施證明妨礙的行為人課以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效果也可以達(dá)到制裁的效果,畢竟舉證之所在往往是勝敗之所在。其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被批評為僵化的做法,可能給予受妨礙者超過其未受妨礙時的利益,而且在訴訟中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有害于程序的安定。從而學(xué)說轉(zhuǎn)向以自由心證或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但是這并非意味著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從此不再作為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選擇,而是應(yīng)該討論其于何種情形下可以適用。
2、客觀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
此外,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究竟是指客觀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還是主觀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學(xué)界存有爭議。從多數(shù)學(xué)者的論述中可以得知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是指客觀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
(1)德國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1977年7月1日通過的《民事訴訟法》,雖然未就證明妨礙設(shè)置通則性規(guī)定,但是在其委員會的報告(Kommissionsbericht)中,對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6條提出修訂意見為:“(第一款)法院應(yīng)當(dāng)考慮言詞辯論的全部內(nèi)容以及已有的調(diào)查證據(jù)的結(jié)果,經(jīng)過自由心證,以判斷事實(shí)上的主張是否可以認(rèn)為真實(shí)。(第二款)如果一方當(dāng)事人不能舉證,是因?yàn)樗疆?dāng)事人隱匿、剝奪或致令不堪使用的,第一款規(guī)定適用之。(第三款)如果對方當(dāng)事人可歸責(zé)違反就證據(jù)方法予以提出、供使用、予以取得、或其他就其可使用性不得侵害的義務(wù)的,則法院可以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從該規(guī)定可以看出,《修正草案》是主張如果屬于可歸責(zé)違反協(xié)力義務(wù)類型,那么可以依據(jù)轉(zhuǎn)換客觀證明責(zé)任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將真?zhèn)尾幻鞯臄≡V危險歸由實(shí)施證明妨礙的行為人負(fù)擔(dān)。但是該規(guī)定并沒有被立法者所采納,所以并未成為明文立法。
(2)日本
日本學(xué)界有學(xué)者認(rèn)為證明妨礙屬于法院自由心證的問題,而自由心證屬于對于當(dāng)事人態(tài)度的評價問題,因?yàn)楣室獾淖C明妨礙是屬于誠實(shí)信用原則的違背,是關(guān)于事實(shí)的自由心證領(lǐng)域的問題,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遇有證明妨礙情形時其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是屬于提供證據(jù)責(zé)任,即主觀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另外,也有學(xué)者從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24條有關(guān)“法院可以認(rèn)定對方當(dāng)事人所主張的關(guān)于該文書的記載為真實(shí)”的規(guī)定出發(fā),并基于客觀證明責(zé)任在訴訟中發(fā)生轉(zhuǎn)換會導(dǎo)致程序不安定,認(rèn)為發(fā)生轉(zhuǎn)換的證明責(zé)任是屬于提供證據(jù)責(zé)任,即主觀證明責(zé)任。
(3)我國臺灣地區(qū)
我國臺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于2000年修正為:“當(dāng)事人主張有利于己之事實(shí)者,就其事實(shí)有舉證之責(zé)任。但法律別有規(guī)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修正理由認(rèn)為:“在當(dāng)事人主張之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鲿r,應(yīng)如何定舉證責(zé)任之分配,對訴訟之勝敗,攸關(guān)甚鉅。夷考德、日等國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均未就舉證責(zé)任直接設(shè)有概括性或通則性之一般規(guī)定,通常均委由學(xué)說、判例而為補(bǔ)充。現(xiàn)行法就舉證責(zé)任之分配,于本條設(shè)有原則性之概括規(guī)定,在適用上固有標(biāo)準(zhǔn)可循。惟關(guān)于舉證責(zé)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shè)原則性規(guī)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zé)任之分配問題,于具體事件之適用上,自難免發(fā)生困難,故最高法院于判例中,即曾依誠信原則定舉證責(zé)任之分配。尤以關(guān)于公害事件、交通事故、商品制作人責(zé)任、醫(y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理,如嚴(yán)守本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chǎn)生不公平之結(jié)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yīng)有之救濟(jì),有違正義原則,爰于原條文之下增訂但書,規(guī)定‘但法律別有規(guī)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以資因應(yīng)。”就證明責(zé)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我國臺灣地區(qū)以法律要件分類說為通說,而我國臺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可謂明文授與法院可以依其自由裁量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的分配以求個案的公平。這里規(guī)定的證明責(zé)任即為客觀意義的證明責(zé)任。在這里需要進(jìn)一步探討的是,在民事訴訟中發(fā)生證明妨礙的情形,可否適用該法第277條但書的規(guī)定。有學(xué)者認(rèn)為,可以依據(jù)危險領(lǐng)域理論,而將證明妨礙歸類于可以適用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類型,但是這屬于證明責(zé)任分配的例外情形,尚待實(shí)務(wù)予以類型化。有學(xué)者認(rèn)為,依據(jù)我國臺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的修正理由,因證明妨礙行為導(dǎo)致依據(jù)原先標(biāo)準(zhǔn)分配證明責(zé)任屬于顯失公平時,自可進(jìn)行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
(二)自由心證說
1、自由心證說對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的批判
從歷史沿革來看,關(guān)于證明妨礙法律效果討論始于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但是,主張自由心證說的學(xué)者認(rèn)為將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至少有下述缺點(diǎn):其一,承認(rèn)在訴訟程序中可以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將導(dǎo)致訴訟程序不安定;其二,不盡可能就相反事實(shí)的存在進(jìn)行舉證,僅僅以與其他證據(jù)無關(guān)的證明妨礙的存否來決定,過于形式;其三,不問過錯輕重,一律課予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效果不當(dāng);其四,一律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可能使因證明妨礙而遭受不利益的當(dāng)事人獲得超過限度的利益。質(zhì)言之,操作僵化是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被批判的最主要原因。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存在的諸多缺點(diǎn)為自由心證說的發(fā)展提供了空間。
2、自由心證說的主要觀點(diǎn)
自由心證說認(rèn)為,發(fā)生證明妨礙的情形時,法院可以認(rèn)定舉證人的主張為真實(shí)。但是如果有其他證據(jù)方法存在,而妨礙者申請證據(jù)調(diào)查時,法院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一般原則進(jìn)行證據(jù)調(diào)查。而法院根據(jù)調(diào)查證據(jù)的結(jié)果及全辯論意旨,依自由心證,認(rèn)為舉證人的主張不真實(shí)的,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不真實(shí)。相較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承認(rèn)證明責(zé)任分配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自由心證說認(rèn)為,證明責(zé)任的分配是預(yù)先通過法條的規(guī)定早于當(dāng)事人起訴之前即已確立。證明責(zé)任并不因具體訴訟中所產(chǎn)生的證明困難或證據(jù)方法的偏向存在而有所變動。具體而言,相較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自由心證說有以下觀點(diǎn):
其一,因證明妨礙的問題大多發(fā)生于訴訟進(jìn)行過程中,如果依據(jù)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將導(dǎo)致證明責(zé)任在訴訟進(jìn)行的過程中發(fā)生變動,造成訴訟程序的不安定。就證明妨礙的構(gòu)成要件而言,究竟原本負(fù)擔(dān)證明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因?qū)Ψ疆?dāng)事人證明妨礙的行為而陷入多大的證明困難?因該等證明困難是否造成其無法進(jìn)行證明?以上事實(shí)本身均相當(dāng)難以證明。由此可知,以“陷于證明困難”為標(biāo)準(zhǔn)而決定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與否,實(shí)在無法保證法院決定證明責(zé)任分配標(biāo)準(zhǔn)的明確性與法律適用的安定性。相對于此,自由心證說本于事實(shí)審言詞辯論終結(jié)時,由法官綜合全案證據(jù)調(diào)查的結(jié)果與全辯論意旨而進(jìn)行最終決定評價,所以判決的結(jié)論并不僵化而有助于實(shí)現(xiàn)個案正義。
其二,依據(jù)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如果實(shí)施證明妨礙的當(dāng)事人無法使法官就系爭要件的相反事實(shí)形成確信,法院即可認(rèn)定要件事實(shí)存在并依此進(jìn)行裁判。僅僅因?yàn)榘l(fā)生證明妨礙的行為而一律使證明責(zé)任發(fā)生轉(zhuǎn)換,毫不考慮如果不存在證明妨礙行為法官是否依舊無法對要件事實(shí)的存在形成確信,此等立論似乎需要再作討論。事實(shí)上,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此等過于形式化的作法,就裁判結(jié)果而言確有不當(dāng)。相對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自由心證說即可靈活因應(yīng)具體個案多變的狀況,有助于實(shí)現(xiàn)個案的正義。
其三,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不區(qū)分故意或過失,一律使證明責(zé)任發(fā)生轉(zhuǎn)換,此等機(jī)械化的作法也有欠妥當(dāng)。依據(jù)自由心證說,不僅可以區(qū)分當(dāng)事人主觀的狀態(tài)而進(jìn)行彈性處理,另一方面,更可細(xì)化過失的種類,針對重大過失、輕過失等不同類型而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
(三)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說
德國將民事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設(shè)定為確信真實(shí)或高度蓋然性的標(biāo)準(zhǔn),由于設(shè)定較高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以至于在司法實(shí)踐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無法實(shí)現(xiàn)立法主旨、具體的正義以及適用法規(guī)范目的的情形。因此,有必要依據(jù)糾紛的類型和具體案件的不同,為實(shí)現(xiàn)立法的目的和具體的正義在特定情形下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減輕證明責(zé)任。在德國民事訴訟中,有關(guān)表見證明的判例和理論基礎(chǔ)應(yīng)運(yùn)而生。受德國理論的影響,日本也發(fā)展出“大致推定”的理論以實(shí)現(xiàn)減輕當(dāng)事人證明負(fù)擔(dān)的目的。
1、德國
具體至證明妨礙領(lǐng)域,在一方當(dāng)事人就對方當(dāng)事人證明事實(shí)所需的證據(jù)實(shí)施證明妨礙行為時,對方當(dāng)事人因無法接近、使用該證據(jù),往往發(fā)生無從使法院就自己所主張的事實(shí)形成確信心證的情況,進(jìn)而導(dǎo)致其敗訴。因此,有學(xué)者倡議將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在降低程度的選擇上則須考量證明妨礙行為人的主觀可歸責(zé)性。提出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的想法主要也是著眼于如果一律以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作為證明妨礙的效果不具備彈性及過于僵化,并且在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反而侵害當(dāng)事人之間的公平時,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降低可以滿足這種情形。德國學(xué)界有少數(shù)持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說的學(xué)者將自由心證理解為依據(jù)自由裁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確定,并以優(yōu)越蓋然性作為其認(rèn)定事實(sh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德國學(xué)者Baumggrtel則主張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分層(Ab—stufung des BeweismaBes)理論,其認(rèn)為主張自由心證說的,不免會賦予法院必要的裁量空間,以便在不同個案中作適當(dāng)?shù)倪x擇。但是為了保全可預(yù)測性的原則,仍然應(yīng)當(dāng)尋找若干標(biāo)準(zhǔn)定其分界。此等標(biāo)準(zhǔn)的認(rèn)定當(dāng)自可歸責(zé)性程度出發(fā)。詳言之,對于故意的證明妨礙行為,法院基本上可以將負(fù)證明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所主張的事實(shí)認(rèn)定為真實(shí),即可以將故意的證明妨礙行為作為擬制舉證者主張事實(shí)為真實(shí)的憑證。對于重大過失的證明妨礙行為,法院根據(jù)低度蓋然性(eine geringe Wahrscheinlichkeit)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可認(rèn)定當(dāng)事人所主張的事實(shí)為真實(shí)。對于輕過失的證明妨礙行為,法院根據(jù)優(yōu)越蓋然性(eine iiberwiegende Wahrscheinlichkeit)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可認(rèn)定當(dāng)事人所主張的事實(shí)為真實(shí)。除了上述原則外,仍然可能存在其他例外情形,于該等情形,即使將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至低度蓋然性于當(dāng)事人仍屬不公時,也可能有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的必要。例如,當(dāng)醫(yī)生違反了文書保管義務(wù)時,因該等文書的制作、保存、提出均由醫(yī)生控制,而并非患者所能影響,所以有必要將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但其認(rèn)為此等例外類型,仍須由實(shí)務(wù)學(xué)說建立類型,以確保法治國法律安定性原則的要求。
2、日本
受德國學(xué)者Baumgartel的影響,日本學(xué)者伊藤真認(rèn)為,從與當(dāng)事人證明活動相關(guān)的事實(shí)出發(fā),推導(dǎo)出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甚為困難。毋寧認(rèn)為,一般而言,由于證明妨礙行為使得證據(jù)調(diào)查不可能,所以如果法院即便基于負(fù)證明責(zé)任當(dāng)事人的舉證行為不能形成有關(guān)事實(shí)的內(nèi)心確信時,也可以較低的心證度認(rèn)定該事實(shí)。因而,應(yīng)當(dāng)考慮將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其同時認(rèn)為,與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不同的是,證明主題即便是間接事實(shí)與輔助事實(shí),也能產(chǎn)生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法律效果。
學(xué)者加藤新太郎認(rèn)為,之所以提出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構(gòu)想,最初主要是為了克服現(xiàn)實(shí)民事訴訟中因證據(jù)偏向存在或案情性質(zhì)而產(chǎn)生的證明困難,此種證明困難與通說采取“無合理懷疑的確信”作為原則上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相結(jié)合,有時反而造成當(dāng)事人實(shí)體法上權(quán)利無從實(shí)現(xiàn)的不當(dāng)判決。詳言之,證明標(biāo)準(zhǔn)成為了因案件證據(jù)偏向存在產(chǎn)生不公平和阻礙案件真實(shí)發(fā)現(xiàn)的幫兇。為了實(shí)體法適用前提而進(jìn)行的事實(shí)認(rèn)定程序依據(jù)原則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要求,卻招來抹煞實(shí)體法旨趣的違反實(shí)體正義的結(jié)果和忽略當(dāng)事人實(shí)質(zhì)平等的違反程序正義的結(jié)果。因而,基于實(shí)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于適當(dāng)情形可以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加藤新太郎進(jìn)而嘗試就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所需的要件進(jìn)行論述,其認(rèn)為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的容許要件應(yīng)以必要性、相當(dāng)性、補(bǔ)充性為基礎(chǔ),具體言之應(yīng)當(dāng)具備以下要件:一,事實(shí)的證明有性質(zhì)上的困難;二,證明困難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依據(jù)實(shí)體法規(guī)范目的旨趣會出現(xiàn)顯著的不正義;三,原則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并無等價值證明的替代方案。符合以上要件時,法律效果原則上應(yīng)將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至相當(dāng)于“證據(jù)優(yōu)越(五分五分)”的程度。
3、我國臺灣地區(qū)
在我國臺灣地區(qū),學(xué)者許士宦認(rèn)為其“民事訴訟法”第282條第1款既然沒有明文肯定可以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那么應(yīng)當(dāng)以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作為其法律效果以達(dá)到證明妨礙的立法目的。就證明妨礙的行為態(tài)樣而言,可以依據(jù)當(dāng)事人的可歸責(zé)程度,區(qū)分各階層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一方面使法院享有基于自由心證主義所必要的裁量,而在具體事例能于證據(jù)法上正確反映證明妨礙的事實(shí);另一方面為確保當(dāng)事人的預(yù)見可能性,設(shè)定法院反映各種類證明妨礙的基準(zhǔn)。換言之,其運(yùn)作的標(biāo)準(zhǔn)可以依據(jù)妨礙者主觀可歸責(zé)的程度進(jìn)行區(qū)別對待。當(dāng)一方當(dāng)事人故意實(shí)施證明妨礙時,通常可以將其作為對方當(dāng)事人主張的依據(jù),利用“當(dāng)事人之所以故意妨礙證明,實(shí)由于恐其被使用致使對方當(dāng)事人的主張獲得證明,而使自己蒙受不利益”的經(jīng)驗(yàn)法則,推認(rèn)對方當(dāng)事人的主張為真實(shí);而當(dāng)一方當(dāng)事人具有過失時,輕過失的證明妨礙不能與重大過失的證明妨礙降低至同樣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如于輕過失的情形要求優(yōu)越的蓋然性即可,則于重大過失的情形僅要求低度的蓋然性即為已足。但是,在上述情形,即使將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至低度蓋然性,仍不能正確評價當(dāng)事人的證明困難的,即應(yīng)當(dāng)考慮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
另有學(xué)者黃國昌先生不贊同上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分級理論,其認(rèn)為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擇定應(yīng)當(dāng)取向于“對被妨礙者所造成的不公平程度”,亦即考慮的焦點(diǎn)應(yīng)置于“如該證據(jù)存在對被妨礙者的證明活動所將產(chǎn)生的影響”,而非“妨礙者的主觀歸責(zé)程度”。自此而論,學(xué)說上將判斷的重點(diǎn)置于“主觀歸責(zé)要件”,并依其程度的高低,擇定強(qiáng)弱不同的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見解,有再加檢討的必要。詳言之,在系爭證據(jù)未提出的狀況下,的確產(chǎn)生法院無從得知其確切內(nèi)容的現(xiàn)實(shí)上的困難。此時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是應(yīng)當(dāng)遵循何種基準(zhǔn)判斷其對待證事實(shí)認(rèn)定的影響。黃國昌先生認(rèn)為,法院判斷的重心應(yīng)當(dāng)置于“妨礙行為對被妨礙者所造成的不公平程度”。而此不公平程度,必須由被妨礙者負(fù)證據(jù)提出責(zé)任加以顯示,其所顯示的不公平程度越高,法院越得以施加較強(qiáng)的法律效果,以回復(fù)當(dāng)事人之間的公平。在此所謂“不公平程度的顯示”,是指法院可以依被妨礙者所提出的證據(jù),就“未提出的證據(jù)”對“認(rèn)定待證事實(shí)的重要性”加以“形式上客觀判斷”,作為其行使裁量權(quán)以擇定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基準(zhǔn)。至于妨礙者的主觀可歸責(zé)性是定位在“被妨礙證據(jù)的重要性的征表”以及“達(dá)成制裁目標(biāo)的工具”兩方面。此說在其關(guān)于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選擇中,似亦未贊同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說。
4、祖國大陸
祖國大陸學(xué)者基本不贊成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說。張衛(wèi)平教授認(rèn)為,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qū)相當(dāng)一部分學(xué)者的觀點(diǎn)是,通過降低當(dāng)事人證明標(biāo)準(zhǔn),使得當(dāng)事人即使缺乏某些證據(jù)時也能夠?qū)崿F(xiàn)其主張的證明。對方當(dāng)事人實(shí)施證明妨礙行為的結(jié)果往往是使負(fù)有證明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在證明時無法達(dá)到所要求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從而使自己處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如果能夠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這種受妨礙的損失就會因此降低,也同樣能夠保障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張衛(wèi)平教授進(jìn)而認(rèn)為,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必須有一個前提,即法官對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把握可以自由裁量,如果不能自由裁量,也就無法根據(jù)個案情況適用證明標(biāo)準(zhǔn)。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按照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qū)的通說為“高度蓋然性”,是指當(dāng)事人的證明雖然沒有達(dá)到使法官對待事實(shí)確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經(jīng)相信存在極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而如何把握所謂高度蓋然性,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將證明標(biāo)準(zhǔn)從“高度蓋然性”降為“中度蓋然性”或“低度蓋然性”,也同樣需要法官根據(jù)具體情況自由裁量,因?yàn)椤暗投壬w然性”、“中度蓋然性”以及“高度蓋然性”之間的差異并非十分明晰,尤其是在相近蓋然性之間。而究竟是降為低度蓋然性,還是中度蓋然性,也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不過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目前在我國是否行得通,是有疑問的。一方面,盡管訴訟實(shí)踐中實(shí)際存在著法官自由裁量,但人們的觀念和正統(tǒng)的法理并未認(rèn)可自由心證原則;另一方面,缺乏社會對法官素質(zhì)和品性充分和廣泛的信任,法官對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自由判斷,必將遭受人們強(qiáng)烈的質(zhì)疑。因此,張衛(wèi)平教授認(rèn)為此對策恐非良策。
湯維建教授認(rèn)為,既然僅僅在案件事實(shí)處于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下才構(gòu)成證明妨礙,現(xiàn)在通過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方法查明案件事實(shí),那么前述行為還能否被視為是證明妨礙行為便值得推敲。況且,證明標(biāo)準(zhǔn)本身就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如何衡量法官內(nèi)心的確信程度本身就難以把握,更不論從一個層次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為另一個層次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在案件的實(shí)際操作中,證明活動需要借助于法官的內(nèi)心活動來實(shí)現(xiàn);高度蓋然性、中度蓋然性等證明標(biāo)準(zhǔn)層次的界限模糊不清,缺乏可操作的量化指標(biāo),易受法官的主觀影響。因此,與其通過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方法制裁妨礙者,不如由法官直接自由裁量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
(四)其他學(xué)說
1、折中說
另有采折中說的學(xué)者認(rèn)為,在遇有證明妨礙情形時,發(fā)生可達(dá)到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證明減輕效果。亦即,原則上減輕舉證人的證明責(zé)任,但是于妨礙者的目標(biāo)是使舉證人不能證明的情形,則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此項(xiàng)見解承認(rèn)從證明減輕到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廣泛效果,固然較能適應(yīng)各種證明妨礙的形態(tài)。但是正因如此,也容易發(fā)生法律上不安定的危險,因?yàn)閷Ξ?dāng)事人而言,究竟是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抑或止于證明減輕,難以預(yù)見。為免致此,仍須開發(fā)應(yīng)承認(rèn)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典型案例群,并就各種證明減輕予以類型化。簡言之,折中說的觀點(diǎn)為在民事訴訟中發(fā)生證明妨礙行為時,給予法院廣泛的自由裁量權(quán),使其可以針對個案的不同,從自由心證、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直至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等法律效果中擇一使用。
2、擬制自認(rèn)說
在德國,學(xué)者施蒂爾納主張“可推翻的不利擬制說”,即認(rèn)為若不負(fù)證明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有證明妨礙行為的,則應(yīng)將負(fù)證明責(zé)任的一方當(dāng)事人所提出的主張視為被自認(rèn)或視為已被證明。僅僅當(dāng)法院對相對事實(shí)獲得確信,或在較輕微證明妨礙者能獲得優(yōu)越性的確信時,主要事實(shí)的真正擬制才被推翻。自此以后,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出現(xiàn)了擬制自認(rèn)說,即當(dāng)一方當(dāng)事人的證明妨礙行為造成對方當(dāng)事人證明困難或證明不能時,視為其承認(rèn)對方當(dāng)事人提出的事實(shí)主張。
當(dāng)事人在言詞辯論中,對對方當(dāng)事人主張的事實(shí)無明顯的爭議,并且根據(jù)全部辯論的內(nèi)容認(rèn)定也無爭議時,該事實(shí)視為自認(rèn),這就是所謂的擬制自認(rèn)。法律擬制為自認(rèn)者,意味著其無需依據(jù)證據(jù)加以認(rèn)定,且就法院受到須將其采為裁判依據(jù)的羈束力這點(diǎn)而言,其與自認(rèn)相同。在此作為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自認(rèn)并非一方當(dāng)事人對對方當(dāng)事人陳述事實(shí)的明確承認(rèn),而是一種擬制自認(rèn)。在訴訟中,一般不會發(fā)生妨礙者就被妨礙者主張的事實(shí)明確表示承認(rèn)的情況,因?yàn)槿绻恋K者意欲就被妨礙者主張的事實(shí)明確表示承認(rèn)的話,其便無需實(shí)施證明妨礙。因而,在妨礙者實(shí)施了證明妨礙行為且未就被妨礙者主張的事實(shí)明確表示承認(rèn)時,擬制其已經(jīng)自認(rèn)被妨礙者主張的事實(shí)便作為對其證明妨礙行為的懲罰。
有學(xué)者認(rèn)為,與推定主張成立相比,擬制自認(rèn)無需推定所需要的前提條件,如經(jīng)驗(yàn)法則。從理論上講,作為推定成立的事實(shí)主張,如果有相反的證據(jù)能夠加以證明時,推定的事實(shí)不能成立,當(dāng)事人仍然需要對主張的事實(shí)加以證明,亦即,推定的主張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民事證據(jù)規(guī)定》)第9條規(guī)定,推定的事實(shí),如果對方當(dāng)事人有相反的證據(jù)足以推翻時,當(dāng)事人依然需要對主張的事實(shí)加以證明。擬制自認(rèn)就不存在這一問題。但擬制自認(rèn)與自認(rèn)的基本含義相差較大,實(shí)際上擬制自認(rèn),不過是想取得自認(rèn)的效果,即免除主張者對主張事實(shí)加以證明而已,因此,在制度上還不如直接規(guī)定免除當(dāng)事人的證明責(zé)任以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救濟(jì)來得自然。因此,該學(xué)者認(rèn)為擬制自認(rèn)也并非規(guī)制證明妨礙的上策。
3、推定主張成立說
從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民事訴訟立法規(guī)定來看,推定主張成立說獲得了諸多國家或地區(qū)民事訴訟立法者的青睞。再者,從上述規(guī)定的表述來看,推定對方當(dāng)事人的主張成立應(yīng)當(dāng)屬于證據(jù)推定的一種。理論上一般認(rèn)為推定的根據(jù)是依據(jù)經(jīng)驗(yàn)法則推定該證據(jù)有利于對方當(dāng)事人。而該經(jīng)驗(yàn)法則為:在一般情形下,如果是對自己有利的證據(jù),當(dāng)事人沒有理由拒不提供;正是因?yàn)閷ψ约翰焕艧o正當(dāng)理由拒不提供。
也有學(xué)者質(zhì)疑推定主張成立說,認(rèn)為如果證據(jù)持有人拒不提供證據(jù)材料,便一律推定對方關(guān)于證據(jù)內(nèi)容的主張成立,那是否過于主觀?而且對方主張什么就是什么,這也并非合理。其實(shí)這種情形發(fā)生的可能性很小。在證據(jù)內(nèi)容方面,不外乎兩個方面:一為是否存在某種事實(shí);二為在存在某種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還存在量的問題,即證據(jù)內(nèi)容涉及數(shù)量的確定問題。容易發(fā)生與客觀事實(shí)不一致的情形主要在數(shù)量方面。例如,一方當(dāng)事人認(rèn)為對方當(dāng)事人持有的證據(jù)——收據(jù)可以證明所欠數(shù)額為5萬元,而對方認(rèn)為,收據(jù)已經(jīng)丟失無法提出。此時,按照《民事證據(jù)規(guī)定》,當(dāng)事人關(guān)于債務(wù)數(shù)額為5萬元的主張便可以成立。這樣會不會導(dǎo)致主張的隨意性,而完全偏離案件的真實(shí)呢?這里應(yīng)當(dāng)說明的是,即使提出主張的當(dāng)事人在訴訟一開始就預(yù)料對方當(dāng)事人會拒絕提出證據(jù),也不大可能提出一個大大超出真實(shí)數(shù)額的主張,因?yàn)橐坏┐蟠蟪^,使對方當(dāng)事人蒙受大的損失,對方當(dāng)事人如有證據(jù)在手,必然出示證據(jù)加以證明。在對方當(dāng)事人拒絕提出證據(jù)后,提出主張的當(dāng)事人想借此變更事實(shí)主張是不被允許的,審判人員能夠判斷該行為的企圖。當(dāng)然,也不排除提出主張的當(dāng)事人事先將對方持有的證據(jù)盜走或銷毀,然后提出一個預(yù)謀的債權(quán)數(shù)額,由于對方當(dāng)事人無法提出證據(jù)而使自己的主張推定成立,但這種情形如果數(shù)額很大則已經(jīng)構(gòu)成刑事犯罪,將被納入另外一種程序,不是民事訴訟程序所要解決的問題。
4、強(qiáng)制措施說
民事訴訟強(qiáng)制措施是指為了維護(hù)民事訴訟程序的正常進(jìn)行而由法律規(guī)定的、對有妨害訴訟行為的人實(shí)施的帶有強(qiáng)制性的排除措施。從立法規(guī)定而言,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qū)對于證明妨礙行為均有采取強(qiáng)制措施的規(guī)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72條第1款規(guī)定,在有確定血統(tǒng)關(guān)系的必要時,任何人(不僅包括訴訟當(dāng)事人,連第三人特別是當(dāng)事人的近親屬)都有受檢查的義務(wù),特別是有為查明血型而容忍抽血的義務(wù)。無正當(dāng)理由而再次拒絕檢查時,可以直接予以強(qiáng)制,特別是為了檢查,可以命令拘傳。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35條規(guī)定,訴訟外的第三人無正當(dāng)理由違反文書提出命令的,法院可以對其處以2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與舊法規(guī)定的10萬元相比增加了一倍。我國臺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349條對于無正當(dāng)理由不服從文書提出命令的第三人,規(guī)定了兩種制裁方式:其一為法院可以裁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的罰款;其二為有必要時法院可以裁定命為強(qiáng)制處分。其強(qiáng)制處分的內(nèi)容,是對于不服從文書提出命令的第三人,由法院以強(qiáng)制的方式取出,相當(dāng)于“強(qiáng)制執(zhí)行法”中關(guān)于物之交付請求權(quán)的執(zhí)行,并準(zhǔn)用該規(guī)定。
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章中就規(guī)定了一系列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qiáng)制措施。《民事訴訟法》第102條中規(guī)定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行為即屬于證明妨礙的行為。在民事訴訟實(shí)務(wù)中,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尤其是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的情況。一般情形是,當(dāng)事人向法院提出證人名單后,該證人由于對方當(dāng)事人的阻礙而不愿或不能出庭作證。在民事訴訟法中,這些妨害行為被歸入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其違法性被界定在對民事訴訟秩序的妨害這一層面。對此,采取的對策是,法院可以對行為人處以罰款、拘留等措施。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zé)任。正因?yàn)閷⑦@些行為作為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一種,因此,在措施上也就必然以維護(hù)民事訴訟秩序正常進(jìn)行為主要目的,主要是通過懲戒達(dá)到一般預(yù)防的目的,不可能具體考慮證明妨礙的救濟(jì)問題,這也使得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在消除妨礙證明影響方面的對策尚有較大的局限性。
三、證明妨礙法律效果主要學(xué)說之評析
(一)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
首先,就證明妨礙是否可以以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作為法律效果而言,理論界和實(shí)務(wù)界大多持肯定見解,本文也表示贊成。而且,我國《民事證據(jù)規(guī)定》第7條明確規(guī)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guī)定,依本規(guī)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zé)任承擔(dān)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jù)公平原則和誠實(shí)信用原則,綜合當(dāng)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zé)任的承擔(dān)。”由于民事訴訟案件千變?nèi)f化,所以在證明責(zé)任分配上要完全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權(quán)并非現(xiàn)實(shí)。“當(dāng)然,承認(rèn)法官在證明責(zé)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權(quán)并不意味著法官可以在相當(dāng)多的案件中置法律規(guī)定的一般規(guī)則和倒置規(guī)則于不顧,而依自己的感覺任意地分配證明責(zé)任,證明責(zé)任的自由裁量規(guī)則只應(yīng)在極為特殊的情形下方可適用。”在訴訟中出現(xiàn)顯失公平的證明妨礙情形,就屬于這里所說的_極為特殊的情形。此時,法院可以根據(jù)公平原則和誠實(shí)信用原則,將證明責(zé)任的分配規(guī)則作出一定的調(diào)整,由妨礙者就被妨礙證明的事實(shí)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
其次,雖然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承認(rèn)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但是究竟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并無確切規(guī)定,所以還需要法院在審理時依據(jù)個案情形妥善斟酌適用。希望今后適用的案例達(dá)到一定數(shù)量之后,可以建立類型化的模式,這樣也有助于法律程序上的安定。至于因訴訟程序中轉(zhuǎn)換客觀證明責(zé)任可能造成程序的不安定,本文認(rèn)為,可以通過法院的闡明,讓當(dāng)事人事先知曉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情形,這樣可以防止當(dāng)事人受到突襲性裁判。
再次,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選定應(yīng)當(dāng)考慮妨礙者主觀方面的差異。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相對于自由心證或者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而言,屬于較為嚴(yán)重的法律效果,所以遇有故意證明妨礙的情形時才可以適用。實(shí)施證明妨礙的當(dāng)事人既然以故意心態(tài)毀滅、隱匿證據(jù),其惡性昭然若揭,可以處以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法律效果。遇有過失證明妨礙的情形時,可以考慮選擇諸如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等法律效果。
(二)自由心證說
相對于較為僵化的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說,自由心證說的優(yōu)點(diǎn)在于其靈活性。也有學(xué)者質(zhì)疑如果將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求諸于自由心證說,是否會由于完全聽任法官自由心證的運(yùn)作而使證明妨礙理論完全失去意義?本文認(rèn)為不然。因?yàn)榧幢闶遣捎米杂尚淖C主義,法官的心證也并非如野馬脫疆般毫無限制,通過證明妨礙理論的建立,將更有助于當(dāng)事人預(yù)測法院可能的心證走向。
自由心證說原則上要求法院應(yīng)當(dāng)將證明妨礙的行為與其他證據(jù)調(diào)查的結(jié)果綜合評價而認(rèn)定事實(shí)。在當(dāng)事人有證明妨礙的行為時,應(yīng)當(dāng)就當(dāng)事人是故意或過失、該被毀棄隱匿的證據(jù)是否屬于唯一證據(jù)、當(dāng)事人是否提出反證、在何等范圍內(nèi)決定法律效果可避免使被妨礙者獲取過度的利益等等因素進(jìn)行考量,酌定妨礙者應(yīng)得的法律效果。
(三)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說
當(dāng)訴訟中發(fā)生證明妨礙時,通常被隱匿毀滅的證據(jù)皆為重要的、能夠證明主要事實(shí)的證據(jù)。一旦證據(jù)被銷毀,往往會立刻引起被妨礙者證明困難或證明不能,從而導(dǎo)致其敗訴。而且,訴訟的勝敗不能取決于證據(jù)偏向存在甚至是證明妨礙,否則即不符合當(dāng)事人實(shí)質(zhì)的武器平等原則。而如果被妨礙的證據(jù)是重要或甚至唯一的證據(jù),當(dāng)事人也不可能再提出其他等價的證據(jù)方法,這也是訴訟中證明妨礙最常遇見的情況。因此,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妨礙行為基本上都能符合上述加藤教授闡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的三要件,從而,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可以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應(yīng)無疑問。在實(shí)際的操作方面,學(xué)者就證明標(biāo)準(zhǔn)分層的基準(zhǔn)見解不一。
本文認(rèn)為,雖然學(xué)說上常有將證明標(biāo)準(zhǔn)以數(shù)字量化,但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問題應(yīng)當(dāng)屬于價值判斷的問題,而并非單純的數(shù)字或機(jī)率。詳言之,有學(xué)者認(rèn)為當(dāng)事人主觀可歸責(zé)性可作為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的分層依據(jù),也有認(rèn)為重點(diǎn)在于當(dāng)事人之間不公平的程度,主觀可歸責(zé)性只是判斷不公平程度的依據(jù)之一。但其實(shí)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作為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其降低程度所應(yīng)考慮的要素本來就不只當(dāng)事人主觀可歸責(zé)性,而是必須依據(jù)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所需要件,例如因證明妨礙行為造成當(dāng)事人多大程度的證明困難,綜合判斷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的多寡,才能應(yīng)付各種各樣的訴訟情形。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的程度是綜合所有證據(jù)調(diào)查結(jié)果而進(jìn)行價值判斷,而且證明標(biāo)準(zhǔn)降低也常與自由心證相結(jié)合。
四、結(jié)論:證明妨礙法律效果的多元化適用
基于“自由心證的終點(diǎn)即證明責(zé)任的起點(diǎn)”,原則上在訴訟過程中如果遇有待證事實(shí)陷于真?zhèn)尾幻鞯那闆r,法院應(yīng)當(dāng)優(yōu)先適用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公平分配敗訴風(fēng)險。然而,在例外情況下,本案待證事實(shí)之所以陷于真?zhèn)尾幻鳎浅鲇诋?dāng)事人實(shí)施的證明妨礙行為所致,如果此時仍然根據(jù)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作出裁判,恐將打破當(dāng)事人之間的實(shí)質(zhì)平等。為了貫徹訴訟法上的誠實(shí)信用原則,在當(dāng)事人實(shí)施證明妨礙行為時,法院即應(yīng)當(dāng)適用證明妨礙理論以回復(fù)雙方當(dāng)事人不平等的訴訟地位。
至于證明妨礙的法律效果,本文認(rèn)為,不宜采取劃一性的方式制裁妨礙者。雖然采取劃一性的方式制裁妨礙者,可以使法院的裁判變得簡單、快捷并富有預(yù)見性,但是其弊端為法院無法根據(jù)證明妨礙行為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來靈活地作出不同的處理。當(dāng)事人主張對自己有利的事實(shí)或者反駁對方當(dāng)事人主張的事實(shí)均必須提供證據(jù)加以證明。從邏輯上分析,即使證據(jù)持有人按照舉證人的要求提交了相關(guān)的證據(jù)材料,沒有證明妨礙行為,舉證人所主張的事實(shí)也未必成立,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可能依舊存在。換言之,造成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鞯脑蚧蛟S不止一個,即使證據(jù)持有人拒不提供證據(jù),也不能將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鞯木売赏耆珰w于證明妨礙行為。再者,在民事訴訟實(shí)踐中,證明妨礙行為形態(tài)各異,妨礙程度也各不相同,如果一律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或者采取某一種制裁措施,既不符合審判規(guī)律的客觀性,也不利于案件客觀真實(shí)的發(fā)現(xiàn)。
本文進(jìn)而認(rèn)為,不論妨礙者出于故意、重大過失乃至于輕過失而實(shí)施證明妨礙行為,法官基于證明妨礙的行為態(tài)樣、行為人可歸責(zé)的程度及所妨礙的證據(jù)方法對查明待證事實(shí)的重要程度等因素進(jìn)行綜合考量,是出于自己內(nèi)心的自由評價。換言之,法院應(yīng)當(dāng)本著誠實(shí)信用原則,仔細(xì)斟酌妨礙者的主觀心態(tài)、實(shí)施方式、可歸責(zé)程度及被妨礙證據(jù)的重要性等因素,在結(jié)合其他證據(jù)的基礎(chǔ)上采取自由心證的方式對事實(shí)作出認(rèn)定。亦即,此時法院可以選擇應(yīng)當(dāng)推定舉證人的主張為真實(shí)、或者直接認(rèn)定妨礙者擬制自認(rèn),或者針對該等事實(shí)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甚至在必要時轉(zhuǎn)換證明責(zé)任,或者采取罰款、拘留或直接強(qiáng)制等強(qiáng)制措施。如此一來,法院更能彈性因應(yīng)各個具體案件,更能在法律效果的制裁上適度反映出不同案件的不同處理。當(dāng)然,多元化法律效果的適用勢必會弱化法院裁判的可預(yù)見性。因而,為了保障當(dāng)事人的法定聽審請求權(quán),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應(yīng)當(dāng)令當(dāng)事人有辯論的機(jī)會。
參考文獻(xiàn):
[1]E·博登海默.法理學(xué)、法律哲學(xué)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344.

<img src="https://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mlaw/mlaw201105/mlaw20110509-2-l.jpg?auth_key=1736838625-348638782-0-82d6925db2e77def4081f6b967a01004" hspace="15" vspace="5" 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