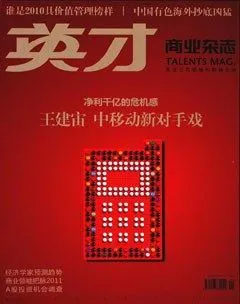有人就有秘密
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幾年前挑戰了一個真理。他說,世界是平的。
這可能是本世紀以來(盡管本世紀過去才僅僅十年)一個最有趣的社會學觀點。《世界是平的》一書出版發行之后,弗里德曼便成了大師。“世界的格局驟然變平了,從溝通到實現,從設想到傳播,一切都理所當然,如履平地”,弗里德曼說。
是的,我們現在正在用一只小小的鼠標操控著世界,這是新技術時代的必然風景:“鼠標輕點,不管身在何處都能輕易調動世界的產業鏈條。”這就是佛里德曼所
說的全球化進程中的最高階段,即“全球化3.0”時代。
在2010年的最后一個月里,全世界的人都在熱議著“秘密”和“解密”的話題。這個話題的焦點涉及一個名叫朱利安·阿桑奇的傳奇人物。
朱利安·阿桑奇是維基解密的創始人。其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正是弗里德曼學說的生動證明,他以一種“如履平地”的方式,不僅向世人證明了“世界是平的”,他還用使人震驚的“解密”業績向我們宣告:世界是透明的。巧合的是,阿桑奇曾經也是一名記者,跟弗里德曼一樣。
維基解密作為一家解密政府秘密和敏感文件的專業網站,在過去的一年當中可謂是出盡了風頭。在這一年中,維基解密先后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保存的逾47.7萬份秘密文件公之于眾,在國際社會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2010年11月,維基解密又將超過20萬份美國外交加密文件對外公布。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阿桑奇的維基解密正在讓美國政府裸奔,他將美國政府的秘密信息透明化了。
維基解密成立于2006年12月,其建站的宗旨就是為了“揭露政府及企業的腐敗行為”。在此之前的2005年,《世界是平的》剛剛問世。
如果說弗里德曼的理論給人帶來的是一種嶄新的全球化視覺和驚喜,那么阿桑奇的解密行動給人帶來的則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感,或者說是恐慌。試想,如果世界真的變成透明的,我們該如何自處?信息自由和信息安全之間的界限在哪里?公眾知情權的邊界又在哪里?
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仍在繼續,且角度各異。而我在這里要著重探討的是,維基解密事件留給商業世界的啟示。
阿桑奇解密行動的落腳點之一、也就是維基解密網站存在的價值是,要向那些“缺乏職業道德的公司”征收代價高昂的“名譽稅”。為此,維基解密曾宣稱將于2011年初拋出一枚重磅炸彈。這枚炸彈將涉及美國多家銀行和財團的內幕丑聞,其殺傷力將完全不輸給當年的“安然丑聞”。
不得不承認,盡管維基解密的行為定性讓世人眾說不一,但阿桑奇還算是一個相對單純的人,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創造符合道德規范的事業”。這是他的理想,聽起來有些“俠”的味道。
其實,維基解密所具備的功能價值使得網站自身有著“工具化”的特質,而工具是中性的,本身無所謂好與壞的界定。這就像是一把菜刀一樣,是被視為一件普通的廚具,還是被當成一把鋒利的兇器,這取決于使用它的動機和目的。
那么,在我們的公司周圍,有沒有潛伏著行蹤不定且動機不純的“維基解密”呢?
如果你好奇地觀察過一些轟轟烈烈的商業戰爭,相信你就一定能在斗爭雙方你來我往的對弈中聞到“維基解密”的味道,一些公司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機密總是會鬼魅地出現在各大商業報紙上。
“維基解密”無處不在。它可能是因為競爭對手公司的奸細混進了內部,竊取了機密——比如豐田“召回門”里的那位名叫比勒的“潛伏者”,最早受雇于福特,2003年才加盟到豐田;也有可能是公司“內鬼”在倒賣有用信息,比如“力拓間諜門”;或者是違背競業禁止的高管投奔對手所造成的信息泄密——例如2009年,I B M指控負責并購事務的前高管大衛·約翰遜加盟戴爾,因為“約翰遜掌握著大量商業機密”;又或者是違反保密協議的咨詢服務公司故意泄密,賺取不義之財……除此之外,目前國內活躍著的一大批專業的商業調查公司,也是公司秘密曝光的一大管道。
面對這樣的現實,企業首先要做的恐怕就是設立“首席安全官”(CSO),為企業搭建一套全方位的信息安全保密系統,比如建立嚴格的公司保密制度,對各類信息進行安全分級,對公司進行全方位的安全體檢等有效措施。作為一名合格的公司C S O,他應該最為清楚公司信息的漏洞所在,并事先準備好一套盡可能完善的應急處理方案。
任何事件、任何信息都會在三個維度上進行定性,即合情、合理、合法。如果定性是負面的,那就是不合情、不合理和不合法,縱觀那些商業口水戰中所炮制出來的種種“猛料”,大多跟這“三不”有關。所以,作為公司的首席安全官,就必須對自身的“三不”有著清晰的認知和評估。
按照最為常規的認識,法律問題應該是彈性很小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不合法”的問題之上,并不存在太多的商討空間,也為此,法律才是解決爭端的終極手段。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繁多的商業競爭口水戰中,法律問題卻總是能退避三舍:你告我盜版,我就反告你盜版;你訴我侵權,我就反訴你侵權;你說我壟斷,我就說你也是壟斷……問題的是非曲直就這樣在拉鋸中被擱置了,轉而演變成了一場場情緒之戰,一場場民意爭奪之戰。“不合情”和“不合理”的公司行為,最終往往反而喧賓奪主,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這也無可厚非,輿論不是法庭,它有是非曲直判斷的缺失性。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無論是仕文化,還是商文化,或者是政治文化,都存在一些既定的傾向,這種傾向造就了認知思維上的慣性,好像情理之外的事情讓人更難以接受。畢竟,民眾不是法官,他們有的只是情緒。
以上這些怪誕的現狀,也是“安全官”要充分認知的,這對信息分級和信息評估有著很現實的參考價值。
世界正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變得越來越透明,我們應該學會如何在透明的玻璃屋子里生存。這是維基解密案留給我們的啟示,“保密”不一定就意味著陰暗,我們都有經營“陽光公司”的良好愿望,但在公司的發展過程當中,有成長就會有煩惱,有煩惱就會做錯事,就會有這樣和那樣的原罪。是人就會有秘密,公司也是。
維基解密之所以能在2010年的最后一個月里讓全球皆知,主要是因為在12月7日這一天,阿桑奇在英國倫敦鋃鐺入獄了,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性侵犯”和“性騷擾”。
這可能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陰謀。套用坊間的說法,阿桑奇是被“技術性立案”了。
(作者系盛世原道咨詢機構總裁,合伙人,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