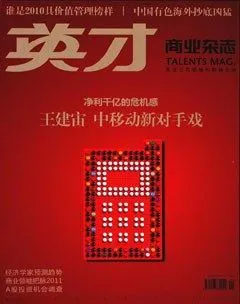江平:以社會自治代替國家強制
2011-01-01 00:00:00
英才 2011年1期

演講人|知名法學家江平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寫進了中國《憲法》,法制也寫進了中國《憲法》,但是市場和法制在《憲法》里的表述都有一個前置詞,即社會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法制。為什么要在《憲法》中寫進社會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法制呢?因為可以求得最大的公約數,即求得更多的人能夠贊同此理念。
既然是最大公約數,就必然存在很多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市場經濟模式下,國家的作用和市場規范的作用各自能起多大作用。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也有人認為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爭論的焦點。那么,國家這只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二者究竟有何不同?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國家宏觀政策作為調控市場經濟的主要手段,30年來被過多地強調,而輕視了社會自己的作用。強調國家作用,就是用國家的強制力干預社會各個方面,包括經濟、教育、家庭,甚至個人的生活方式等。而市場經濟則是要解決市場的自治、企業的自治和社會的自治。以社會自治來代替國家強制,這也是改革的中心思想。
其次,市場經濟下國家這只手的作用在不同地域、不同領域應該有所區分。眾所周知,市場以社會自治代替國家強制自由和市場秩序是構成市場本身活動和法制的最大結合點。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都離不開國家這只手,但是過去國家這只手更多的放在了市場自由這一領域,而在市場秩序領域方面所起的作用較小。
市場自由是需要法律調整的。目前,民營企業享受的自由比過去多,但相對于西方國家的市場自由而言還是很少,為什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在市場自由領域的作用過多,應該減少其在這方面的積極性。或者是在資源分配,以及市場準入方面,國家應該盡量少地參與。
另外,市場秩序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目前,中國在市場秩序方面的國際排名還是很靠后的。這意味著,在市場秩序領域里,應該有國家法律和國家執法部門的介入,才能使得市場秩序更加完好。
第三,市場調整的手段應該有所區分。在市場自由方面,通常采用法律手段來進行調整。法律在調整市場行為的時候,采用強制性規范。強制性規范所規定的東西不能違背,如果違背就是無效的。
所以法律中有一些明確的規定:違反了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行為無效。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調整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尤其是市場活動,那么結果就是國家規定的法律越詳細,就等于國家在代替當事人牽動這個活動。
但是法律調整就涉及到給當事人的自治能度有多大。西方國家在法律領域的一個準則是,在合同領域或者在市場交易領域,采用當事人意識自治。所謂當事人意識自治,就是任意性規范。所謂任意性規范,就是如果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和法律所規定的準則不一樣時,以當事人的意志為準。而我們在市場經濟活動里面看到的,當事人的意志和法律的意志不一樣的時候,法律的意志高于當事人的意志,就是強制性的。
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這兩種規范良好地結合起來,才可以既體現國家的強制作用,也體現了市場規律自主作用,才能夠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才能夠
真正的發揮市場的作用。
(本文節選自作者在“第十屆中國年度管理大會”上的主題演講,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