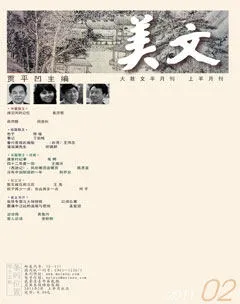鹽鐵專營與土地財稅
以閱眾甫
陜西人,2008年法學專業畢業,從事于法律相關工作。
中國歷史中有多少得失真是說不清,前人有得有失的,到今天又有多少能保證不失有得的,就比如中國很早就廢除了井田制卻在此后兩千年的時間里常常為了民有其田又改來改去,還伴著江山一代代易主。雖然不能說這得失全在這土地以及相關的財稅上,但是有關農業經濟及其財稅的變化也展現了以農業為主的傳統中國的變化軌跡。傳統中國社會中農業在財政稅收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很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其他商業、手工業的存在,因此,夾雜在這期間的許多史實——特別是關于財稅改革、商業政策的內容——如果聯系起來或許值得認真思考。
回溯歷史,自漢武帝時代之前,商業在一個國家中的比重不是那么重要的,雖然我們都知道春秋時期范蠡已經是一位有名的“跨國商業巨頭”,但是就各國的商業而言更多的是以民間販運、買賣為主,而國營的商業在春秋最有影響力則是管仲對于鹽鐵利益的控制,這是有史可見的最明確的關于國家專營的記錄,但是還是以民間貿易為主。不過它卻是國家介入商業貿易并控制商業規模的一個嘗試,這也與先秦時期的公室財政困難有很大關系。因為在周的分封體制下,不同等級之間的利益輸送還是主要依靠貢賦而不是稅收,而貢賦的受益人也就是公室。在諸侯國里王室私產管理和侯國公共財產管理還沒有完全分離,而且這也取決于侯國的政府還是依靠公室的管理團隊充任,而公卿的出身其實也是公室的家臣。所以稅收的出現無非有兩個原因:一是諸侯國從一個封地開始向國家轉變,開始承擔諸如國防、基礎建設方面的公共支出,公室財政已經無法承受,而公卿越來越強勢,井田制的式微造成貢賦收入越來越少。二是在農業之外新的產業諸如煉鐵、制鹽、釀酒在一些諸侯國逐漸出現,在侯國內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它們作為諸侯土地上的產出,因此也促使公室考慮如何將其納入公室的收入中來補充財政。
然而這種政府結構到了秦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就點出了這些差異,政府已經初步地從王室分離出來,雖然宰相還承擔政府首腦和名義上的宮室管家的雙重身份,但是御史中丞的存在實際承擔了政府和王室的溝通關系,至少原先的公室管理團隊已經開始承擔了國家的管理角色,并在財政方面出現分離。錢穆先生就特別講到了少府和大司農這兩個官職的區別,大司農大家都能明白負責國家的農業管理,因為當時農業是國家官方經濟收入來源,因此也主要用于國家的公共財政收支,而商業在秦的時候還并不能體現出其重要性,所以就成為了少府收入的一部分,而少府恰恰是公室管理體制殘余的一部分仍在為皇室服務,并為其承擔財政管理。漢朝的時候這一政府結構還繼續繼承,但是變化在于商業已經相當繁榮了,特別是鹽鐵等行業的巨大暴利為少府提供了巨大的稅收來源,漢武帝時少府在國家收入中的比重愈加增強,但是它卻屬于皇室私產。同時商人的強勢也令他們蠢蠢欲動,逐漸涉及政府的管理,比如著名的桑弘羊,他本來就是商業出身。不過漢武帝因為對外戰事的需要開始將其私人腰包也就是少府財政開始用于支持國家支出,迫于農業收入的有限性以及一些重要商業行業的收入相當可觀,國家開始著手將鹽鐵釀酒等重要行業納入官營,并禁止商人在從事這些行業,以減少商人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干預國家管理。而這個政策的一個直接目的就是政府通過國營專利來支持政府運轉。所以,經過這次重要的經濟結構的改革的影響就是以后歷朝歷代政府都意識到其重要性,因此基本延續了這一模式。然而抑制商人群體的發展和影響力,絕不代表著整個中國就沒有了商業,因為最大的商人就是政府自身。
從漢朝當時商業發展規模上看來,尚看不出商業和農業之間的完整關系,但是今天我們再重讀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隨著財稅制的改革,這種商業模式給農民和國家本身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制約。這是為什么呢?原因在于對于一些國民經濟重要行業的官營,造成民間商業資本的活動空間極度萎縮,于是這些資本可以從事的內容就只能集中于糧食、布匹、木材等關乎日常消費的一些行業,而諸如糧食、布帛這些能夠充當稅收的物品則成為商人關注的重要內容。起初國家的稅收主要是實物稅收,比如到唐朝還持續了相當長時間的租庸調制。可是租庸調制最大的短板就是古代政府在數目字管理方面存在技術困難,也許在均田之初還可以保證戶籍和土地檔案與實際情況一致,但越往后隨著人口的不斷變動加上政府賬目管理不善以及地方官府對于均田制的推行力度不夠,致使均田制難以維持下去,因此也就直接影響了國家的稅收。所以到了唐德宗時期,當時的大臣楊炎就建議改革稅制,就是國家不再以戶征稅,而是依據土地征稅,核心內容為:“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予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實就是稅收按土地所在征收,而雜役等折成費,國家不再像以前那樣量入為出的征,而是變成量出為入的征。這樣人口就不再被限制在土地上,卻又不影響國家征雜役。當然,這種稅制的推行歸功于門閥家族勢力逐漸弱化。這個改革對后來中國最大的影響其實是貨幣稅收的出現,而且不同土地征收相同租稅的做法也被取消,開始因地征稅。
一旦開始以貨幣征稅就必須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凡雜役折費就必須要把糧食等交換成絹帛或其他貨幣來繳納,而不需再征用勞力,政府則改go3ghCgAmszmpXmqmxnhPA==用征收的費用臨時雇傭。這時候中國商業結構的弊端就開始體現出來了,狹小的商業流通機制就使得農民只能賣糧換取貨幣。由于國家專營致使商業經營范圍有限,兩稅制對商人來說則是難得的機會,他們通過低價收購囤積糧食到糧荒時高價拋出賺取暴利,那么反映到農民手中的貨幣產出卻越來越少,最后不得不賣地、拋荒變成流民。由于傳統中國又不能給商人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和經營環境,使得商人不得不用利潤購置田產等不動產,加劇土地兼并,而這也是政府重農抑商政策所要引導的結果。國家就這樣一方面專營一些重要行業充實財政,一方面又把商人逼向土地收取租稅。而這個過程中農民則在一次次改革中更加悲慘。等到明代萬歷年間,以前的稅制已經無法在大一統的國家內順暢的推行,一是兩稅制雖然以土地征稅,但是政府龐大的開支又難免增加了新的稅種落在民眾頭上,以解決財政困境;同時也為解決全國范圍內調運糧食布帛的困難,張居正開始推行一條鞭法,中國開始完全將稅收貨幣化,全部折銀一次征收,從而方便了地方財政收支和中央財政的整合、調度利用。那么這也間接地推動了佃農和地主之間的地租形式開始向貨幣地租完全轉變。和兩稅制所談到的農民土地產出賤賣的情況一樣,現在只會更加嚴重。從實物地租走向貨幣地租的發展過程中,農民作為國家的最主要人口其土地產出是越來越多,但是其貨幣產出卻是越來越小。
排除金銀開采有限所造成的通貨緊縮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商業范圍的狹窄致使商人操縱農產品市價獲取暴利,然而這些資本并未大規模的變成早期中國的資本積累,而是造成了每個朝代都不得不面對的社會性問題——土地兼并。國營專利限制商人的政策實際上成為傳統政府不得不解決的社會問題的背后推力,而且當其逐具規模時就開始危及政府征稅和社會穩定。可以想見,流失土地的人越多,政府的稅率所面對的將更多是大地產者,而他們又將提高的稅率轉移給農民,農民終因難以承受租稅而流離失所成為流民。可以想見,這一商業政策沒有為政府的財稅改革和貨幣改革提供緩沖的余地,反倒將其負面因素予以放大。那么如果放在現在社會,面對廣大的農民,如果國家既要承認市場經濟,又不放開市場,那么國家就必須長期地維持國家糧食定價等保護性政策,否則任商業資本操縱必然會造成農業社會的失序。這就是農業政府堅持國營專利的一個困境。
當然,土地與稅收只是一部分現象,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反觀其他各個經濟領域所面對的影響。國有專營所造成的有限的商業市場,造成商人資本的狹小活動空間,必然會推高許多不動產和普通消費領域的操縱和投機活動,這將會與貨幣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成正比,而政府就需要花費更大的財政能力來保障國計民生,以化解經濟不安定因素。因此,傳統中國若論得失,其失有其一就是:刻意將商業資本的收放問題棄之一邊,而選擇了國有專營所帶來的收入維持政府運轉。當然,政府自然也是意識到不能夠解決政府自身的管理結構和權力控制問題,就不得不需要增加財政來源維持龐大的管理機器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