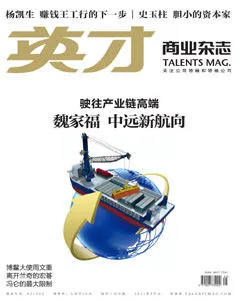銀行的“華麗困境”
稅后利潤8991億元,同比增長34.5%。2010年,國內商業銀行業又交上了一份不錯的答案。據銀監會最近的公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95.3萬億元,比2009年增加15.8萬億元,增長19.9%。
作為高端產業,金融業的發展尤為關鍵。而國內金融業最核心,也是資產規模最為龐大的銀行業體系,直接干系著眾多實業產業的發展態勢。觀察近幾年銀行業自身的發展,在剝離不良資產,順利完成股改并陸續上市之后,銀行業脫胎換骨般的迅猛增長,其基于巨大“盤子”之上的高速增長率,讓傳統制造業等望塵莫及。
于是,有評論人士甚至發出了銀行業與實業產業之間爭利的質疑。一邊是諸多產業的融資瓶頸問題依然突出;一邊是銀行業“嫌貧愛富”式的信貸投放和逐年利潤的高增長。現在看來,4萬億投資下的銀行大規模信貸投放,獲益最明顯的恐怕是銀行業自身。即便上調存準利率和加息等收縮流動性的措施陸續放出,但息差還在繼續拉大也使銀行短期之內仍然處于讓國際同行羨慕嫉妒恨的高速增長中。
在資本市場上,當四大行比拼業績,股份制商業銀行暗中較勁增長,城商行不甘落寞而排隊上市時,投資者只是對銀行賺錢能力嘩然一片,卻并不“買單”,銀行業上市公司10倍左右的市盈率仍然還是整個市場價值洼地的最深處。
不可否認的是,信貸規模的持續放大,資本市場上相應的巨額再融資,如此循環,讓外界對于“當銀行行長如此容易”的調侃聲,聲聲刺耳。但現實依然是,息差收入占據著國內銀行業高增長的絕對因素,中間業務以規模占比來看,不過還是小小配角。守著如此容易的“賺錢方法”,銀行業究竟有多大的動力去實現“十二五”的轉型調整?如果繼續這樣的發展模式,銀行業的高增長是否會帶來整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利率市場化又是否是促使銀行保持變革精神的靈丹妙藥?
高增率不可持續
《英才》:2010年國內銀行業仍有高達34.5%的利潤增長率,如何看待這一增長?
趙慶明:利潤增長率有一個基數的問題,像農業銀行2010年利潤同比增長了49%,它的資產規模和建行、中行都差不多,但就是因為基數小。在2009年時,國內貸款增長很快,但銀行的利潤非常薄,有的銀行可能還存在財務上的虧損,所以之前的基數可能比較低。要比較,我們應該還要看資本的利潤率和資產的利潤率,這樣可比性就比較強了。
孫立堅:目前銀行的高利潤率其實是宏觀調控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顯現,過去政府財政刺激下,銀行獲得息差的收益。前期的房貸規模很大,房貸的收益增加體現在利潤收益上,再加上現在加息,銀行的存量資產是受益的。
《英才》:與國外同業和國內其他行業比,這樣的增長率是否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
趙慶明:這個數字不太能和國外銀行業比。與國外比,就資產收益率和資本收益率來說,我們和他們相差不大。就利潤增幅來說,國際上因為宏觀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可能會偏低一些,這很正常。
孫立堅:國外銀行現在還處于一個去杠桿化的過程,瘦身、裁員和節省成本;而我們不一樣,我們是通過項目拉動,通過擴大貸款規模來增加利潤。如果國外經濟恢復,那也會和我們一樣靠投資新的項目來獲取利潤的增長。一個是新增投資帶來的增長,一個是節約成本帶來的增長,這是不一樣的。
郭田勇:中國經濟增長快,需求旺盛,銀行通過改革也提高了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在增強。這種增長率總體還在一個合理的空間。
《英才》:按照目前的經濟態勢和銀行盈利模式,這樣的增長率是否能持續?
趙慶明:我覺得銀行業正在走入發展的正軌狀態,就不會增長30%多了。另外,今年的信貸增長比去年和前年都要低一些,這也會影響利潤增長。還有就是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隨著經濟增長率下降,企業的還款能力就會有所下降,銀行的不良貸款也會處理多一些。這就會沖減利潤。
孫立堅:未來增量貸款的減少會影響到新增業務,但現在還是存量,吃老本。至于轉折點,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退出,銀行現在只是暫時受到國家的政策限制,所以短期內會有影響,拐點在下半年增速會有下降,但很快就會在“十二五”規劃展開后,投資還是要提升,增速馬上又會起來。現在銀行都在說沒錢,隨著“十二五”規劃項目的啟動,銀行的資金還會充裕的,再加上緊縮貨幣政策,很多的f7b073e1763fbd3666b8d322318a66bd錢會回流銀行。
利率市場化條件不足
《英才》: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銀行業的高利潤增長相當一部分來自對實業的爭利,怎么看待這一觀點?
趙慶明:現在我們的利率還是一個行政決定,有一些市場化的因素在里面,但調控也不是單純偏向于銀行的。雖然銀行業準入的門檻很高,但現有銀行之間也是高度競爭的。
孫立堅:中國現在不僅是銀行在加息,民間資本的利率也在增加。今天流動性泛濫和物價上漲,靠貨幣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越加息,實業就越難做,市場的錢就越來越多,甚至都不在銀行。這樣再加息,錢還是一點都沒有少,從實業逼出來的錢又跑到了灰色體系當中。現在關鍵是對這種成本推高的通貨膨脹,我們應該從降低成本的角度去考慮,通過減稅和扶持民營資本,抵抗成本上漲的壓力,這才是關鍵。
郭田勇:這是一個分割,雖然銀行少掙些錢,實業就可以多掙些錢,但一方面這和國家調控政策有關,利率如何設定是政策的制定。另外從金融業的作用來看,銀行業更穩健一些,對維護經濟的穩定是有幫助的。如果銀行不賺錢,就像美國一樣,對社會也有負面影響。
《英才》:從銀行的收入結構來看,國內的銀行主要依靠息差收入,而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趨勢下,未來銀行的利潤增長是否會走向下行通道?
趙慶明:我們的銀行在收入結構上側重于利差收入,中間業務收入低得多,只在10%—20%,而國外利差以外的收入占到50%以上。其實,哪一種經營模式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關鍵還是看宏觀經濟狀況,銀行風險管理能力和內部控制能力。我們和全球多數實現了利率市場化的國家相比,利差是處于中下游的,所以并不是實行了利率市場化后,利差就會收窄。
孫立堅:現在的問題是,銀行實行利率市場化的條件還不具備。通脹風險已經存在了,再加上其他風險,老百姓感覺到財富縮水的壓力很大。畢竟現在的老百姓不是以消費為主,而是以財富增長的訴求為主,所以對付通脹是以財富增長來對付通脹。但國內銀行的難處就是,老百姓對理財收益要求非常高,這樣中間業務很難開展。目前一般老百姓不愿把錢交給銀行去打理,除非存款的人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提高了,那么銀行開展中間業務的空間就會大大拓寬。
郭田勇:即便沒有利率市場化改革,只靠利息收入,銀行的資本金也會出現瓶頸,未來利息收入占比下降都將是種趨勢。未來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銀行利差收窄就會對銀行盈利產生負面影響。
《英才》:在前兩年,寬松政策的推出使銀行產生了大量長期貸款,如果靠息差的增長模式不改變,這種貸款是否會成為未來的隱患,從而引發系統性風險?
孫立堅:只要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不退出,銀行利潤的波動性不會很大。關鍵是怎樣讓民營和產業的資本到舞臺中央來,讓銀行的增長不是靠政府來拉動,而是靠企業自身來增長,這才是關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