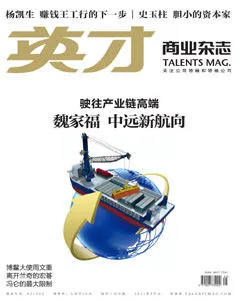當慈善太沉重
他的企業不大,世人甚至不知道其做何生意、靠什么賺錢;
他不善言辭,卻每每被青年奉為榜樣;
他甚至捐200塊錢還非要拉被捐者一起照相,并讓這些照片見諸于報端……
近幾年,他已成為中國企業界最具話題式的人物——因慈善而躥紅,也因慈善而飽受非議。圍繞他而展開的話題持久不息,贊揚與責罵、鼓勵與批評,始終伴其左右。
他就是陳光標,以拷問中國企業家良心和責任標桿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
雖說中國自古就有“扶貧濟困”、“樂善好施”的慈善美德,但現代慈善理念和制度還處在啟蒙、孕育階段,將慈善常規化、可持續性發展,依然任重而道遠,許多人只有在大災大難的危機時刻,才施手援助,甚至不少企業將慈善與公關、品牌建設、企業家名譽捆綁為一體。
“暴力慈善”
在手舉百元大鈔、笑逐顏開的災民擁簇下,陳光標意氣風發的與眾人合影。
這是陳光標3月16日在云南盈江地震災區行善時的一個片段。隨著這張照片在網上風傳,指責與痛斥洶涌而至:做秀、影帝、暴力慈善……將這位“中國首善”再次卷進輿論漩渦。
這已經不是陳光標第一次因照片而遭受批評。
僅在一年多之前,陳光標在中國工商銀行江蘇分行會議廳用一捆捆“錢磚”擺列成墻,并在墻前留影,遭到網友質疑;1月26日,陳光標率領50余位大陸企業家赴臺灣做慈善,計劃捐出5億元新臺幣,并堅持以現金方式當面發放,卻遭到部分縣市拒絕;不久前,陳光標在日本地震災區救出一名婦女的照片遭到網友炮轟,不少人嚴詞質問:“你到底是去救援還是去攝影?”
不僅僅是網友,慈善界的某些人士也對陳光標的高調慈善行為頗多詬病。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指出:“以喪失受贈人的尊嚴來獲得自己的某種滿足,是一種慈善的暴力行為。”中山大學教授朱建鋼也認為:“這樣的慈善行為是對窮人不可抗拒的暴力,讓窮人不得不接受這樣一種傷害。”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韓俊魁更表示:“這種行為凸顯的是捐贈者那種居高臨下的優勢——不管從經濟上還是道德上,所以我不太喜歡全民公益的說法,慈善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
而就在對“暴力慈善”的指責最為火熱之時,有一種聲音卻是針鋒相對:“只要他行善,不管是高調還是低調、暴力還是溫和,都應該叫好,而不應該苛責。”
“我的高調不是為了個人,也不是為了宣傳個人。”陳光標本人也如此辯白。
其實,從陳光標多年來的善舉不難看出,無論是汶川地震還是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日本地震,凡是有災之處,他總會最先出現,雖然他的善款不一定最多,但肯定是第一個做出反應的大陸企業家。行善不甘人后或許就是陳光標的個人風格。
而黃如論的行善風格,則與陳光標形成了鮮明對比。
盡管從2005年以來,黃如論已連續5年獲得“中華慈善獎”,同時還不斷現身各類慈善排行榜的前列,但他在捐助時卻絕少讓媒體報道。有一次,某慈善組織打算在以黃如論名字命名的“如論講堂”給黃如論頒獎。他得知后堅決不去參加。他崇尚的只是“做善事可得善報”的慈善觀念,并以低調的行善風格堅持自我。
在西方,每年匿名捐贈的善款可高達10億美元。在近期的日本大地震、海嘯及“福島核泄漏”事件中,臺灣也有企業家匿名為“福島50壯士”的家屬捐款5000萬臺幣。
其實,高調或低調,這兩種慈善家的不同態度,都是中國慈善環境目前所需要的,本無對錯之分。但是,損害受捐者尊嚴,不顧弱者的形象,以粗俗的方式,充滿炫耀色彩四處張揚的慈善,濟困救難的本意會大打折扣。
不過,高調行善又不等同于“暴力慈善”。在中國慈善事業剛剛起步的此刻,“暴力慈善”應該引起格外重視,它很容易將慈善理念帶往另一個極端,甚至將社會價值觀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美國慈善之父卡內基曾告誡社會:“富人布施式的慈善與其說是偽善,不如說是作惡。”
寬容慈善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中國歷代讀書人信奉的做人準則,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觀緊密切合。可是,不少人在飛黃騰達報效天下時,卻困難重重,甚至遭受罵名。
“5.12”大地震當天,萬科宣布捐款220萬元,這在全國企業界動輒千萬、上億元的捐款中并不算多,網友對于萬科捐款數額過低提出質疑。三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回應:“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
一言激起千層浪,王石隨即被詬病為“王十塊”。6月5日,萬科臨時股東大會高票通過1億元援建四川災區的議案,持續20多天的“捐款門”危機才算暫告一段落。
2009年10月20日,陳發樹在北京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并將個人持有的價值83億元的青島啤酒和紫金礦業的股權捐贈給基金會,占個人財富的45%。但是,陳發樹的慷慨壯舉卻并未贏來掌聲,媒體紛紛質疑此舉有避稅和通過基金會進行關聯交易的嫌疑。
有記者甚至責問:“基金會注冊資金只有1億元,加上后來補充的6000萬元,依然離83億元相去甚遠,是否存在詐捐行為?”事實上,有價證券并不等于現金,它只是一種承諾,目前國內沒有條文規定,是否兌現完全依靠企業家自律。
2007年6月5日,農夫山泉曾開展“一分錢”公益活動,稱“每賣出一瓶農夫山泉就為水源地的貧困孩子捐出一分錢”,輿論一片嘩然,認為此舉存在借公益進行商業炒作之嫌。2008年汶川地震后,王老吉也曾以“捐款1億元”為熱點大肆宣傳,使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涼茶品牌一夜爆紅,網友卻一臉鄙夷,認為企業拿慈善做廣告不道德。
廣告炒作也罷,政府公關也好,實際上慈善捐款與商業目的本身并不矛盾,凡是心懷感恩、樂善好施的企業家,都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可是目前,社會各界顯然對慈善不夠包容,過于苛責。畢竟慈善家們都在身體力行,拿出真金白銀來幫扶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盡管他們可能存在高調炒作、商業投機的目的,但若沒有違反法律,只是行善方式上的瑕疵,公眾應該原諒。更何況我國目前的慈善事業尚處于起步階段,任何微小的善舉都如雨后甘霖、雪中送炭,應該受到尊重和鼓勵,而不是圍觀之后的指責和謾罵。
因此,全國工商聯鼓勵企業家把慈善當成一種投資行為、商業行為。換言之,只有將成熟的商業模式應用到慈善中,才能夠促進慈善體制良性循環,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外差別
客觀來說,無論是對陳光標“暴力慈善”的批評,還是對陳發樹的“詐捐”指責,其恰恰是我國慈善事業目前所處艱難境況的真實寫照。有沒有一種方式能讓企業家們不因高調而將私心放大?慈善機構不就是為此服務的第三方嗎?
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處于嘗試、摸索的初級階段,公益基金的管理體制僵化、不透明導致企業家對捐款的去向存疑屬于普遍現象,善款被挪用、暗箱操作等現象時有發生,企業家將捐款直接發放到受助人手中,既能減少中間環節,而且公正透明,落到實處。
例如,曹德旺曾在捐款時提出如下條件:半年內將2億元善款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3%,而業內標準是10%。即便如此苛刻,輿論還是一片掌聲,原因就在于公眾對捐款渠道缺乏信任。陳光標的“暴力慈善”,事實上是對公益基金運營方式的變相質問與挑戰,有益于加快慈善體制改革進程。
與陳光標等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企業及企業家們在這次地震和海嘯災難中的表現。雖然有不少的日本企業家為災害踴躍捐款,但在日本的各種媒體上卻很少看到類似的捐贈新聞。
這涉及到的是觀念、是救助體系完善與否的問題。日本的媒體和公眾普遍有這樣一個共識:捐贈是一種功德,但沒必要過分宣揚,否則目的就不純粹了;而對于日本企業家而言,本國救助體系的完善和透明,讓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把錢捐贈給相關慈善機構,而不用自己拋頭露面地親歷親為。
《公益時報》自2004年開始發布中國慈善排行榜,7年間中國民間慈善捐贈增速超過100%,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關注、參與慈善活動的人激增,企業家們的慈善熱情空前高漲,他們希望將商業領域的成功理念注入到公益領域,讓更多人得到幫助,官方對民間的慈善支持力度也持續增加。
但中國的慈善事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統計表明,中國擁有80%財富的富人階層只貢獻15%的慈善捐款。一般發達國家慈善捐款占GDP的3%-5%,美國高達9%,而中國還不到0.5%,2009年我國人均慈善捐款額與美國相差7300倍。差距擺在面前,西方的慈善模式值得借鑒。
2010年9月底,巴菲PuYhSnL6uaDhHlQeB5W6kPK4GYWQ2+kdn8Nv47qoD2c=特與蓋茨在北京邀請50位中國富豪參加的“慈善晚宴”一度引發空前關注,巴菲特發現一些中國富豪擔心隱私被泄露或家人安全受到威脅,盡管美國也有此類情況,但中國富豪主要是擔心被誤解,害怕影響聲譽。他認為美國的慈善模式不適合中國,美國文化和中國不一樣,慈善方式也不同。而胡潤百富榜創始人胡潤認為,中國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人們對慈善機構不信任,擔心機構會克扣一部分的錢,畢竟大多數機構正常運作始于1994年,起步較晚,在人才、系統和品牌信任度上還有欠缺。他給出的國外經驗是:除了構建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環境之外,企業捐贈時可以給慈善機構捐一筆錢,以保證它正常運作。另外,讓民間慈善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他們往往用1元錢便能夠完成政府需要花費3元錢才能完成的事情。
此外,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國內也涌現出一些新的慈善模式。比如總部設在浙江金華的慈善網站“施樂會”:賣家“出售”自己的困難,買家通過捐贈行善“購買困難”幫助賣家,這看起來有些類似于C2C的電子商務模式。
“施樂會”操作透明,所有善款的銀行匯款截圖公開,也不收取管理費用,善款可全額資助受捐者。這種方式在參與性、專業性、可信任方面都不失為新的嘗試。不過網絡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而受捐者、捐助者的信息則高度透明,難保不被別有用心的人欺騙,一旦失信于人,“施樂會”將遭受重創。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人的財富觀念和慈善理念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這其中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推動因素,也有陳光標等慈善標桿人物奔走呼號、身體力行的榜樣作用。
客觀來看,財富階層更應該承擔慈善責任,慈善行為一旦避開富豪群體將會十分危險,而且不可持續。在中國慈善的朝霞初升之際,對“暴力慈善”暴風驟雨般的爭論,及時而珍貴,它讓人們看到更多的慈善選擇,不管是道德層面,還是模式、制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