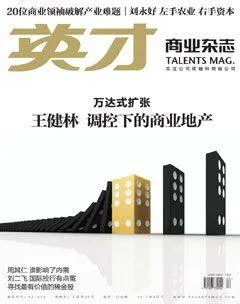劉二飛:國際投行有點“冤”
2011-01-01 00:00:00王瀛
英才 2011年4期

3月,人民幣持續走強,再創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新高。自去年底爭論的“熱錢流入”話題,再度升級。近日,外管局發布《2010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首次對外解讀熱錢動向。根據這份報告,2010年熱錢凈流入有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
但官方的數據似乎只是揭開冰山一角,因為報告中只是外管局從外匯儲備增量中扣除進出口順差、直接投資凈流入、境外投資收益、境內企業境外上市籌資調回等外匯賬款未入賬部分來測算,卻忽略了其他的構成途徑,其中占比重較大的就是由香港過境的熱錢。
香港一直被視為熱錢“過關”的橋頭堡,隨著近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以及央行再加息,大批的國際熱錢早已經蟄伏于此。原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曾公開表示,僅去年香港熱錢就超過千億美元,而近期又有“十萬億熱錢屯兵香港”的新聞一度喧囂塵上。人們對于熱錢涌入的擔心,從根源上講,無論是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還是2008年的越南金融危機,熱錢帶給新興市場國家的教訓慘痛而深刻。
同樣是在西方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元貶值、國際市場資金涌入的情況下,千億規模的綠鈔熱錢對于人民幣,對于中國經濟的沖擊力有多強?華爾街的金融大鱷是否就是這一戰局幕后的推手?《英才》記者專訪美銀美林集團中國區主席劉二飛,解讀迷局。
熱錢襲港是“大鱷”布局?
從香港政府公布的1月通脹數據來看,香港1月通脹率,環比上升0.5個百分點,升至3.6%,這是自1997年以來香港最高的通脹水平。同時,港府預計的全年通脹率將達到4.5%。事實上,香港股市和樓市也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持續走高。
熱錢從國際金融市場流向套利的金融或資產市場,短期的逐利性決定了其不會進入實體經濟,會轉而在證券市場與資本市場中潛伏。雖然中國大陸對熱錢的進入有嚴格的限制與監管措施,但香港作為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無法進行資本管制與流入中國內地的渠道,這勢必使其成為熱錢狙擊的前沿陣地。
“香港通脹肯定是存在的,但熱錢真正的意圖是想進入中國內地,并不是對香港股市有預期,也并不是要炒港幣。”劉二飛向《英才》記者表示,囤港的熱錢數量,其對應的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一旦熱錢流入中國內地,其龐大的規模會不會形成影響甚至于威脅中國經濟的力量?在劉二飛看來,這種可能性存在的前提本身就很微弱,“熱錢借香港進入中國雖然也有一些非法渠道與監管漏洞可循,但是流入的總量非常小,并且中國對境外熱錢本身也有嚴格的管控措施。因此,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更不會影響到國內的貨幣政策。”
劉二飛認為,香港經濟受中國內地影響,是大陸相關經濟,但是港幣卻和美元掛鉤,當大陸高通貨膨脹率時,貨幣政策從緊加息,港幣卻隨美元利率下降并且貶值,最后的結果就是香港從中國內地進口的東西都很貴,本身也面臨著很高的通貨膨脹的威脅。“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港幣應該逐步實現與人民幣掛鉤,這樣就可以抑制香港這種通脹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大鱷開始加速在香港的擴張似乎引起了很多分析人士的憂慮。
早在去年底媒體報6500億美元熱錢進駐香港時,這其中就有攜90億美元身家卷土重來的資本大鱷索羅斯,其在香港設立的對沖基金公司正式開業。
而今年2月底,美國高盛集團自營交易的全球主管施家文在香港設立一家對沖基金,在香港建立分支機構,目前已取得牌照,基金將于今年二季度開業。規模可能達10億—15億美元(約78億—117億港元),將是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規模的新成立對沖基金,也是亞太區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
除此之外,一些大型對沖基金公司,如維京全球投資者、Maverick Capital等紛紛擴充亞洲業務,香港則無疑是他們的首選之地。
對沖基金往往因能帶動百億甚至千億規模的國際游資進行投機交易而看成是熱錢的主要力量,數據顯示,僅2010年前9個月香港證監會接到對沖基金申請牌照數目已與2009年總和相當,達307家。
那么,外資金融機構是否為熱錢真正的幕后推手?
“人民幣升值有預期,用外匯投進來,人民幣升值后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是好事,但這個問題不能孤立來看。投資分兩個概念,一個是產業投資,一個是市場投資。如果是產業投資,即使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型外向經濟的企業會受到影響,但考慮到其產業增值的因素依然會投。”
在劉二飛看來,這是由于外資金融機構的投資性質與策略所決定,并不會由于短期的資產增值為套利而偏離,相反會挑選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對其利潤有所影響的企業在低位時進入,這不失為一種更有效的投資方式。
華爾街陰謀論不成立?
從金融危機到能源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漲跌,國際游資在其中都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也因此,近年外資金融機構利用大規模游資借唱多做空等手段在新興市場國家獲利、金融陰謀的言論也開始為人所爭論。
對于在高盛、摩根士丹利、所羅門兄弟等華爾街知名投行工作過的劉二飛在接受《英才》記者專訪時表示:“利用金融手段操縱市場與經濟下行抄底市場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是違法行為,而后者是市場運行的自然規律。”
這種規律,被劉二飛比喻成資本界的一種弱肉強食:每個個體的D N A決定其在這條生物鏈上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人負責“吃”,而有的人就是負責“炒”,比如對沖基金,但這并不代表不符合監管與市場正常的運作規律。
“投資商業銀行的核心目的就是賺錢,投資銀行或者是商業實體,他們的目標就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股東利益最大化,就是賺錢最多,抄底并不代表投機。”對于大部分人都將金融危機歸咎于華爾街投行,劉二飛顯然認為國際投行有點“冤”。
“以一個不懂金融的人來看,金融危機是華爾街創造了一些大規模的金融殺傷武器,不小心引爆了,把整個經濟帶入危急,很多勤勤懇懇的人失業了,華爾街只經歷了一年低谷,那些人又開始賺錢了,獎金比以前還多。他們很不明白。”
從另一方面看,美國老百姓買房子可以零首付還貸款,房價上漲還不起房貸時可以把房子賣掉獲利,等房產不增值賣不出去又還不起貸款,就相當于債券從根上爛掉了。后來有國會,讓買不起房子的人貸款給他買房子,泡沫越來越高,終于破了。最終輿論將始作俑者變成了華爾街,卻不想在這一條“生態”鏈上,老百姓、政府與華爾街是扮演者同等分量的角色。
“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認為是監管不到位,開始金融整頓。現在很多華爾街投行去上海、香港,在亞洲很多新興市場國家落腳,但是美國卻因此而很緊張意識到了嚴重性,因為這代表著國際金融中心的轉移,會危及他的地位。”劉二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