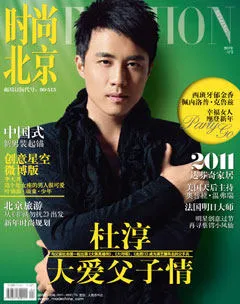熊文韻 人性感悟“空空”
2011-01-01 00:00:00郭媛媛
時尚北京 2011年1期

從工筆人物畫到現代日本畫,從帶動川藏線上的“流動彩虹”到制作有著三個觸角的小玩偶,這些跳躍性的轉變都讓我對于采訪熊文韻老師充滿期待。借由宋莊藝術節的契機,我有幸來到熊文韻老師家中與她近距離接觸,了解她與宋莊的故事……
沿著宋莊寧靜的道路,我們驅車前行。路過的一幢幢房屋里仿佛都蘊藏著永不完結的之于藝術的渴望。車子終停在了一片湖面旁,晚秋的陽光落在湖上,波光粼粼,熊文韻老師的家便在不遠處。院落雖然不大,卻十分寫意。
因并未見過熊文韻老師,依著她的藝術經歷,感覺她應該是充滿無限能量的。不過眼前這位身材嬌小的藝術家,著實讓我有點驚訝。但聽到她洪亮的、擲地有聲的談話,這絲詫異便蕩然無存了。
熊文韻老師首先就解答了我對于她的那些跳躍性轉變的疑惑。她告訴我她當年畢業于四川美術學院,學的是工筆人物,后到北京中央美院和中國文化研究院進修了兩年。之后從北京去到日本。在日本學習了幾年的日本畫,日本畫比中國畫更講究制作上的技巧。再后來她在日本筑波大學學了三年設計。1996年她回到中國,并在中國美術館辦了第一次個展。之后,她的作品就傾向于抽象化。1998年她又在中國美術館做了一次展覽。這之后,她開始接觸當代藝術。而這之前,她在日本學習的還是比較傳統的,日本的學院派。“從1995年開始,我越來越覺得當時我所掌握的語言已不能充分表達我對于自然與社會的認識。我在95年到96年間用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試驗,也就是想找到能充分表達我內心感受的那種形式。這里還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在去日本之前,基本上還屬于那種對于錢沒有什么概念的人。去日本之后,一下子面對那種高度發達的商品社會,很不適應,可以說在日本學畫的那幾年,我基本上是處在一種自我封閉的狀態中,在這中間我差不多每一年都去西藏寫生,因為我16歲的時候就已經在阿壩地區插過隊,每次去西藏的時候就感覺又找回到了一點自我。”
從1998年開始,熊文韻老師懷著對西藏的那份獨特的情懷,在川藏線和青藏線做了三年“流動彩虹”計劃。談到最初的緣由,她說:“我在做前一批抽象作品之后,體會到一種極度空虛與失落感,覺得自己在找到一種形式并把它表達出來之后,就又什么都沒有了。這時我又去了一趟西藏,那次去身邊還帶了一套把那批抽象的東西縮小了的作品,但我在貢嘎機場下飛機的時候,馬上就感覺到這批東西和西藏的環境十分不符合,不相襯。于是我去文具店買了一些顏料,開始在自然中尋找可以表現的色彩,同時自己也有感覺的自然物體。”這就演變成后來將單色布塊掛于汽車上,汽車在川藏線、青藏線上行駛形成流動的色彩,宛若彩虹。也觸動了當地人和進藏人員對于美的追求,對人類破壞自然的關注。“這個計劃開始是很個人的。后來才跟環境、人、砍伐樹木、交通污染聯系上。當時就想通過駕駛員和他們所運載的人的覺悟促進這個地區,這種動態的東西,會讓他們突然有對自然美的向往,或是心理有一種不愿讓她改變的想法。”
而談到從“流動彩虹”到“空空”的轉變,透露出熊文韻老師對于現實的一種無奈。“因為當年我在國外生活,很理想主義。回來覺得很多人支持‘流動彩虹’計劃,當時就決定找一千輛車來做。但最后找贊助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煩,我們需要資金能讓活動得以實施。那段時間,我往返于日本和中國,在日本逛街購物成了我釋放壓力的一種方式。一次偶然中,我買了幾個時髦的小戒指,愛不釋手,戴著給朋友們看,結果被一搶而光。沒辦法,我就試著去買些珠子魚線自己穿戒指。很快,我發現自己在這方面很有創造力,編戒指的過程讓人廢寢忘食,一發不可收拾。當我全神貫注地編戒指時,現實中所要面對的困難統統都被這穿珠引線的簡單動作消解掉。在我編的戒指中,一個有四個小觸角的戒指觸動了我,觸角感覺很有生命感,有點像肢體、有點像昆蟲、又有點像草,說不清楚。直覺讓我決定跟蹤這個小精靈,并幫助它完成下一步驟。之后我對這個戒指的造型稍作改動,于是就出現了一個有著三個觸角造型的小玩偶,它成為‘流動彩虹’吉祥物,陪伴我繼續‘流動彩虹’的路程。”這有著三個觸角的小玩偶便是“空空”的最初狀態。
提到“空空”,就不能不談到宋莊。在第六屆中國宋莊文化藝術節開幕式現場,可愛的五個“空空”形象煞是吸引觀眾眼球。熊文韻老師在宋莊的生活讓“空空”進入了另一個發展階段。2003年,熊文韻老師在798創辦了空空工作室,開始在那里進行“空空”的設計制作。2006年,她開始畫曼陀羅形式的“空空”。但隨著798越來越熱鬧,她開始覺得不安。“我有很大一部分時間被分割,朋友來的很多,要應酬。那個地方旅游的人也越來越多,房租越來越貴……”2008年,在著名現代藝術批評家栗憲庭老師的推薦下,熊文韻老師搬來宋莊。“我一直想有自己的院子,很幸運能來到宋莊。本來還留著城里的房子,可一旦住在這里,就越來越不想回城里。于是便把工作室的東西全部搬過來。這邊生活很健康。我的生活節奏和心境都發生了變化。離城市遠了,少了許多與人交往聚會的機會。我有足夠的時間仔細觀察大自然的變化。”
這次藝術節的主題是“跨界”,而對于熊文韻老師來說,早已引領了“跨界”的潮流。“流動彩虹”從最初的個人創作到后來形成的環保活動已經體現了藝術的強大力量。“現代物質文明對環境,對人的傳統價值觀念的破壞非常大。西藏地區的環境被破壞得很嚴重。作為一個畫家,我不能去解決,但我可以通過這個計劃喚起人們對于環保的重視。”
熊文韻老師的社會責任感更體現于她去年參加嫣然天使基金——挽救唇腭裂兒童活動。當時的她不顧自己身體不適,隨李亞鵬帶領的醫療隊去阿里救治當地的唇腭裂兒童。在醫院里,孩子們接受手術前后都很難受,熊文韻老師就在病房里與他們聊天,教他們畫畫,分散他們對于疼痛的注意力。最后,她把孩子們的畫制作成一幅大圖,李亞鵬將這幅圖帶到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上進行展示,令在場的嘉賓都感受到了唇腭裂兒童的痛苦與心聲。
與熊文韻老師聊天,讓我深深被她對于藝術的熱情所感染,創作過程的愉悅令她快樂、滿足。“空空”的不同階段,也是她不斷對人本性的感悟。“空空”也許是她,也許是你,也許是我們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