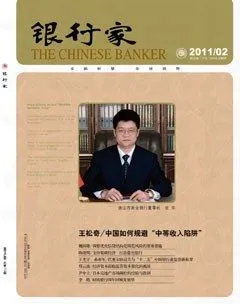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猜想
2011-01-01 00:00:00劉煜輝
銀行家 2011年2期




很少有人想到,在這么短的時間里(一年多的時間),世界經濟就從洶涌的金融海嘯中走了出來,這一切皆拜賜于史無前例的全球政府空前一致的貨幣、財政刺激。
20世紀30年代那場“大蕭條”告訴我們,不救市會有多么不好,但是救呢,沒有答案。當世界經濟出現迅速反彈時,人們以為金融危機已經遠去,經濟學家們開始憧憬下一輪增長周期的重啟。然而就在此時,反危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后遺癥也開始逐步顯現:以政府部門的“杠桿化”抵消私人部門“去杠桿化”;以大規模發鈔為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融資功能“補血”,并沒有解決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卻引發了金融風險的財政化和金融風險的貨幣化,2010年上半年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而下半年又打起了“貨幣混戰”。
歐洲:大危機沒有,小麻煩不斷
這是筆者對未來一段時期內歐洲經濟的判斷。遭遇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要想順利地走出來是相當不容易的。
7500億歐元拯救資金的動用均與IMF的貸款條件掛鉤,這意味著遭遇危機的成員國要想獲得外部援助,必須與希臘政府一樣,承諾在短期內大幅削減財政支出,以將未來的財政赤字與債務規模降低至可控水平。
大家都曾寄望20世紀90年代東亞國家迅速走出流動性危機沖擊的奇跡再度出現,但卻事與愿違。
一是全球的強勁需求不再,全球化碰到了真正的坎。美歐經濟此次不知道要蟄伏多久。
二是貨幣不可能大幅貶值。歐元區(貨幣同盟)最大的問題在于統一了金融沒有統一財政,當一國財政困境時無法通過自主的貨幣貶值加以轉移風險。而這正是當年韓國和東南亞走出困境的關鍵。
三是生產型國家在遭遇流動性沖擊后,經濟實體化和較強的工業部門成為經濟抗擊打的彈性所在。當流動性退潮,成本下去了,制造業部門競爭力是變強的,經濟承壓后很快就能恢復均衡,對企業家精神激發有利的,對于就業是有利的。
四是東亞人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認同感,痛苦忍耐力非凡,而自由民主的歐洲削減一點福利,都會激發激烈的政治動蕩。
此外,陷入危機的國家債務償付的負擔還在后面。比如希臘,2010年并非其債務償付高峰期(2010年本息償付負擔總計160億歐元),而未來兩三年內每年的償付負擔都是2010年的兩倍左右(圖1)。財政平衡若不能如預期達標時,美國的評級公司就會以此來說事(完全可以理解,歐元一旦轉軟,美元就垮不了)。
所以,這些國家的主權評級每次被下調時,歐元區銀行和金融市場的神經就得被敲打一下。因為歐元區中持續多年的套利活動(低息的西歐銀行都喜歡把大量的資金貸到高息的東南歐),使得德、法、英國的銀行體系中集聚了大量的“歐豬五國”的債權(公共債務1800億歐元,私人部門債務高達3萬億歐元)。評級下調意味著資產的重估。沒完沒了地敲打,使得歐洲的銀行體系不時地收縮,投資和消費很難進入持續的復蘇軌道。
迫于形勢,“嚴謹”的歐洲人也學會了量化寬松政策。正是由于歐洲央行在危機爆發后立即敞開了融資窗口,用收購危機深重成員國國債的方式為它們融資,至少成功地壓制了這場危機。
美國:不一樣的衰退
危機爆發已過去了兩年,全球的經濟學家對于此輪危機演變的判斷才逐步趨于一致。這的確不同于二戰之后任何一次經濟9+RSJbbIqOxVlodJBolE1g==的周期性調整,或只有從20世紀30年代那次“大蕭條”中才能找到某些相似之處。
危機確立至今已30多個月了,失業率始終居高不下,即便2010年下半年美國政府提供了50萬個臨時就業崗位(美國經濟大普查開始),失業率也未見明顯下降。這是二戰結束之后從來沒有過的。過去最長完成復蘇的一次調整周期也就耗時18個月(圖2)。
當下美國手中的要素可選的的確太少,除了金融。美國人工成本比新興國家高幾十倍,比其他發達國家都高,經濟競爭力短期提振只能從匯率和利率著手。但美元單邊主義政策已導致貨幣信用和國際匯率體系的穩定受到嚴重沖擊,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都放棄了作為國際“貨幣錨”的責任,各國匯率進入匯率的“價值重估期”(圖3)。
美聯儲在2010年9月初宣布了要實施第二輪貨幣刺激政策(QE2)(其實QE2三個月前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