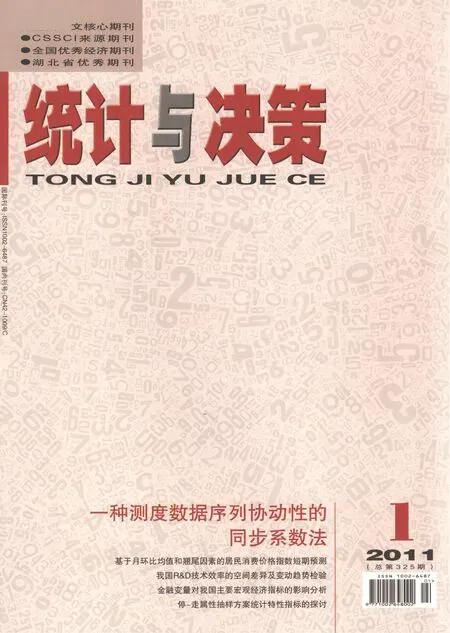我國R&D技術效率的空間差異及變動趨勢檢驗
師 萍,韓先鋒 ,宋文飛 ,周凡磬
(西北大學a.經濟管理學院;b.公共管理學院,西安 710127)
我國R&D技術效率的空間差異及變動趨勢檢驗
師 萍a,韓先鋒a,宋文飛a,周凡磬b
(西北大學a.經濟管理學院;b.公共管理學院,西安 710127)
文章以1999~2008年省級地區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模型對我國R&D技術效率進行了測度,并進一步考察了技術效率的空間差異及變動趨勢。研究發現,我國R&D技術效率平均水平較低,但呈現穩步的增長趨勢。各地區R&D技術效率存在明顯的差異,東部高于中、西部,但有逐步縮小的趨勢,不同地區間也有向各自穩態逼近的趨勢。我國R&D技術效率在空間上呈現出東高西低、南高北低、“兩極分化,東南聚集”的分布特征。
R&D技術效率;隨機前沿模型;空間差異;收斂性
0 前言
我國已經把自主創新提升到重要高度,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這就客觀上要求自主創新活動不僅要注重創新資源的投入,更要注重效率問題。一直以來,政府對科技活動均保持著強有力的支持力度,對科技資源的投入的強度也逐年持續增大,我國R&D強度(R&D/GDP)由1999年的0.76%上升到2008年的1.54%,R&D人員投入也由1999年的82.17萬人猛增到2008年的196.54萬人。但對尚處于發展階段的我國來說,R&D強度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如日本2007年為3.44%,而同時期我國僅為1.44%。因此,分析在有限資源投入的條件下,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對于我國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我國R&D技術效率的區域差異、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動趨勢。
1 研究方法
本文認為相對于DEA方法,SFA方法具有以下優點:SFA方法可以建立隨機前沿模型,使得前沿面本身是隨機的,可對研究模型的適宜性及模型中的參數進行檢驗,有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對于跨時期的面板數據而言,其結論更加接近于現實;DEA方法不能考慮到隨機誤差因素對R&D產出的影響,也忽略了價格等對效率的影響,從而導致效率估計出現偏差。因此,在模型設定合理且采用面板數據條件下,SFA方法會得到比DEA方法更好的估計結果 (Gong和Sickles,1992)[1]。基于研究樣本的特征和DEA方法的缺陷,本文選擇SFA方法測度1999-2008年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
根據Battese、Coelli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模型的基本原理[2],本文構建的:我國R&D技術效率的測度模型如下:

式中,yit、Kit、Lit分別為第 i省份第年的國內專利申請受理量、R&D 資本存量和 R&D 人員投入,β0,β1,…,β9為待估參數。 本文對 uit和 vit做如下假定e-mit反映第i個省份第t年R&D的技術效率水平,其中mit是技術無效率項,mit越大表明技術效率越低,即技術無效率程度越高。
本文重點考慮政府對科技活動的支持強度、外商直接投資、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對技術效率變化的無效率項的影響,無效率項函數設定如(2)所示:

式中,GOVit表示政府對科技活動的支持強度,TRADit表示貿易依存度,FDIit表示外資依存度,INDit表示工業化水平度,INFit表示信息化水平,t表示時間趨勢,δ0,δ1,δ2,…,δ6為待估參數,表示各因素對我國R&D技術效率的影響程度,Wit是技術無效方程的隨機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N(0,σ2W)。
判斷上述設定的模型是否合理,需考慮(1)式隨機誤差項中技術無效的比重,即考慮中 γ 的大小,當γ越接近于1,越能說明隨機前沿生產函數的誤差主要來源于隨機變量。此時,采用SFA方法對生產函數的估計也就越合適;相反,當γ=0時,表明實際產出偏離前沿產出,完全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白噪聲引起的,用最小二乘法就可以實現對生產函數的估計,無需采用隨機前沿模型。
2 變量設定與數據處理
本文的研究樣本包括30個省市區(不包括港澳臺地區、西藏自治區),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1個省市;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西部包括內蒙古、重慶、四川、陜西、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寧夏、廣西、新疆11個省市區。本文涉及的所有原始數據均來源于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9~2009)、《中國統計年鑒》(1999~2009)、《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 沿襲Griliches(1990)[3]等學者的研究,將R&D行為視為生產過程,每個省份視為R&D活動的生產單元,各自使用一定的R&D投入資源,得到R&D產出。具體數據處理及變量設定如下:
(1)產出指標
R&D與專利之間存在高度顯著的相關性,即使考慮到滯后效應也是如此[4],專利是衡量創新活動的可靠指標[5]。專利包括專利受理量和專利授權量兩個指標,專利授權量由于受到政府專利機構等人為因素的影響、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專利申請受理量比專利申請授權量更能反映R&D產出的真實水平[6]。鑒于此,本文選國內專利申請受理量(單位:項)作為衡量R&D活動的產出指標。
(2)投入指標
根據R&D活動的特征及我國統計指標的特點,本文選取R&D人員全時當量(單位:人年),作為衡量R&D活動的人員投入指標。涂正指出,R&D投資對產出的影響很大程度是前期投資累計的結果,即R&D資本存量,而不僅僅是R&D經費支出[7]。我國現行的統計年鑒中只有R&D經費支出數據,沒有R&D資本存量數據,根據Griliches(1990)、吳延兵(2008)[8]的做法,本文采取永續存盤法來核算R&D資本存量。R&D資本存量的測算模型如下:

式中,Kit和 Ki(t-1)分別表示第i個省區第t和t-1期的R&D資本存量,δ為折舊率,根據Griliches(1990)、吳延兵(2006)[9]等對 R&D 資本折舊率的估計,取 δ=15%,Ei(t-1)表示第個省區第的實際R&D經費支出,其值用朱平芳和徐偉民(2003)構造的 R&D價格指數[10],即 R&D價格指數=0.55×消費價格指數+0.45×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以1998年為基期,對R&D經費支出進行平減。
估算R&D基期資本存量時,本文假設R&D資本存量的增長率等于R&D經費的增長率。基期資本存量的測算模型如下:

式中,Ki0為R&D基期資本存量,Ei0為基期實際R&D經費支出,g為考察期內實際R&D經費支出的平均增長率,δ為R&D資本折舊率。根據模型(3)、(4)即可計算出 1999~2008年我國30省市區的R&D資本存量(萬元)。
(3)影響因素變量
本文設:(1)GOVit為省份年度的財政科技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2)TRADit為省份年度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年GDP的比值,其中,對于用美元表示的所有進出口總額數值,均按當年的人民幣平均匯率將其換算為人民幣。(3)FDIit為省份年度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GDP的比值,它可以從整體上反映各省份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規模。其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按照當年人民幣的平均匯率換算為人民幣,再進行測算。(4)INDit為省份年度的工業總產值與GDP的比值,用來反映工業化水平對R&D活動無效率的影響。(5)INFit為省份年度的郵電業務總量與全國郵電業務的總量的比值,用來反映信息化水平對R&D活動無效率的影響。
3 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模型和數據,運用Frontier4.1軟件對我國1999~2008年R&D技術效率進行了估計,結果如下。
3.1 研究模型適宜性的假設檢驗
為了檢驗本文采用超越對數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分析我國R&D技術效率的適宜性,我們設定了以下5個研究假設,具體如下:
假設1:在生產函數形式的選擇上,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5中所有二次項系數均等于零)優于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假設2:1999~2008年間,我國R&D活動不存在技術進步,即模型5中所有和時間有關的項的系數都等于零。
假設3:1999~2008年間,我國R&D活動的技術進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模型5中投入要素R&D資本存量、R&D人員全時當量與技術進步t交叉項系數為零。
假設4:1999~2008年間,我國30省市區R&D活動均處于生產前沿面上,即隨機誤差項所代表的技術非效率影響為零,此時平均生產函數就是生產前沿面,用普通最小二乘法(COLS)估計出來的平均生產函數可以很好的描述樣本的生產活動過程,無需采用隨機前沿方法來估計函數形式。
假設5:1999~2008年間,我國R&D技術效率不具有時間趨勢,即技術無效率函數中的時間項系數為零。
上述5個假設用廣義似然率統計量進行檢驗,統計量的檢驗模型為:

式中,L(H0)和L(H1)分別是前沿面生產函數模型(1)和(2)在零假設和備擇假設下的似然函數值。自由度q是受約束變量的數目,備擇假設H1為不受約束的模型(1)和(2)。檢驗結果見表1。
從表1的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所有假設均被拒絕。假設1被拒絕,表明超越對數生產函數更適宜于本文研究,若采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形式會產生較大誤差;假設2被拒絕,意味著考察期內R&D活動技術進步是顯著的;假設3被拒絕,表明R&D活動過程中技術并不獨立于生產要素,技術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說技術進步會影響要素間的邊際技術替代率;假設4被拒絕,說明1999~2008年間,我國R&D技術非效率是顯著存在的,樣本均處于生產前沿下方,因此傳統的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得到的平均生產函數不適用于本文的研究;假設5被拒絕,可以認為考察期內我國R&D技術效率是隨時間變化的。由此可見,本文建立的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測度模型是合理的,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度,同時也說明模型測度結果是精確的。
3.2 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的空間差異分析
根據表2可以看出,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的如下事實:
(1)1999~2008年間,全國R&D技術效率均值為0.256,該值高于閆冰和馮根福(2005)所得到的整個工業行業R&D效率均值水平(0.16)[11],但略低于朱有為(2006)所得到的中國高新技術產業R&D效率均值水平(0.258)[12],這表明我國整體R&D技術效率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時間角度看,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從1999年的0.249已升至2008年的0.262,可見我國R&D技術效率雖然低下,但呈現增長趨勢。
(2)從整個考察期的區域R&D的平均技術效率差異來看,東部地區(TE=0.4239)>(全國平均水平 TE=0.256)>中部地區(TE=0.1828)>西部地區(TE=0.141),東部地區 R&D 技術效率值遠遠大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R&D技術效率均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可見我國R&D技術效率存在著明顯的區域差異,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R&D技術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可能是:較中、西部而言,東部地區經濟實力雄厚,在R&D活動基礎設施,人才和制度建設等方面已形成較完備的體系,有力的促進了R&D效率的提高;而中、西部地區經濟水平較低,削弱了其在R&D環境建設方面的能力,進而也制約了R&D活動的有效發展。1999年東、中、西部地區R&D技術效率分別為0.416、0.191、0.125,2008 年其值變為 0.421、0.193、0.155,說明R&D技術效率的區域差異有縮小的趨勢。

表1 零假設及檢驗結果

表2 1999~2008年各地區R&D技術效率(TE)

表3 絕對β收斂檢驗結果

為了進一步考慮我國R&D技術效率的空間分布,本文按照1999-2008年間平均技術效率繪制了技術效率的地理分布圖,見圖1。可以看出,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的空間分布很不均衡,有很大的變異性,我國R&D技術效率在地理空間上呈現出東高西低、南高北低、南高北低、“兩極分化,東南聚集”的分布特征。R&D技術效率高的省市區密集于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地區,R&D技術效率較低的省市區主要集中于西北、西南地區。這充分表明我國R&D效率的空間布局還不夠合理,我們認為這主要還是與各省市區的經濟發展水平,R&D人員素質,政府、企業、研發機構等對R&D活動的支持程度、對外貿易等因素有關,東南沿海地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門戶,可以充分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在人才引進、制度建設、設施水平等方面遠遠優越于中、西部地區 ,最終導致我國R&D技術效率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根據R&D技術效率分布圖,可以把我國30省市區的技術效率由高到低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北京、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上海等8省市;第二類: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河南、河北、黑龍江、天津等8省市;第三類:新疆、云南、貴州、廣西、海南、江西、安徽、吉林等8省區;第四類:西藏、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山西、內蒙古等7省區。
3.3 我國地區R&D技術效率的變動趨勢分析
鑒于技術擴散的作用往往會導致后進地區從中受益,后進地區對先進地區的模仿、趕超或先進地區的“技術溢出效應”也會成為后進地區的“技術后發優勢”。新技術的擴散、傳播和轉移速度的加快,以及后進地區技術學習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最終會實現技術水平的跨越(Abramovitz,1986[13];Blomstrom,2003[14])。因此,本文應用借助收斂檢測方法,對地區間R&D技術效率的收斂或發散情況進行相應的測試。借鑒Barro和Sala-i-Martin(1992)的分析模型,采用如下的檢驗收斂性的回歸模型:

式中,gi0和giT分別為各地區期初與期末R&D 的技術效率,T為觀察期時間跨度,α為常數項,β為收斂系數,εt為隨機擾動項。如果β為負,則說明區域間的R&D技術效率趨于收斂,反之則發散。上式所表示的收斂又叫絕對β收斂,表示各地區均會達到相同的穩態增長速度和增長水平。運用SPSS17.0對模型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看出,全國R&D技術效率β系數為負值,且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1999~2008年,我國R&D技術效率呈現收斂趨勢,這意味著我國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R&D技術效率的增長速度存在不斷縮小的趨勢。從地區角度分析發現,東、中、西部三大地區β系數均為負,其中西部地區β的收斂系數顯著通過檢驗,東、中部地區β的收斂系數系數雖不顯著,但總體上說明我國各地區R&D技術效率亦存在所謂的追趕效應。從收斂速度上看,東部、西部R&D技術效率均居全國水平之上,且西部收斂速度遠高于全國水平和東、中部水平。
4 小結
本文以1999~2008年省域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模型對我國R&D技術效率進行了測度,并進一步考察了技術效率的空間差異及變動趨勢。研究發現:我國R&D平均技術效率水平偏低,僅為0.256,但呈現穩步上升狀態。我國R&D技術效率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東部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但有逐步縮小的趨勢,且不同地區間也有向各自穩態逼近的趨勢。我國R&D技術效率在空間上呈現出東高西低、南高北低、“兩極分化,東南聚集”的分布特征。
[1]Gong B H,Sickles R C.Finite Sample Evid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tochastic Frontiers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Using Panel Data[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2,(51).
[2]Battese,G.E.,Coelli,T.J.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 Data[J].Empirical Economics,1995,(20).
[3]Griliches,Z.Patents Stastics as Economic Indicators:A Surve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0,(28).
[4]Goto,A.,K.Suzuki.R&D Capital,Rate of Return on R&D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s of R&D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4).
[5]Acs Z J,Anselin Luc,Varga Attila.Patents and Innovation Counts as Measures of Regional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J].Research Policy,2002(31).
[6]張海洋.R&D兩面性、外資活動與中國工業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000,(5).
[7]涂正革,肖耿.中國的工業生產力革命———用隨機前沿生產模型對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分解及分析[J].經濟研究,2005,(3).
[8]吳延兵.中國地區知識生產效率測算[J].財經研究,2008,(10).
[9]吳延兵.R&D存量、知識函數與生產效率[J].經濟學(季刊),2006,(4).
[10]朱平芳,徐偉民.政府的科技激勵政策對大中型工業企業R&D投入及其專利產出的影響—上海市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3,(6).
[11]閆冰,馮根福.基于隨機前沿生產函數的中國工業R&D效率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5,(11).
[12]朱有為等.中國高技術產業研發效率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11).
[13]Abramovitz,M.“Catching Up,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in 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4]Blomstrom,M.,Kokko,A.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entive[M].Berlin:Spring,2003.
F223
A
1002-6487(2011)01-0077-03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07JA630067);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0873095)
師 萍(1949-),女,陜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技術經濟及管理。
(責任編輯/易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