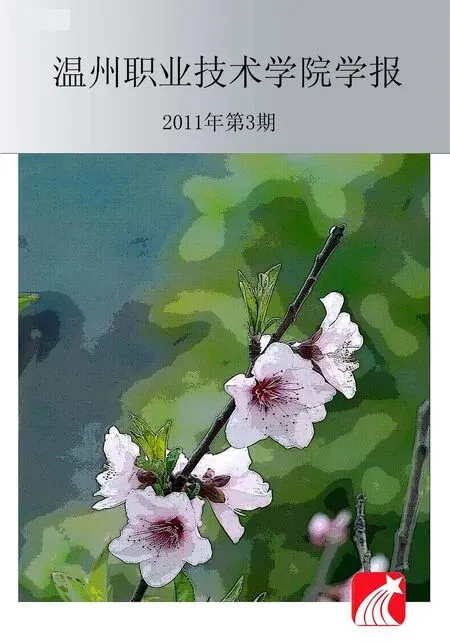城市化發展的國際經驗及浙江城市化發展的對策
聶獻忠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杭州 310025)
城市化發展的國際經驗及浙江城市化發展的對策
聶獻忠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杭州 310025)
城市化發展的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 10 000美元階段必須走“要素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服務進一步向中小城市均衡”的集聚型均衡發展道路。浙江城市化正處于集聚型均衡發展階段,集聚型均衡發展模式是其必由之路。浙江應大力提升大城市的主導地位,建設高速軌道交通網以推進大郊區化進程,大力構建中小城市均衡的公共服務,形成中小城市內生的發展動力。
浙江;城市化;國際經驗;集聚型均衡
“十二五”時期是浙江城市化進程加快和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浙江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業界對“優先發展大城市”還是“優先發展中小城市”一直處于爭論之中。國際經驗表明,單一的大都市集聚型發展模式很容易加大城鄉差距并帶來諸多社會矛盾,人口與要素資源過度向大城市集聚反而會阻礙城市化進程;反之,重點選擇縣域城市化發展模式,雖然能大力促進中小城鎮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又會造成要素分散,不利于吸引高端要素資源進而缺乏強大的核心引導,不利于形成強大的核心競爭力。實際上,從城市化發展的國際經驗看,各種規模城市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在歐美、日本和韓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更多是從實際出發,形成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并舉、層次遞進、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網絡式、金字塔型的集聚型均衡結構體系。
浙江能否跨越當前“集中型非均衡增長”城市化模式,有效化解交通堵塞、教育不均衡及衛生醫療不夠完善等眾多矛盾與問題,關鍵在于突破“大城市主導動力不強、中小城市(或城鎮)公共服務均衡不夠”①本文所指大城市為人口在1 0 0萬以上的城市;中小城市(或城鎮)為人口在1 0 0萬以下的城市,主要包括舟山、麗水和衢州等地級市、各縣級市和縣域中心鎮。的兩大結構性難題,并尋找到適宜自己的城市化發展道路。
一、城市化發展的四個階段
西方國家的城市化自18、19世紀開始,到現在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城市化率基本達80%以上;而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在20世紀加速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率也已達到80%以上。尤其是日本,1947—1965 年間,僅用18年時間城市化率就由33.1%提高到68.1%,年均提高1.94%,年新增城市人口約228萬人;其中1947—1955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2.9%,城市人口每年增加305萬人[1]。
從國際發展歷程看,城市化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2](見表1)。城市化率不足30%,城市人口主要從農村遷入城市;30%~50%之間,中小城市人口等要素開始向大城市集中;50%~70%之間,人口繼續由小城市向大城市轉移,大城市則優先發展出現大郊區化趨勢,城市郊區人口增長較快,大城市周邊出現大量的衛星城,形成龐大的都市圈;70%則是美國地理學研究認為趨于穩定的發展階段。可見,城市化率不足70%,要素集中一直是中心主題,尤其是城市化率在50%~70%(人均GDP 6 000~10 000美元)之間這個階段,“大集中”是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即更多更高等級要素持續向大城市集聚(但要素資源向郊區和中小城市的分散是零散的、小規模的),交通與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持續向中小城市擴散。而且,城市化率在30%~70%之間的加速發展階段,由于農村人口遷入城市和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轉移,產生大量的居住需求,從而導致地價和房價的上漲。

表1 城市化發展四個階段的相關特征及比較
先行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雖各有特點但具有相似規律,尤其是人均GDP 10 000美元階段的成功推進模式值得浙江借鑒。
二、浙江城市化發展階段的判定
按1987年購買力計算,2010年浙江人均GDP約7 600美元,城市化率約為59%。根據浙江省“十二五”規劃,預計2013年人均GDP可達10 000美元(或可提前),2015年城市化率達65%左右。可見,“十二五”時期基本上是浙江人均GDP處于10 000美元的發展階段[3]。但總體而言,浙江城市化水平仍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1.浙江處于集聚型均衡發展階段
集聚型均衡是指以大城市的要素資源集聚為主導動力、中小城市公共服務均衡發展的空間格局。具體來說,城市規模等級體系中不同等級城市的居民能夠享受相似水平的公共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服務。不同等級規模城市之間在人才、資源等要素上能夠自由流動,逐步實現城市居民與鄉村農民的自由流動以及權利與收益的基本相等。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大城市的強大帶動、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均衡發展,使得不同地區、不同規模等級城市的居民有相似的生活水平和享受公平的競爭機會。
實現集聚型均衡發展需要達到以下目標:一是通過強化大城市要素與現代產業“大集中”,推進浙江大城市主導地位的提升。而城市人口增加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人數逐步上升,又會帶來新的消費需求,推進消費品行業轉型升級進程。二是通過加快以中小城市為重點的縣域城市化進程,更大釋放城市化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潛力。其中農村服務業是關鍵,服務業的發展有助于帶動城市化向縱深推進。三是通過縣域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廣泛吸納農村人口,將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城市化所帶來的投資需求將有利于消化過剩的產能。四是通過集聚與均衡的共同推進,更好實現“共富裕、享增長”的城市化目標。
2.集聚型均衡發展模式是浙江的必由之路
與國際同等工業化水平國家和地區相比,浙江城市化水平大約滯后15%~20%[4]。推進浙江城市化加速發展,關鍵在于以集聚型均衡為指導,進一步強化大城市中心集聚。其主要理由是:一是浙江大城市中心帶動力不夠強大。世界各國發展經驗表明,經濟活動(尤其是人口要素)集中于大城市不可避免。浙江經濟活動集中于杭州、寧波和溫州地區,是導致省內區域和城鄉差距的一個關鍵因素,但這種集中所產生的集聚經濟效應也是生產率增長和競爭力的主要來源,大城市持續擴張形成的強大推動力不言自明。但目前浙江大城市數量明顯不足,大城市帶動作用也明顯不強,尤其是在“都市圈、都市帶”體系上明顯缺乏強大的中心吸引力。二是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務功能不足。中小城市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和落后的非均衡空間結構,已經嚴重制約著浙江城市化進程和競爭優勢。從浙江城市化發展現狀看,城市化模式總體上處于非均衡狀態,大城市擁有更優質的教育、醫療、公共衛生等資源,對遷移人口形成強烈的吸引力;中小城市教育、醫療等優質資源少,難以吸引真正的優秀人才和企業項目,導致規模集聚效應難以發揮:農村地區人才、資金外流,出現“空殼化”或“臟亂差”現象。這種非均衡城市化模式不僅造成高房價、大城市病,而且對轉變發展方式和調節居民收入分配都將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甚至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這兩大結構性矛盾決定“十二五”時期的浙江必須走集聚型均衡發展道路,才能有效化解大城市動力不強、中小城市服務不足的難題。因此,在人均GDP 10 000美元的階段,“以要素產業向大城市集中、公共服務向中小城市擴散的集聚型差異化均衡”發展道路是浙江的必然選擇。
三、國際經驗與教訓
在人均GDP 10 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先行國家和地區在城市化發展戰略方面,以集聚促均衡有力地推進了城市化加速發展。
1.國際經驗
(1)“軸式集聚、兩翼擴散”的均衡模式。日本的城市化起步于20世紀20年代,發展于戰后高速增長時期,此后進入成熟階段,經歷了“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的標準S型曲線過程。日本城市化加速后,人口、產業大量向東京、名古屋和大阪等中心城市集聚,促進了中心城市發展和城市功能的均衡完善。這一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征為:一是社會均等化發展,首要標志是經濟收入差距縮小。這與日本政府實施的高就業制度與就業保障政策、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稅收政策、收入再分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社會制度有關。二是消費成為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和日本經濟多年的高速增長。
日本城市化率在50%~70%之間的城市化加速階段的主要經驗是:一是強力推進人口與要素向大城市集聚,并通過大城市郊區化化解分散壓力。以東京都市圈為例,二戰后東京迅速集聚發展成為超大城市,受東京的輻射和影響,神奈川、千葉、琦玉等周邊地區通過接受產業轉移、為中心城市提供服務等,分擔中心城市功能,發展成為以東京為核心的城市群。目前,東京都市圈人口超過3 4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27%;面積占全國的3.7%;經濟總量占全國的31%[5]。二是全面構建快速交通服務網絡。三大都市圈的快速輕軌交通以快速、高效而聞名于世,快速輕軌交通的建設為現代化城市交通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三是大力完善提升中小城市的服務功能和水平,不斷縮小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差距,消除城鄉發展的制度和經濟鴻溝。
(2)“中心集聚、面狀分散”的均衡模式。歐洲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主要采取向諸多大城市的相對平衡集聚,以及向各等級中小城市或城鎮規模體系的均衡發展。其城市化加速發展的主要經驗是:一是多中心型城市集聚。德國有11個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國各地,中小型城市星羅棋布,城鎮規模不大,但基礎設施完善。德國先注重大城市之間的均衡,然后與中小城市或城鎮協調發展。二是注重生態與生活環境(包括公共服務)的均衡[5]。在城鄉建設和區域規劃的政策上,注重形成平等的生活環境,追求可持續發展。這種城市化模式不容易造成人口、資源的過度集中和要素資源價格過度高漲,有利于經濟平穩運行。三是大力發展特色農業,保證中小城鎮不落后。法國采取強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全面保障農民權益,并時刻將人的生存空間放在重要的位置;德國則以特色產業推動縣域城鎮化發展,包括建立中小型城市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完善的法制體系和平等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以“農村經濟發展行動聯盟”等系列計劃促進生態產業鏈等。
2.“拉美陷阱”的教訓
大城市動力不強和中小城市服務不足,是“拉美陷阱”的主要教訓。拉丁美洲和南亞地區(如菲律賓等)是戰后人口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地區,約3/4的人口生活在中小城鎮[6],但由于其大城市始終未能形成足夠規模,大城市的帶動力不強,從而不能為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提供支撐。同時,在進入快速城市化過程中,中小城鎮的各項社會服務功能嚴重缺乏而不均衡,使得它們很快跌入經濟發展受社會問題鉗制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貧民窟城市成為拉美城市化模式揮之不去的陰影。“十二五”時期浙江城市化應警惕“拉美陷阱”的城市化發展道路。
四、浙江城市化發展的對策
1.以“大城市促大空間”,大力提升杭州等大城市的主導地位
改變以往各類要素資源“粗放式”的向大城市集中的模式,從戰略創新角度,強力推進杭州、寧波和溫州大城市發展,形成集約型、質量型的主導型“大集中”。與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相比,杭州和寧波對集聚高端人才等要素資源還缺乏強大的吸引力,甚至因房價因素還遜于武漢、蘇州、大連等城市。因此,杭州和寧波應未雨綢繆,盡早規劃2 000萬人的城市圈規模,通過中心城區的高素質集聚與強大吸引力、郊區網絡(交通與信息)的大力擴張延伸,形成中心集中、軸式延伸的城市化空間格局,更加突出“新、高、優”要素向大城市集中的整體格局。在產業選擇上,中心城區主要發展高新產業、金融等現代服務業,而要素與資源向郊區和衛星城的擴散、制造業的轉移則需要通過快捷的交通信息網來實現。
2.以“大交通促大郊區化”,建設高速軌道交通網以推進大郊區化進程
有效降低大城市集聚過程中的交通擁堵等城市病,需要參考國際經驗,大力建設城市軌道交通網并不斷創新優化。杭州、寧波和溫州等大城市乃至金華、義烏等不僅要通過高架、地下鐵實現與一環的30分鐘連接,還要規劃實現主干道與二環的1h連接,遠期規劃1.5~2h的三環高速交通網,從而全面覆蓋周邊縣域,實現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交通均衡發展。這樣,通過三環網絡就可基本實現全省高速交通的無縫對接,屆時浙江城市化的均衡發展也就基本成型并趨于穩定。同時,為化解大城市可能出現的交通擁堵等弊病,需要依托高速軌道交通網絡,推進大城市大郊區化進程。杭州、寧波和溫州等大城市近期可把0.5h副城的郊區化推進到1h以內,遠期推進到2h郊區化。
3.以“均等機會促均等發展”,大力構建中小城市均衡的公共服務
在不斷強化大都市的主導作用下,浙江應切實以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重點,通過推進縣域城市化進程,采取縮小差距、實現“共享增長”的均衡型發展,即圍繞以縣域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均衡發展結構。在構建中小城市均衡的公共服務方面,人的發展為根本出發點,政府應將重點放在對人的投資上,確保更加平等的基礎教育、技能培訓和醫療衛生服務。根據近年來在改革義務教育融資方面取得的進展,建議逐漸增加補貼以取代學雜費,并加強對教育績效的多維度考評和監測;在技能培訓方面,可采取績效預算制度、培訓券和培訓基金,以保證公共經費支出確實帶來效果;在深化農村衛生改革方面,應強化醫療救助制度的作用并試點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籌從縣級提高到省級。公共服務的均衡化,最終目標是實現開放式均衡,即在省內達到農民能自由成為市民,市民能自由成為農民的發展階段。
4.“以大政策促大發展”,形成中小城市的內生發展動力
縣域城市化不是一條“模式統一、千篇一律”的發展道路,而是特色各異的差異化發展道路。因此,提升縣域中小城市發展動力、形成多元化發展,必須強化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縣域城市化發展的關鍵,不是城市建設水平和質量形象提高的問題,而是就業、環境、社會保障、產業發展等問題。縣域城市化充滿機遇與挑戰,它不是簡單的戶籍關系轉移而是要讓城鎮對農村人口有吸引力,這種吸引力更多地體現在養老、就業、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支撐。政府可以通過確保全民享有更加平等的機會,促進農民收入提高、便利農村勞動力向非農就業轉移。同時要積極推進金融支持,實現中小城市均衡發展,尤其是深化金融改革,包括有選擇地在縣域城鎮開展村級會員制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試點,重新設計促進農戶和微小企業融資的財政激勵措施,真正實現以廣大農村和農民“人的全面發展”,推動區域均衡發展。
[1]巴曙松.從日式泡沫審視中國房地產[N].第一財經日報,2010-11-25(A8).
[2]星彥.城市化是房地產發展的基石[EB/OL].(2010-10-08)[2011-04-30].ht t p://news.di chan.si na.com.cn/.
[3]聶獻忠.浙江“十二五”發展速度之辨[J].浙江經濟,2011(2):32-33.
[4]孫永森.浙江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EB/OL].(2010-01-23) [2011-04-30].ht t p://www.chi naci t y.org.cn/csf z/f zzl/51555.ht m l.
[5]劉華,李學梅.周谷風城鎮化“他山之石”—走進國外小城鎮[J].半月談,2010(3):26-28.
[6]全毅,張旭華.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東亞和拉美地區的比較[EB/OL].(2007-12-04)[2011-04-30]. ht t p://www.chi naref orm.org.cn/ci rdbbs/di spbbs.asp?boardi d=12&I d=149507.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Zhejiang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NIE Xianzho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25, China)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hows that at the stage of per capita GDP $ 10,000, it is important to adopt the cluster and balanced developing mode of "clustering the elements around the big cities, spreading the servic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e urbanization of Zhejiang is at the stage of cluster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l is indispensable. Zhejiang should improve the leading role of big cities, building the high-speed railway transportation net to expand the urban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service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create the internal developing force of them.
Zhejiang;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luster and balanced mode
F291.1
A
1671-4326(2011)03-0041-04
2011-05-29
浙江省委省政府重大決策理論支撐研究課題(2011ZDZC02);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課題(201122210)
聶獻忠(1972—),男,安徽潛山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吳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