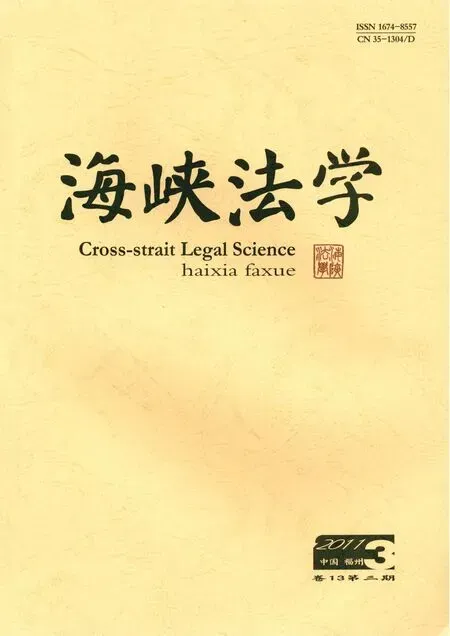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檢察實踐──以輕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實證研究為基點
林占發,陳家標
(1.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福建泉州 362000;2.廣東省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廣東東莞 523000)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檢察實踐──以輕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實證研究為基點
林占發1,陳家標2
(1.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福建泉州 362000;2.廣東省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廣東東莞 523000)
依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檢察機關以和解制度為契機,以相關法律規范為基礎,透過相關實務數據和現實案例的分析,研究檢察機關針對輕微刑事案件運用和解制度的實證運作效果,以期達到寬嚴相濟的檢察效能。
輕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寬嚴相濟
對于法律的理性研究在今天可能屬于和白紙黑字打交道的人,但是未來它卻會屬于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
——O·W·霍姆斯[1]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基于刑罰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刑罰資源的有限性以及刑罰謙抑性觀念而產生的,它認為有限的刑罰資源應當使用到最需要刑罰規制的地方。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和“恢復性司法”的基本特點,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建立健全檢察環節社會矛盾糾紛排解機制,不斷深化輕微刑事案件和解機制(“等腰三角形”模式、關注易和解案件成效、不捕不訴詳細說理充分論證等),努力把輕微刑事案件中的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做到“寬”見成效、“嚴”格規范、寬嚴相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一、檢察機關輕微刑事案件和解概覽:“寬”見成效
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全國檢察機關要認真研究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體措施,在各項檢察工作中正確運用這一刑事政策,做到當寬則寬、該嚴則嚴,提高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的水平。一方面,要繼續貫徹“嚴打”方針,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不能把寬嚴相濟片面理解為一味從寬,從而影響打擊犯罪的力度,造成新的社會不和諧。另一方面,要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該寬的、能寬的,就盡量依法從寬。要著眼和諧,致力和諧,努力改進執法方式,探索正確運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新途徑、新機制。要研究制定對輕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從寬的具體意見。通過檢察機關的各項工作,盡可能地減少社會對抗,盡可能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促進社會的和諧。
“刑事和解”是中國式的用語,在西方則稱為“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或者Victmi-Offender Mediationor,簡稱VOR或者VOM)[2],刑事和解的基本內涵是在犯罪發生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使被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洽,推進在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直接交流,解決刑事糾紛,對于和解協議,由司法機關予以認可并作為對加害人刑事處罰的依據[3]。我們中國經常提及“和合”一詞,儒學大師錢穆也認為“中國人的天性,所謂我們的國民性,是‘和合’的分數比較多過‘分別’的。”[4]筆者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刑事和解問題,因為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5]

圖1 昆明市兩級檢察機關辦理輕微刑事案件人數圖

圖2 昆明市兩級檢察機關辦理輕微刑事案件比例圖
在討論刑事和解制度之前,我們先看下現行輕微刑事案件的人數和比例(如圖1和圖2所示),2004年昆明市兩級人民法院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拘役、管制、單處罰金 4051人,占有罪判決總人數的 49.40%;2005年的數據是 4094人,占有罪判決總人數的50.76%;而2006年的數據為4098人,占有罪判決總人數的52.86%,人數和比例均逐年上升。[6]
從圖1和圖2的昆明市兩級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人數和數量中,我們可以發現輕微刑事犯罪在所有的刑事犯罪中占據較大的份額,由此可能產生兩個后果:一方面,輕微刑事案件的增加與有限的司法資源之間的矛盾日趨突出;另一方面,單純刑罰手段可能無法達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某些輕微犯罪能否采用刑事和解程序予以解決?2008年以來,三門峽市湖濱區人民檢察院對輕微刑事案件68案102人依法適用刑事和解。回訪表明,無一出現反復,無一引發上訪,無一重新犯罪。[7]這樣的“零反復”、“零上訪”、“零犯罪”是否顯示出刑事和解對輕微刑事案件的療效?在我們這個十分重視“和諧”特質的鄉土中國,是否考慮從“重打擊”向“重挽救”的思維轉變?我國臺灣地區“緩起訴”制度要求檢察官應當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基礎上才能作出“緩起訴”決定,也正是刑事起訴中和解制度應當進行公共利益衡量這一訴訟理念的體現。無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中,在立法、理論或實踐上,都要求檢察機關在行使公訴權時必須符合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和最大多數人的普遍期待,都將公共利益衡量視為如何運用起訴便宜原則的核心問題。
案例1:2008年6月,張某和同事謝某等人在一飯店吃飯時發生口角。張某抓起桌子上一個杯子向謝某砸去,恰好砸在謝某的右側面部,經鑒定為輕傷。張某、謝某本是同事,全運會在即,張某正備戰有把握奪獎的舉重項目。案件移送到永川區檢察院,檢察官發現該案具備刑事和解的基礎。經調解,雙方最終達成賠償協議并落實賠付。該院依法對張某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考察期三個月。經檢察機關批準,張某帶隊前往天津進行異地訓練。在第十一屆全運會上,張某所訓練的運動員在女子48公斤級舉重比賽中獲得總成績第五名。[8]
“張某事件”只是重慶市檢察機關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個縮影,2010年重慶市檢察機關對1005件因親友鄰里、同事同學糾紛等引發的輕微刑事案件,促成雙方和解后,依法不予起訴或建議法院從輕判處,以努力修復社會關系,這樣有效地化解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比適用刑法更加合理。英國法哲學家邊沁曾經指出,當刑罰在濫用、無效、過分、太昂貴時,不應當適用刑罰。[9]從以上的數據和案例我們可以發現,輕微刑事案件的和解制度在很大程度在促進了社會矛盾的化解,實現了“寬”的效能,但是一個好的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和量化,以促使其更加高效與完善。
二、檢察機關輕微刑事案件和解的分析:“嚴”格規范
1.杜絕“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發生
當今社會是商品經濟社會,檢察官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既要承受洶涌澎湃的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又要擺脫層層人情關系網的束縛。如何奉公執法、恪盡職守,同時又要處理好身邊的各種關系是我們不容回避的嚴峻課題。
案例2:犯罪嫌疑人翁某無證駕駛小型面包車由石城縣往瑞金市方向行駛至瑞金葉坪鄉路段,不慎將年僅六歲的被害人鐘某撞倒并卷入車底。翁某撞人后未停車,反而加速逃離事故現場,導致被害人鐘某被掛在車底拖行三十余公里,造成身體右前側和左下肢右側嚴重擦傷、腦組織外露、胸腹及臟器缺損,其狀況慘不忍睹。案件發生后五天,犯罪嫌疑人翁某被公安局抓獲歸案并移送瑞金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在審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家屬與被害人家屬就民事賠償問題進行協商,由犯罪嫌疑人賠償被害人人民幣二十余萬元。雙方協商后,犯罪嫌疑人家屬以達成和解為由申請不捕。[10]
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嚴重暴力犯罪,擾亂金融秩序、市場秩序的犯罪,有組織犯罪;犯罪嫌疑人可能有其它犯罪事實有待進一步偵查的案件;共同犯罪中有同伙在逃,適用刑事和解影響對犯罪事實的進一步偵查的案件;當事人雙方情緒尖銳對立,根本利益沖突,適用刑事和解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案件;雙方當事人是否自愿達成諒解不明確的案件,在審查逮捕階段均不宜適用刑事和解。[11]對于案例2中犯罪嫌疑人翁謀肇事逃逸行為惡劣,而且不存在諸如自首等情節,不適宜刑事和解,應當避免該類案件因某些原因而出現“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
2.和解中加害人承擔責任的方式過于單一
在當前輕微刑事案件的和解中,受害人在收到加害人的賠償款之后案件就基本全部辦理結束了,有些案件可能還存在訓誡、具結悔過、賠禮道歉等幾種附加形式。其實加害人的精神賠償和受害人的精神撫慰也是重要的責任方式,諸如社區服務,管教協助,保護觀察處分,交納保證金,定期匯報學習、生活情況等輔助懲戒和幫教措施,值得我們在檢察實踐中進行考慮,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受害人的精神上的賠償才是發自內心的賠償,這也是輕微刑事案件和解的關鍵前提。
案例3:2010年4月,重慶市石柱縣檢察院在辦理黎某故意傷害一案中,案件承辦人發現嫌疑人黎某不是出于真心悔罪,而是以利益為誘餌,試圖通過被害人申請檢察機關對其不起訴,逃避法律的制裁。對此,該院立即終止了和解,并依法對黎某提起了公訴。[8]
正如案例3所示,刑事和解與“花錢買刑”最根本的界限就在于加害人是否真誠悔罪、賠禮道歉,獲得被害人的諒解。如果當事人以降低刑罰標準作為賠償數額的條件,那么就證明其賠償之意在于“買刑”,也就違背了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即使其達成了所謂的和解協議,也將不被允許。賠償損失應該與被告人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害相適應,并以被告人的真心悔過為前提,否則的話就會出現新的司法不公。通過因地制宜不同形式的和解,才能多角度地考慮被告人是否真心悔過,也從另一個方面避免被害人過分注重物質賠償從而漫天要價。
三、具體數據和案例的推演:寬嚴相濟
2007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隨后還出臺了《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使各地檢察機關掌握“寬嚴相濟”有了具體尺度。 筆者以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以通過對“寬”、“嚴”和“濟”這三個關鍵詞進行語義學上的分析,從而揭示其基本內涵。前文兩個部分分別從“寬”和“嚴”兩個角度進行論述,下文筆者重點論述兩者之間的“并濟”,即寬中有嚴、嚴中有寬。
1.“等腰三角形”模式定位輕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的精髓
刑事和解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犯罪人對被害人的悔罪、道歉以及物質與精神損害的賠償;二是被害人對犯罪人的寬恕、諒解以及放棄追究其刑事責任的表示;三是受到犯罪影響的各方修復社會關系的解決方案。[12]但現實的檢察實踐中經常出現以下三種濫用情況:一是檢察人員權力的濫用,少數檢察人員利用刑事和解權收受當事人賄賂,以案謀私,強迫和解,或以刑罰代替和解威脅當事人;二是被害人權利的濫用,被害人會利用加害人急于刑事和解的心理而漫天要價,獲得“不對等”的賠償;三是加害人權利的濫用,加害人通過種種途徑,采取種種不當甚至違法的手段影響受害人,迫使其“自愿”和解。

圖3 輕微刑事案件“等腰三角形”模式

圖4 檢察機關輕微刑事案件和解監督圖
因此筆者以為可否參考一下“等腰三角形”模式進行約束和定位輕微刑事案件和解中各方扮演的角色。如圖3所示:在“等腰三角形”的上方是檢察官角色,應當不偏不倚,不能收受任何一方的財物,堅決做到秉公執法,有效化解矛盾;在“等腰三角形”的下方,加害人和被害人處在和解的雙方,權利平等,義務相當,履行和解的自主、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則,加害人真心實意地悔過并履行相應的賠償義務,被害人接收合理的賠償并寬恕和諒解加害人的罪行。
這里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這個“等腰三角形”當中,最需要規范的一方應當是檢察官的角色定位,因為其權力最容易被濫用。如圖4所示,檢察機關內部可以通過檢務督察制度對因達成刑事和解擬作不批準逮捕、不起訴案件實施監督。達成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以刑事和解協議書或刑事和解調解書的形式載明并入卷,同時,報檢務督察辦公室和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備案。紀檢、監察部門可以通過對本院辦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不定期隨機抽查,對辦案人員是否廉潔、文明、公正執法進行監督。從外部看,公安機關不同意和解的,可要求作出決定的檢察機關進行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以向上級檢察機關提請復核。加大社會公眾監督力度,參與刑事和解的當事人及其近親屬、其它社會參與主體以及其它國家機關、公民,發現檢察機關在主持刑事和解活動中存在違法情形的,可以直接向主持刑事和解的檢察機關及其上級部門舉報、控告,有關機關應當接受并視調查的具體情況,依法撤銷或維持刑事和解,對檢察人員在和解過程中存在徇私枉法行為,依法追究相應的紀律和刑事責任。
2.以易和解案由為重點開展輕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
重慶市檢察機關自2008年9月正式開展刑事和解工作以來,已有38個區縣檢察院開展了刑事和解辦理輕微刑事案件工作,工作鋪開率高達 95%。從各地開展情況來看(如圖 5),達成和解的案件主要集中在故意傷害案(221件245人),交通肇事案(181件181人),這兩類案件數占到和解案件總數的 83.40%。此外,還涉及故意毀壞財物、搶劫、盜竊、非法拘禁、詐騙、強奸、過失致人死亡和敲詐勒索等多個罪名。[13]

圖5 輕微刑事案件易和解的案由分布圖
從圖5中,我們可以發現輕微刑事案件中容易達成和解的案由主要集中在故意傷害罪和交通肇事罪兩個罪名上,這樣高比率的和解事由為今后檢察和解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檢察機關可以考慮從這兩個罪名的和解經驗入手進行總結,從而實驗性地推廣至其它領域。
3.不捕、不訴應當詳細說理、充分論證
為進一步化解矛盾、促進社會管理創新,對于作出不捕和不起訴決定的,人民檢察院應當積極推行詳細說理、充分論證的制度,如圖4所示,說理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犯罪情節、悔過程度、社會危害性等幾個方面。在《不起訴理由說明書》、《不逮捕理由說明書》等法律文書中嚴格執行不逮捕、不起訴說理制度,在向移送審查起訴的公安機關、自偵部門、案件被害人、被不起訴人及其所在單位送達不起訴書的同時,詳細地說明和論證不逮捕、不起訴的事實和法律依據。
案例4:劉某交通肇事案案發后,車主立即撥打了“110”報警并撥打“120”急救電話,隨后,劉某和車主在將傷者送往醫院搶救后返回現場等候處理。鑒于劉某案發后積極救助傷者,并有自首情節,在與被害人近親屬達成和解協議后,襄陽區人民檢察院對其作出了不起訴決定。[14]
案例4中,襄陽區人民檢察院在《不起訴理由說明書》、《不逮捕理由說明書》等法律文書中詳細地說明并論證了劉某的犯罪情節(造成的傷害)、悔過程度(救助、賠償和自首情節)、社會危害性(是否具有再犯的可能性)等幾個方面,將該案成功和解。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樣詳細地說理和論證不僅讓雙方當事人成功和解,更從另一個側面約束了辦案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使該項檢察權在陽光下實現公平和正義。
四、小結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但承襲了我國自古以來“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的治國思想,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煥發出長盛不衰的生命力,而且也契合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意味著我國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在寬嚴相濟這項刑事政策中,把“寬”放在前面,是為了突出這項政策的側重點在于“寬”,在于刑事訴訟領域的非犯罪化、輕刑化和非監禁化。但強調“寬”不是要放棄“嚴”,真正的司法和諧,必然是嚴要有度,寬要有節,寬嚴相濟。
[1]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J].Harvard Law Review,1897:457.
[2] 陳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國法學,2006(5):3-14.
[3] 向朝陽,馬靜華.刑事和解的價值構造及中國模式的構建[J].中國法學,2003(6):113-114.
[4] 張建偉.對抗與和合[C]//刑事訴訟法論文選萃.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489.
[5] 錢穆.文化學大義[M].臺北:中正書局,1981:3.
[6] 劉娟.昆明輕微刑事案件“在陽光下私了”[EB/OL].(2007-10-17).[2011-03-18].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 00710/17/269867.shtml.
[7] 王萌,李志方.三門峽湖濱兩年依法刑事和解68案102人[N].檢察日報,2010-04-27.
[8] 沈義,俞建軒.重慶去年對1005件輕微刑事案促成雙方和解[N].檢察日報,2011-02-10.
[9] [英]邊沁.立法理論——刑法典原理[M].北京: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66.
[10] 賴國東.交通肇事和解不捕應把握“四項基本原則”[EB/OL].(2010-02-01).[2011-03-08].http://gz.jxzfw.gov.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6174.
[11] 鄭仁敬.檢察機關審查逮捕階段適用刑事和解的思考[J].哲學與法學,2009(11):84-87.
[12] 孫文紅,宋興偉.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的程序問題研究[J].人民檢察,2008(3):26-28.
[13] 徐勤.輕微刑案超九成實現刑事和解[N].重慶商報,2009-12-29.
[14] 葉先國.以人為本,深入推進輕微刑事案件民事部分訴前和解[EB/OL].(2010-08-19).[2011-03-18].http://www.jcrb.com/jcpd/jczlt/201008/t20100819_404633.html.
D926.3
A
1674-8557(2011)03-0098-06
2011-08-20
林占發(1981-),男,福建龍巖人,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陳家標(1982-),男,廣東潮州人,廣東省東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陳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