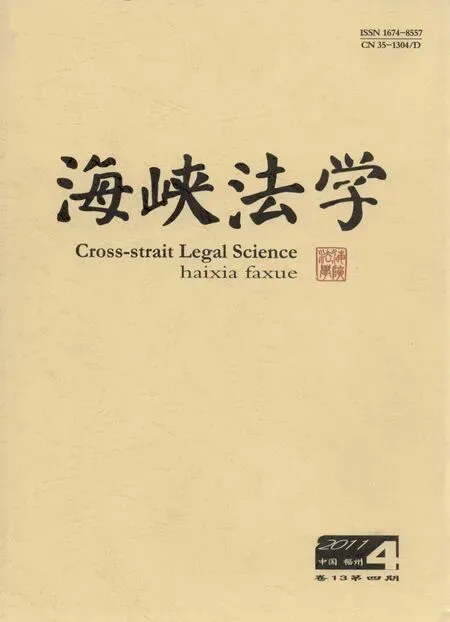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責任的類型化分析──基于對過限類型的精細化區分
薛進展 ,蔡正華
(1,2.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中國上海 200062)
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責任的類型化分析──基于對過限類型的精細化區分
薛進展1,蔡正華2
(1,2.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中國上海 200062)
在結果犯場合,共同犯罪中的個別人過限可以劃分為量的過限、質的過限、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以及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四種類型。其中質的過限和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都屬于傳統共同犯罪理論中的實行過限范疇,實行過限共犯自己承擔過限責任。量的過限則不屬于實行過限的范疇,適用共犯從屬性理論,由共犯人共同承擔責任。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則需要在區別犯罪行為是否存在量的過限的基礎上,再根據相關標準確定過限責任承擔。
共同犯罪;過限;責任承擔
一、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類型的重新區分
傳統的刑法理論將共同犯罪中的個別人過限區分為質的過限和量的過限。應該說,這種對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所進行的分類,是基于確認實行過限概念的需要。在此種二分法下,質的過限被認為是與共同犯罪中實行過限相等同的概念。個別人量的過限則被認為是與實行過限相區別的概念,是不適用過限人自擔其責的歸責原則的,應當根據共犯從屬性理論由共犯人共同承擔責任。①然而,共同犯罪中出現個別人過限是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的情況,此時準確確定過限責任的承擔就顯得極其重要。對個別人過限的傳統分類,著重關注的是實行過限等典型情況下共犯人責任的承擔。對于過限這一用語可能出現的實踐情形卻缺乏周到的考慮,導致了僅僅依靠實行過限理論難以解決出現的全部問題。實際上,從實行過限概念產生的過程出發就可以發現,不僅僅共同犯罪中的過限不止實行過限這一種情況,而且實行過限所適用的過限人自擔其責的歸責原則,也難以適用于所有的過限情況。
筆者認為,在共同犯罪框架下討論過限責任,理應認識到可能出現的所有過限情景,并對各種情景規定歸責原則,這是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基本原則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認為,從犯罪要素中的犯罪行為②和犯罪結果兩個內容出發,可以將共同犯罪中的個別人過限劃分為量的過限、質的過限、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以及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等四種類型。當然,拋開對犯罪結果過于寬泛的理解,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通說都認為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會存在犯罪結果,這就導致在危險犯等場合下,決定個別人過限類型區分的因素只有犯罪行為這一單一因素,此時的個別人過限也就只能劃分為質的過限和量的過限兩種類型。在這個層面看,本文對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所做“四分法”之區分,是僅僅就結果犯場合進行的討論。③
二、各過限類型的界定和責任的承擔
從現有研究來看,學術界對實行過限情況下過限責任的承擔研究較多,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缺乏對共同犯罪情況下個別人過限類型精細化區分的必要性的認識,所以對本文所涉及的其他三種類型的個別人過限情況下過限責任的承擔方式,目前尚未形成較為統一的意見。
(一)質的過限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所論述的質的過限屬于傳統理論中實行過限的范疇。而對于實行過限的概念,我國學術界雖然有著不同意見,但是基本的內涵趨向一致,即認為實行過限是指“實行犯實施了超過共同犯罪人事先預謀或臨時協議的范圍的犯罪行為。”[1]需要明確的是,此處“超過共同犯罪人事先預謀或臨時協議的范圍的犯罪行為”,是超過了共同故意所涉犯罪客觀方面的行為。比如,例一:甲和乙共同故意盜竊丙家中錢財,甲負責放風,乙負責竊取財物,后因發現丙在家,故乙以對人實施暴力的方式劫取財物逃離現場,甲乙二人平分犯罪所得財物。此處,共同故意所涉的犯罪為盜竊罪,其客觀方面為以秘密竊取的方式獲得財物,而乙卻實施了超過這一客觀方面的行為,實施了搶劫罪中所規定的實行行為。由此可見,質的過限中過限行為本身是另一罪的實行行為。這是確認實行過限的一個根本的標準。當然,實行過限共犯對于過限行為與其他共犯人肯定不能具有共同罪過,這是確認實行過限在主觀上的根本標準,也是區分實行過限和一體轉化的根本所在。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由于本文所討論的是結果犯場合下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問題,質的過限是包括犯罪行為質的過限和犯罪結果質的過限。因此,質的過限屬于實行過限的范疇,但二者并不能等同,質的過限的認定要求具備實行過限的要件,即實行行為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疇,成為另一罪犯罪構成下的實行行為。除此之外,質的過限本身還要求同時具備犯罪結果的過限。比如,例二:甲和乙預謀共同故意入室以木棍輕傷害丙,但丙住所毗鄰公安局,故二人商定由甲放風,乙入室實施傷害;但乙與丙宿仇,隱藏其殺人故意,入室后使用木棍猛擊丙頭部,致丙死亡。此時,二人共同故意所涉犯罪為故意傷害罪,乙不但在犯罪行為上超出了故意傷害實行行為的范疇,而且犯罪結果也超過了故意傷害的一般結果,此時就構成了質的過限。
另外,與上述犯罪行為質的過限較為容易判斷不同,犯罪結果質的過限則比較難以判斷。因此,必須正確界定結果質的過限的標準,這是本文對共犯個別人過限進行精細化區分的一個前提。對此,學者有不同意見,比如構成要件異質說認為,并非任何行為都可構成過限犯罪。只有與共犯行為存在構成要件的本質性區別的行為,才是過限犯的客觀外部表現行為[2]。而超出共同犯罪決意說認為,正犯的行為是否構成實行過限,應以其實施的行為有無超出共同犯罪的決意為準[3]。筆者認為,結果質的過限是指犯罪結果的出現超出了刑法分則規定的共同故意所涉個罪犯罪既遂的結果標準,并且成為侵犯相似法益的更重個罪犯罪既遂的結果標準。比如,雖然故意傷害中存在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和死亡的結果加重犯的規定。但是,如果在共同故意傷害的案件中,個別人的行為出現了致人重傷的結果,我們不認為是結果質的過限。因為重傷結果雖然超出了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的既遂標準,但是其仍然不能構成與故意傷害侵害相似法益的重罪名——故意殺人罪既遂的結果標準。同理,當出現致人死亡的結果時,則可以認定為結果的質的過限。
那么,對質的過限場合下,過限責任如何承擔呢?筆者認為,既然質的過限屬于傳統的實行過限的范疇,因此,實行過限理論中對過限責任的承擔原則就理當適用于質的過限場合。根據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觀點,實行過限場合下,過限責任承擔采取個人責任原則,[4]由實行過限共犯自己承擔,未實行者不承擔。[5]據此,例二中,甲承擔故意傷害的責任,而乙承擔故意殺人的責任。
(二)量的過限
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量的過限問題被理論界發現也是基于對實行過限相關理論研究的需要,特別是為了區分實行過限行為與相關概念的差異。在對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進行二分法的情況下,學界通說認為量的過限是實行行為量的過限,藉此與實行過限(實行行為質的過限)相區別。但是,在本文四分法的框架下,量的過限采取廣義概念,指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都不存在質的過限的情況下,并且二者中至少有一者具有量的過限的情景。具體講,此種場合下個別人過限又包括犯罪行為量的過限且犯罪結果不過限、犯罪行為不過限且犯罪結果量的過限以及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都具有量的過限等三種情景。
比如,例三:甲乙二人預謀共同故意盜竊丙家中一價值3000元彩電,商定甲放風,乙行竊;后當乙進入丙家后,發現丙家尚有玉佩一枚,遂盜為己有;后二人將彩電銷贓分款。此時,乙的犯罪行為超過了共同犯罪的故意范圍沒有疑議,如果玉佩是價值百萬的古董,則表示犯罪結果的犯罪數額也因古董玉佩的加入而超過了“數額較大”,進入數額特別巨大行列,此時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對于原有的共同故意都存在過限。但是,盜竊數額的大和小以及盜竊一物和盜竊數物都只存在量上的差別,過限行為和結果所涉及的犯罪仍為盜竊罪,未能實現質的過限,所以屬于量的過限。而如果玉佩是一僅值數元的工藝品,則表示犯罪結果的犯罪數額仍然屬于“數額較大”范疇,犯罪結果不存在過限,此時我們也認為其屬于量的過限類型的個別人過限。最后,假設玉佩仍然是價值連城的古董玉佩。但是,乙在行竊時并未發現玉佩放在電視機上,只是在將電視機搬走之后才發現玉佩的存在,最后將其銷贓。此時,根據前述的標準,犯罪行為并不存在過限問題,而表示犯罪結果的犯罪數額卻超過了“較大”標準,出現了量的過限,我們將這種犯罪行為不過限且犯罪結果過限的情況也認為是量的過限的一種具體形式。
對于量的過限場合下過限責任的承擔,筆者贊同傳統理論的觀點,即由于上述三種納入量的過限范疇內的具體情境下的個別人過限仍然符合共同犯罪的一般情形。比如前述例三中,乙竊取玉佩的行為仍然是在甲的放風行為幫助下完成的,并且甲對乙進入丙家行竊可能多拿的情況存在至少過失的罪過,因此仍然適用共同犯罪從屬性理論,實行部分行為共同責任的規則,過限責任由所有共犯人共同承擔責任。據此,例三中,甲乙二人盜竊的數額都以彩電和玉佩的價值之和計算。
(三)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
在結果犯的場合,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之間并非只存在必然的引起和被引起的一對一的因果關系,這就造成了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可能屬于不同犯罪構成情況的存在,這也是競合型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這一原理也決定了質的過限的犯罪行為不一定造成犯罪結果質的過限,還可能造成犯罪結果量的過限、甚至是犯罪結果不過限等情況。比如,例四:甲和乙預謀共同故意入室以木棍輕傷害丙,但丙住所毗鄰公安局,故二人商定由甲放風,乙入室實施傷害;而乙與丙宿仇,隱藏其殺人故意,入室后使用木棍猛擊丙頭部,致丙輕傷或者重傷。此時如果是致丙輕傷,就屬于犯罪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的不過限;如果是致丙重傷,就屬于犯罪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的量的過限。
筆者認為,此種場合下的個別人過限,也屬于共犯實行過限的范疇。正如前文所述,共犯實行過限是指實施了超過共同犯罪人事先預謀或臨時協議的范圍的犯罪行為。由此概念可知,共犯實行過限概念的界定,只關注行為是否存在質的過限,而不論結果的過限與否。這就為將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場合下的個別人過限納入共犯實行過限提供了可能。同時,共犯實行過限理論的產生主要就是了為了限縮共犯從屬性理論指導下的“部分行為共同責任”規則的適用。而在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的個別人過限場合下,過限共犯基于自有的罪過,實施了超過共同故意的行為。此時,其他共犯人對此質的過限行為并不存在罪過,缺乏非難可能性,因此該過限行為的刑事法律責任理應由過限共犯一己承擔。而且,根據主客觀一致原則,未實行質的過限犯罪行為的其他共犯本身只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觀上也具有該共同故意犯罪的實行、組織或者幫助行為;因此,他們理應只在共同故意所涉犯罪范圍內承擔責任。由此可見,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場合下個別人過限責任的歸責原則和共犯實行過限的責任承擔原則一致。
據此,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場合下個別人過限和前述犯罪行為及犯罪結果都為質的過限的情形一樣,都屬于共犯實行過限的范疇,例四中甲只承擔故意傷害的責任,而乙則需要承擔故意殺人未遂的責任。
(四)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
與行為質的過限且結果非質的過限場合下的個別人過限一樣,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場合下的個別人過限也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犯罪行為不過限且犯罪結果質的過限;另一種是犯罪行為量的過限且犯罪結果質的過限。比如,例五:甲和乙預謀共同故意入室以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的方式輕傷害丙,但丙住所毗鄰公安局,故二人商定由甲放風,乙入室實施傷害;但在乙以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方式輕傷丙后,丙由于疼痛難忍,遂坐到地上,此時地上正好有一豎立匕首,致丙死亡。由于乙采取的是共同故意下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的方式輕傷害丙,并造成了丙死亡的結果,因此屬于行為不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的情況。例六:甲和乙預謀共同故意入室以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的方式輕傷害丙,但丙住所毗鄰公安局,故二人商定由甲放風,乙入室實施傷害;但由于丙的反抗,乙難以實施切掉其小拇指第一關節之目的;故乙拿起手邊匕首刺向丙腹部非致命部位,丙疼痛難忍,遂坐到地上,此時地上正好有一豎立匕首,致丙死亡。此時,由于乙采取的是刺向丙腹部非致命部位的重傷害方式傷害丙,超過了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的輕傷害方式,并造成了丙死亡的結果,屬于行為量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的情況。
應當說,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場合下過限責任的承擔是最復雜的,也是本文之所以對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進行精細化區分的主要原因。將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進行質的過限和量的過限的二分法,在將實行過限概念確定后,認為除了實行過限,共同犯罪中的其他過限都適用共犯從屬性理論指導下的“部分行為全部責任”規則。但是,筆者認為,由于質和量概念本身的差異決定了犯罪行為的變化與犯罪結果的變化之間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可能性也隨之發生變化。比如,前述例五中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的輕傷害方式引起丙癱坐地上的可能性,就遠遠小于例六中用匕首刺向丙腹部非致命部位的重傷害方式引起丙癱坐地上的情況。同時,在教唆的場合下,還可能存在教唆犯對結果質的過限不存在罪過的情況。這都決定了對行為非質的過限且結果質的過限場合下過限責任的承擔方式必須區別對待。
筆者認為,此時過限責任的承擔方式,既要考慮各共犯人對結果質的過限的主觀罪過的有無,同時又要考慮在結果質的過限的情況下,犯罪行為是根本無過限,還是僅僅存在量的過限。一般來講,在行為不過限、結果質的過限的情況下,所有共同犯罪人承擔過限責任的方式是一致的,屬于共犯一體轉化的情景之一,即如果對結果有罪過則所有共犯人都承擔過限責任;而如果對結果無罪過則所有共犯人都不承擔責任。在行為量的過限、結果質的過限的情況下,過限共犯對過限結果承擔責任,而非過限共犯則要根據原行為與現行為對于導致結果質的過限的概率大小的差異來判定是否要承擔過限責任。概率差異特別明顯的,證明非過限共犯對于共同犯罪引起結果質的過限的認識不存在達到認定過失以上罪過的程度,理應不承擔過限責任;概率差別并非特別明顯的,證明非過限共犯對于共同犯罪引起結果質的過限的認識存在達到認定過失以上罪過的程度,則非過限共犯需要承擔過限責任。據此,前述例五中,甲乙都要對丙的死亡承擔責任;例六中,實行犯乙對丙的死亡承擔責任,而由于切掉小拇指第一關節導致人死亡的概率明顯小于用匕首刺向腹部非要害部位致人死亡的概率,所以甲對丙的死亡不具有過失以上罪過,故不承擔過限責任。這種區分責任承擔方式的重要性將在下述典型案例的分析中體現出來。
綜上,以四分法的方式,綜合考察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在量和質兩方面的過限情況,有利于我們清晰其中各種情景下影響罪責分配的細微差別。而這種明確的區分,將過限種類與過限責任承擔方式一一對應,便于司法實踐中對照操作。具體適用可參見下表1。

表1 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不同類型的認定及過限責任的承擔原則
三、典型案例適用
(一)案情
例七:甲為某國有公司負責人,為監督該公司財務支出情況,主管部門以返聘方式聘用退休女職工丁為該公司專職監事,主要工作就是對日常財務細目進行檢查。后甲為獨斷財權,故希望丁因故不能參加此次選聘。甲向其友乙表達此想法,乙與甲協商以用自行車撞擊方式輕傷害丁,致使其不能參加選聘。乙為此找丙幫忙,并指明犯罪方式,支付報酬若干。后丙在具體執行時發現丁每日上下班所經路途僅僅為一過街天橋,故無法用自行車實現傷害目的。但為了獲得報酬,丙遂使用所帶匕首刺向丁的屁股,丁由于疼痛難忍,在未拔出匕首的情況下,直接坐到地上,匕首斜插向大腿內側致股動脈破裂后致丁由于出血過度致死。
檢察機關指控甲乙丙犯故意傷害罪,辯護人認為丁死亡的結果只應由丙承擔。法院判決三人故意傷害罪成立,分別處13年有期徒刑。
(二)爭議問題和分析
根據刑法第234條規定,故意傷害罪中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相對應的情節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由此可見,法院的判決最終認為甲乙丙都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亦即甲乙也為丁的死亡負責。支持這一結論的理由是原有的對個別人過限的二分法。根據這一區分標準,由于此時丙的實行行為并未存在質的過限,所以不適用實行過限理論,而應當根據共犯從屬性理論,對于丁的死亡結果由所有共犯一體承擔。
本案中,甲乙丙三人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共同犯罪是明顯的,但是究竟由誰對丁的死亡負責確是值得研究的。根據本文前述有關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類型的區分來看,甲乙作為教唆犯、丙是實行犯,共同故意所涉個罪為故意傷害罪,丙在實行過程中,選擇了與共同故意中所預謀的用自行車輕傷方式不同的匕首刺屁股的傷害方式,由于用刀刺屁股一般并不會導致被害人死亡,所以仍然屬于傷害方式,不存在犯罪行為質的過限;但最終導致了丁的死亡,而如前文所述,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區別于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屬于犯罪結果質的過限,所以可以認為本案出現了犯罪結果質的過限。據此,該案中的實行過限屬于前述個別人過限中的第四種情形——行為的非質的過限、結果質的過限。但是基于本文精細化區分的規則,此種場合下過限責任的承擔仍然要考察犯罪行為是否存在量的過限這一因素,如果存在量的過限,則要進一步考察原行為與現行為對于導致結果質的過限的概率大小的差異來判定非過限共犯是否要承擔過限責任。
筆者認為,本案中,作為教唆犯甲乙明確指定的用自行車撞擊方式對被害人進行輕傷害的犯罪方式,其本身具有的傷害效能較小,致人重傷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實行犯丙在教唆犯所指定犯罪方式不可行的情況下,為獲得報酬,選擇的用匕首刺擊被害人屁股的犯罪方式,其本身具有的傷害性雖然在丙自己看來似乎可能致受害人輕傷,但是由于行為本身和人體構造的特殊性,該方式致人重傷甚至死亡的可能性較大,本案被害人最后的際遇也正說明了這一點。因為即便不是被害人自己由于疼痛難忍癱坐在地,導致匕首斜刺股動脈并最終致使出血過多死亡,過限共犯乙用匕首刺擊屁股的傷害方式本身就存在刺破股動脈的可能。而雖然這種可能性一般認為尚未達到形成故意犯罪中認識因素要求的程度,但由此仍可發現,用匕首刺擊屁股的犯罪方式較預計的用自行車輕傷害的犯罪方式之間存在明顯的量的過限,并且前者造成犯罪結果質的過限的概率也特別明顯的大于后者。這就說明,本案中甲乙二人在對于共同故意傷害犯罪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結果質的過限的認識,不存在達到認定其具有過失以上罪過的程度,因此不應當對被害人死亡這一質的過限的結果承擔責任,其宣告刑應當在故意傷害罪法定刑第一幅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確定。
四、后記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講,共同犯罪從屬性理論適用的范圍呈現出一種日漸縮小的趨勢,這與共同犯罪構成本身日益受到限制的趨勢是一致的。而這種趨勢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實現共同犯罪理論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之間的協調,真正實現罰當其罪。而這一目標的實現,無疑也對共同犯罪中諸如個別人過限等特殊問題的厘清提出了要求。我們應當看到,過限用語本體上就具有量的過限和質的過限兩種含義。現有刑法理論在共犯過限和實行過限中使用這一詞語,并不能阻礙我們將實踐中的個別人過限類型的劃分朝著更加科學與合理的方向發展。而實踐中傳統的二分法導致的罪責刑不相適應的情況,使得對個別人過限類型進行精細化區分顯得尤為必要了。
注釋:
① 刑法理論中存在實行過限和一體轉化二者區別的討論,為了論述的方便,加之本文所涉及“過限”概念屬于實行過限概念的上位概念,故本文所謂個別人過限,區別于傳統的共犯過限和實行過限概念中的“過限”概念,并不絕對排斥一體轉化的可能。這在文章后半部分的論述中也會有所體現。
②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基以區分共同犯罪中個別人過限類型的兩個因素中,犯罪行為理當是共同犯罪中的行為,至于是否由共同故意支配則不論;而犯罪結果則是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結果犯意義層面的結果。
③ 對于結果犯,我國刑法理論界主要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結果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結果的發生作為犯罪既遂標志的犯罪;而另一種觀點認為結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結果發生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根據通說,本文所涉及的結果犯概念是指第一種觀點下的結果犯。
[1] 趙秉志.中國刑法適用[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20 .
[2] 吳振興.犯罪形態研究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86.
[3] [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818-819.
[4] 葉良芳.實行過限之構成及其判定標準[J].法律科學,2008(1):88-94.
[5] 肖本山.共犯過限與共犯減少[J].政治與法律,2010(2):26-33.
D924.11
A
1674-8557(2011)04-0077-07
2011-11-09
薛進展(1956-),男,上海人,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教授;蔡正華(1985-),男,江蘇鹽城人,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
張 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