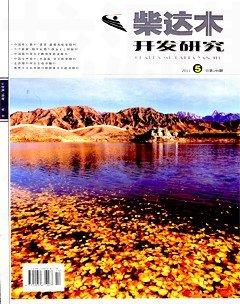學會反思是一種進步
竇孝鵬
“保護藏羚羊”、“愛護植被”、“建設生態家園”……這些都是近些年來頻頻出現于新聞媒體上的語句。每每看到這些,我心里都會有一種深深的愧疚。最近十幾年來,我和我的許多戰友一直在反思:半個世紀前,我們在青藏高原對國家的珍稀動物藏羚羊和稀少植被紅柳的野蠻舉動。
1958年底和1959年初,為了應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可能發動的武裝叛亂,我們幾個汽車團由內地移防昆侖山下的格爾木。當時,由于物質匱乏,不久又遭遇三年自然災害,部隊的生活供應受到很大影響。由于部隊新來乍到,養豬種菜都無從談起,肉食和蔬菜供應發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團和其他兄弟單位都不約而同的成立了幾十個人的打獵隊,帶上槍支彈藥和帳篷,坐上汽車駛進了昆侖山可可西里地區和唐古拉山區,為部隊獵取肉食,主要獵物就是藏羚羊(我們那時稱作黃羊)、野馬、野驢和野牦牛等。那些獵物被一車車拉回來,分給各個伙食單位,每次開飯時飯桌上都會有一大盤野牲肉,或紅燒,或涼拌,成為很受大家青睞的一道主菜。這種打獵隊一直存在了好多年,有多少藏羚羊等珍稀動物死在了槍下,誰也說不清。當時沒有人認為這有什么不對,而且被當作自力更生的一種手段。
在青藏高原的戰斗和生活中,我們還遇到另一個當時無法解決的困難——做飯、燒水、烤車等都缺乏燃料,于是,大家又不約而同地把眼光盯向了周圍戈壁灘上的紅柳樹。
紅柳,是戈壁灘上一種特有的植物,它露出地面上的枝干很細小,開著一種粉紅色的小花,但埋在沙堆里的根系卻很龐大,像一個個大墳包,有人稱為紅柳丘。紅柳丘的形成是紅柳與風沙斗爭的結果:那狂風一次次卷起流沙把紅柳埋掉,不甘示弱的紅柳一次次頂破沙丘露出地面,然后又被埋掉,它又頂出地面……這樣,它不僅起到了防風固沙的作用,而且根部越來越大。由于戈壁缺水,挖出來的紅柳根干硬干硬的,是十分耐燒的好柴火。有時,創開一個紅柳丘就可以裝滿半汽車。
開始,我們只在公路附近挖,慢慢的這里的“資源”枯竭了,便不斷向里邊延伸,挖完北邊的又挖東邊的。那時,每個伙食單位每隔兩三個月便要抽人組成打柴隊,進住戈壁灘,打一個星期,就可以用幾個月。你要是在營區走一遍,就可以看到每個伙房后面都堆放著小山一樣的紅柳根。同樣,當時沒有人認為這有什么不妥。這些柴火不但要供做飯燒水用,而且還要供執勤途中的烤車用。青藏高原的冬春十分寒冷,長途行車途中每天早晨發動車都要點幾堆火,分別放在發電機下、變速箱下和差速器下,烤化那些凝凍成塊的機油和黑油,車才能發動起來;還要用火燒熱兩桶水,加進汽車水箱。所以每臺車出發上路時,都要帶夠供半個多月用的柴火——紅柳根。
紅柳根就這樣一堆堆地變成了灰燼。失去紅柳的戈壁灘,開始向人們報復了——流沙一次次吞沒草原,漫上牧村和公路……
每每想到這些,我心里都會蹦出兩個字:罪過!
細想起來,獵打藏羚羊也好,挖紅柳根也好,不光因為我們那時候認識不到位,缺乏保護自然生態的意識,還因為那時新中國成立不到十年,把解決幾億人民的吃飯問題放在了重中之重,還顧不上全面抓環保生態的問題,缺乏這方面的宣傳教育,更沒有這方面的立法,所以才導致了這種“野蠻”行為的發生。
為了彌補過去的這些過失,幾十年來,我和我的戰友們都自覺地投入到了對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宣傳工作中。
這是青藏高原一個美麗的秋天,我和我的同團戰友王宗仁從北京出發又一次來到了格爾木。我們專門去拜訪了設在這里的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長和當地林業部門領導,向他們了解了保護藏羚羊和格爾木周區的綠化情況;又去格爾木西郊,參觀了那里的紅柳林和胡楊樹,看到郁郁蔥蔥的紅柳樹和挺拔的胡楊,心里感到了些許的慰藉。
接著,我們驅車上路,進了昆侖山到了可可西里,這里是藏羚羊的主要活動區。途中,在昆侖山口的一側,我們看到這里聳立著一座高20米的玉樹藏族自治州治多縣縣委副書記兼西部工委書記索南達杰烈士的紀念碑。他為保護藏羚羊,率領“牦牛隊”與偷獵分子英勇搏斗,于1994年1月犧牲在了這片土地上,被國家授予“環保衛士”稱號。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向這位藏族英雄獻了花,敬了酒和煙。
在可可西里不凍泉的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我們遇到了來自內地的三男一女4個青年志愿者在這里堅持保護藏羚羊的工作,我們與他們進行了詳細交談,對他們的熱情表示了極大的敬意,臨走,把我們車上帶的水果和飲料都留給了他們。在此前后,我們還寫文章對青藏高原的生態環保工作給予了大力宣傳和報道,其中,王宗仁寫的《藏羚羊跪拜》,引起了很大反響。
反思,是一種品質,一種境界,更是一種進步。人類在不斷發展的長河中,如我輩等一樣,曾干過不少蠢事,走過不少彎路。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經過反思和自省,我們從思想到行動,都會跨上一個新的臺階。
(作者單位:北京市豐臺區軍休辦21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