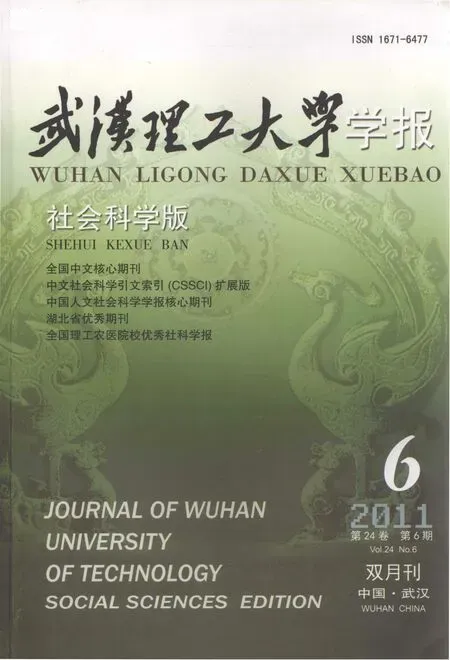重大災害事件群體創傷心理障礙與救助研究*
萬明國,夏東海
(1.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0;2.武漢市公安消防局防火處,湖北武漢430020)
非常規重大災害事件不僅給受害區域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還會帶來整個受災區域人們精神上的巨大傷害,通常會引發相當多數的人群出現一系列的應激心理障礙。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群體性的災害應激心理障礙可以說是重大災害的自然產物和必然后果。當遇到這種突然強烈的刺激,容易出現不同于個體創傷心理特征的群體性心理防御機制的破壞,導致群體性的心理支柱無法支撐如此大的壓力與哀傷,從而失去常態下的社會控制能力,造成群體性的心理失衡、心靈創傷等問題,極端的情況可能會出現社會秩序遭受破壞的現象。在突發重大災害事件,如地震、海嘯等發生之后,如何有效防止重大災害造成的群體心理障礙,實施有效及時的心理救助,成為災害應急管理與重建管理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本文重點探討重大災害情境下群體創傷心理障礙的形成機理與心理救助問題。
一、災害事件心理傷害的相關研究
通常,在一些災害發生初期,大多數作為個體的人會產生一些心理與行為反應,如恐懼、悲傷、焦慮等負面情緒,以及一些不良軀體癥狀,如疲倦、失眠、發抖、噩夢、心跳加快等。這些屬于不正常情境下的正常反應。在重大災難事件后,即刻發生的嚴重的心理障礙多為急性應激障礙。長期遭受心理創傷又沒有接受及時干預和治療,將可能導致人們的心理行為失衡,出現重度抑郁、焦慮癥,有自殺的想法或行為等。更重要的是,這種心理傷害不僅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甚至會波及與他相關的人,最終影響個人的社會關系和集體生活的正常社會功能的發揮。因此,災害心理明顯不同于人們的常態心理,主要反映在從心理反應傾向、反應節奏、情緒表露與傳染及其對心理行為的規范約束等方面,都可見到異于一般的變化。據研究表明,受害者創傷體驗所表現出的創傷反應各不相同。大災后兩個月,心理出現應激相關癥狀的人占18.6%;在災難之后一年內,大部分人都能夠慢慢恢復,但仍有一部分人恢復較慢,而有約5%的人將持續終身[1]。許多人經歷了創傷性和應激性事件后,會在接下來幾天或幾周內表現出一些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癥狀。有研究表明,8%的男性和20%的女性會持續發展PTSD,而大約有30%的這些個體會表現出持續整個后半生的慢性癥狀[2]。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災害事件發生之后,約20%~40%的受災人群會出現輕度的心理失調,30%~50%的人會出現中度至重度的心理失調,而在災害一年之內,20%的人可能出現嚴重的心理疾病[3]。
重大災害、災難研究在1980年代以前的美國,大多集中在救災組織、小區準備、災民的反應、社會調適與安置問題、災難危機管理等[4]。到了1980年代末期,災難研究轉向關注受災者與救災者個別或集體的災害創傷經驗,也就是創傷后壓力疾患的問題。既往的研究表明,災害作為一種集體性大規模的應激處境對心理健康會產生持久而明顯的影響。災害受難者應激障礙的主要表現是調適障礙、急性應激障礙、極度應激障礙和創傷后應激障礙[5],其中PTSD因其對人的心理危害性更大而尤其值得關注。應激研究最早始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醫學領域,其創始人是加拿大著名的生理學家Hans Selye。他認為,應激是指人或動物有機體對環境刺激的一種生物學反應現象,由加在機體上的許多不同需要而引起,并且是非特異的。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應激的傳統學說,即“一般適應綜合征”。它分為三個階段:警覺期、阻抗期和耗竭期[6]。
與通常的個體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相比,重大災害事件對財產與生命的損害往往是大面積的和非常嚴重的,明顯不同于一般性災害事件對個體心理的創傷,它的形成對相當范圍的人群的心理造成極其巨大的傷害。重大突發災害事件的群體心理行為,也屬于應激反應的范疇。由于重大突發災害具有發生突然,難以預料,危害大且影響廣泛等特點,其造成的嚴重后果是形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心理障礙應激反應,它給事件的親歷者們造成的心理反應非常強烈,神經系統遭受強烈刺激,導致集體生活的社會秩序與群體心理行為的混亂無序,高度的驚慌失措和無助感。因此,群體性創傷心理障礙不止限于個體的創傷后應激障礙,還會導致個體性的憂郁和創傷后應激障礙以外的癥狀,如:群體智力偏差、集體焦慮障礙、群體身心障礙等。這種持續的狀態(尤其是超過災難事件發生后一個月),可以稱為“重大創傷后群體心理障礙癥候群”。
二、重大災害事件群體創傷心理特征
國外有關研究表明,災害造成的重大創傷后群體心理障礙癥候群的重要表現特征之一就是它本身是一個包括多種不同程度的心理傷害所造成的應激障礙反應的復合體,因此,形成了多種臨床表現的癥狀。
(一)重大災害事件群體創傷心理應激障礙的類型
依據臨床表現可以將創傷后群體心理應激障礙區分為四種類型。見表1。

表1 創傷后群體心理應激障礙分類
國內吳華[7]等人對松花江洪水受災人群心理健康狀態分析發現,受災組焦慮癥狀檢出率達到63.93%,抑郁癥狀檢出率達到57.52%,明顯高于對照組(P<0.0I)。李潔、林杰[8]等采用SCL-90對遭受洪災的中專學生與一般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考察,發現受災學生抑郁與焦慮因子得分顯著高于一般學生。
(二)重大災害事件群體創傷心理過程的三階段模型
隨著研究的深入,社會-心理-生物現代醫學模式建立帶來醫學領域的觀念改變,應激概念的應用正在從心理學領域進入到預防、康復等醫學領域。近年來,應激的研究也已從疾病范疇擴大到健康范疇,并逐步擴展到創傷心理障礙的救助研究領域。現代應激理論認為,應激是個體面臨或覺察(認知、評價)到環境變化(應激源)對機體有威脅或挑戰時做出的適應和應對的過程。研究表明,應激的產生包括應激源、中介變量和心理生理應激反應三部分,從而使應激研究具有了整體性與明確性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將重大災害事件的群體心理應激反應過程理解為從疾病產生到心理恢復的三個不同階段,其心理影響也表現出相應不同的特征。
第一階段為警覺期,即受傷害群體對重大災害形成的創傷和災難的感知覺、情緒、認知等心理過程的壓力反應期。受傷害者甚至失去行動能力,事情過后往往對此不能回憶。此時,個體機體尚未產生適應性,這段時間里,生存是第一要務,人們聯合起來對抗災難,心理問題表現并不明顯。
第二階段為對抗期,一般是從災后幾天到幾周內。此階段機體動員了全身的防御機制,阻抗能力高于正常水平,是適應的最佳時期;出現重大創傷后群體心理障礙癥候群,急性應激心理反應成為群體心理傷害的常見疾病癥狀。在此時期,絕大多數災難幸存者、搜救者及照顧者都會經歷相當大的壓力,其影響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是情緒影響,如震驚、恐懼、悲傷、生氣、罪惡、羞恥、無力、無助、無望、麻木、空虛,以及喪失快樂及愛的能力;二是認知影響,如困惑,猶豫,無法集中注意,記憶力喪失,不想要的回憶,自責;三是身體影響,如疲倦,失眠,身體疼痛,身體緊張,心悸,惡心,食欲改變,性欲改變;四是行為影響,如無法信任,無法親密,失控,覺得被拒絕,被放棄,群體失范。嚴重者會出現避免接觸與高度警覺的心理癥狀。
第三階段是康復期。經過自身調整和(或)外界幫助,受傷害群體心理重新達到平衡狀態。大部分人在一段時間后可以自己恢復心理平衡和功能,也有部分人可能出現嚴重的心理障礙,需要有效的心理救助干預才能恢復。這一階段是群體心理傷害救助的關鍵時期。
重大突發災害的群體障礙心理過程的實際進展會呈現出波動的特征,它是人們對外部刺激的情感性反映,并涉及受傷害人群的多方面反應狀態,包括軀體反應、集體心理反應及社會行為反應等幾個不同的方面。在警覺期反應趨于上升,并達到頂峰狀態;對抗期出現反復,平靜平和與無助恐懼會交替出現;恢復期則趨于穩定。重大災害的群體心理障礙機制與心理救助,理論上講要依據群體創傷心理過程的不同階段特征而采取一定的差異性措施。
(三)群體創傷心理傷害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對重大自然災害造成的群體心理障礙研究顯示,有些人群容易出現創傷后壓力癥候群,如:曾有其它創傷,長期貧窮、失業、無家,群體性重大生活壓力等。重大突發災害會誘發出每個人之前存在記憶中的創傷經驗,更可能會強化容易受影響群體的心理、身體與行為反應方面的各種障礙問題。但是否出現群體創傷后心理障礙癥候群,取決于不同的影響因素。
第一,事件因素,也可以稱為應激源因素,是重大災害及后續災害事件本身的影響強度與持續性特征。應激源往往具有異常驚恐或災難性質,因而可能對患者導致深度的悲傷或憂傷,如重大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等,這類事件稱為應激源。
第二,群體因素。不同于個體受人格特征、教育程度、智力水平、信念和生活態度等形成個體易患性的影響特點,群體遭受重大災害會出現心理與行為反應的復雜性特征。這取決于群體社會心理認知與心理行為的獨特機理,以及群體結構的特征與演化規律。群體重大災害的社會心理動力學特征明顯不同于個體的災害心理行為影響因素。就個體而言,個體因素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生物免疫系統,通常會通過性格或人格的狀態發揮作用,不同性格的人抵抗力會存在差異。外向人格對各種社會精神刺激、焦慮和抑郁情緒有一定抵抗力,而內向人格則相反[9]。據研究,群體智力與群體平均及最高個體智力無關[10]。
第三,中介變量,如物質性幫助的可獲得性、社會文化背景等。此類中介變量因素影響著當事者對于應激源因素的解讀方式與參照對象。該因素影響了對精神性創傷經歷的反應強度,包括控制力、預見性和覺察威脅的程度。中介變量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社會支持系統,它提供著物質與精神層面的補償機制,是否能夠獲得及時的物質幫助,是災害受傷害人群能否重獲安全感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極大地決定著心理障礙形成的可能程度。社會支持系統構成重大災害后心理重建恢復的先決條件,包括生命線的恢復,安置點及過渡房等的建設和經濟支援等。群體因素與中介變量的交互作用可形成一定意義上的新的解釋變量,如安全感的獲得,新的人際社會關系等,對重大災害的群體心理癥候群會產生重大影響。群體因素與中介變量二者的交互作用可以形成災害事件條件下的群體認知系統,它嘗試提供對群體最小心理傷害的感受能力以及緩解現實的困惑。群體認知系統發揮作用機制的實際效果,將極大地決定著對災害應激源因素的危害程度。
重大災害事件是出現群體創傷后心理傷害癥候群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大多數人在經歷重大災害事件后都會出現程度不等的癥狀。以上相關影響因素對于受害人群的實際影響程度以及心理救助干預的效果都存在關聯性,關聯性的大小與作用方向會因影響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并由此構成復雜的網絡結構關系。重大災害群體創傷心理癥候群的急性應激心理過程、影響因素、心理障礙形成途徑與作用機理及其心理救助的網絡結構關系,見圖1。

圖1 重大災害群體創傷心理過程模型與作用機制示意圖
三、重大災害事件群體創傷心理救助的關鍵問題
重大災害事件群體創傷心理救助是指由政府或其它社會力量組織以心理專家、醫學專家為骨干的專業心理救助隊伍,針對受災區域群體障礙心理癥候群癥狀,運用心理學、醫學等相關知識,對存在心理危機的群體進行心理疏導和干預,緩解因災難帶來的心理壓力,并對心理受到嚴重創傷者進行心理救助工作的總稱。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曾對張北地震心理危機干預所做的調查顯示[11],震后9個月創傷后應激心理障礙的發病率為24.4%,受災程度重,但災后得到救援和支持的發病率可以顯著下降。重大突發災害事件發生后的心理重建要求建立長效的心理危機干預機制,對高危人群進行密切跟蹤,同時普及心理干預知識,鞏固和加強受災區域的經濟與社會領域的重建效果。群體障礙心理救助的實施過程要處理好三個關鍵問題。
(一)明確政府責任,正確識別目標群體
政府要在重大突發災害事件重建過程中通過受災區域的廣大群眾進行及時有效的良性互動,疏導與穩定社會公眾在危機狀態中的不正常心理,奠定災后心理重建的良好基礎。特別要區分災后心理重建的目標人群,明確群體救助的對象與任務。災后群體心理救助按照心理損傷嚴重程度從高到低排列,可分為五類:一是災難親歷的幸存者,如傷員、幸存者和居喪者;二是災難現場的目擊者,如災民、現場指揮、救護人員;三是與前兩種人群有密切關系的人,如幸存者和目擊者的親人等;四是災難發生后在災區和后方開展救援服務的人員,特別是負有一定責任的人員;五是媒體新聞覆蓋的人群。研究表明,可以針對幸存者、遇難者家屬、救援人員和一般公眾四個不同群體,進行有區別的心理援助效果會更好[12]。
面向群體層面的心理重建工作是實施重大災害群體心理救助的直接目的。歸納四川汶川地震災害的群體心理重建經驗可以發現,有效的群體障礙心理救助取決于一系列有效的社會行動過程。第一是在第一時間,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重災區,指揮救援工作。他們所展示的關注,堅定的態度和必勝的信心,通過媒體傳遞到中國每個角落,對災民和全國人們是巨大的心理安定劑,讓人民在災難面前,鼓起信心,戰勝因地震而產生的強烈無助感。第二是媒體全天候關注災區救援進展,隨時通告信息,讓人們有定期、固定途徑,及時了解權威信息,從而增加對災難的可控制感,恢復心理平衡。第三是迅速組織多種渠道,給民眾創造方便快捷的多種愛心表達方式。這些方式包括捐款、捐物、獻血、志愿者培訓、哀悼儀式等。處在災難帶來的巨大痛苦中的人,能夠參與到有效的行動中來,幫助災區人民,會讓行動者體驗到成就感、自信心,驅除掉無助無望的心情。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設立全國哀悼日,除表達對死難者的哀思外,主要是讓民眾有充分的理由宣泄壓抑的情感,從而降低抑郁情緒。第四是盡快恢復災區民眾的正常生活。媒體對災區重建的報道,對未來生活規劃進度的介紹,讓災民及早“安居”,幫助群眾重建生活信心和希望,較快擺脫心理陰影,恢復良好心理狀態,回歸到正常生活中來。
(二)確定適當的群體心理障礙救助方式
以汶川地震后群體創傷心理救助為例,災區心理志愿者隊伍一度無序擴張,國內各高校、心理咨詢機構、志愿者蜂擁而至,各種心理調查問卷也使災民對心理干預有所疑慮。由于部分心理咨詢機構只是發放了調查問卷,對調查結果并未處置,導致當地受災居民對心理咨詢不信任,對進一步開展心理干預工作帶來阻力。我國地震災后群體心理救助干預早在對唐山大地震進行總結和反思的研究中,就有學者呼吁對地震后人們的心理受損狀況建立評估體系和指標,并且呼吁進行災后心理救助的研究,如用溝通技術對群體應激反應進行緊急救助[13]。群體心理障礙救助的目的是預防疾病,緩解癥狀,減少共病,阻止遷延,重點是預防疾病和緩解癥狀。主要措施包括:
1.心理疏泄。干預方式包括各種形式的情緒處理,鼓勵回憶或情緒反應正常化等。有研究表明,單次會談的疏泄既不能減輕心理痛苦也不能預防PTSD發生,即一次性疏泄不能降低焦慮或抑郁、心理障礙的患病率。
2.嚴重事件集體減壓(CISD)。在重大突發災難中,對于幸存者、災害救援人員、急性應激障礙的病人,可以按不同的人群分組進行CISD。CISD是一種心理服務的方式,并不是正式的心理治療,面對的大部分是正常人。實踐表明,CISD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心理干預方式[14]。
3.藥物治療。PTSD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是選擇藥物治療。理想的藥物治療是能夠針對特定的生理心理系統狀態來選擇特殊類別的抗抑郁劑和抗焦慮劑。實際使用中應以抑郁、焦慮量表作為臨床檢測。
4.認知重建法。認知重建法是一種可靠的治療方法,特別對于PTSD的特殊人群具有很好的療效,其焦點是注重對病人的思維、推理和信念以及在認知中包含的態度等進行矯正。盡管各種認知重建法都關心病人的認知,不同的認知治療學派在治療技術上各有差異,如,Ellis的合理情緒療法認為病人的情緒障礙和不適應行為是由于存在不合理信念造成的,所以在治療時通過與不合理信念辯論來重建信念系統,以改變癥狀[15]。
群體心理救助的方式在實踐中可以多種多樣,但無論何種心理救助方式,都需要遵守一些共性的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是團隊合作,需要尊重配合指揮系統,并且融入基本物質救助系統去幫助幸存者及工作人員。第二,做最務實的接觸及溝通。先聆聽而后給建議,要詢問目前狀況,協助提供必要環境條件,如食物、飲料、衣物、防曬物品、雜志報紙、通信工具等。第三,問一些普通的問題。如:你目前需要什么樣的安置環境?我可以幫你和什么人聯絡嗎?等等。第四,評估危險因素,仔細評估其危險因素及癥狀,給與適當幫助。
(三)合理規劃群體心理救助的綜合性解決方案和實施途徑
群體心理救助的綜合性解決方案與實施途徑是指具體心理救助方式的實現路徑與作用平臺。最為重要的實施途徑是獲得物質幫助的狀況,通過物質幫助可以有效緩解受傷害群體的最初恐懼感,它是心理重建的基本前提。其次是一般安全感的回歸。通過社會支持系統的作用,使災害中受傷害的群體重新獲得普遍的社會支持,正確認知災害造成的財產生命危害與心理傷害,增強心理抵抗力。再次,針對群體癥候群癥狀反應實施直接心理救助措施,以獲得心理的平復與校正。據調查,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工作雖然逐漸進入尾聲,但開展最早的災民心理重建工作的普及率僅10%,專家估計還需要10年時間完成災民的心理重建工作。汶川大地震使4%的災民出現了心理障礙,而選擇主動就醫的為數不多,還不到10%[16]。因此,就汶川地震災區群體心理重建而言,需要著重考慮建立災區心理衛生長效機制,組建一支基層心理衛生工作隊伍,承擔培訓地震災區鄉鎮、社區衛生醫務人員基本精神衛生技能,為災區群眾建立連續、完整的心理健康檔案,形成動態的數據資源庫,推動災民心理重建工程有序發展。
四、結 語
重大災害事件的群體創傷心理不同于個體創傷的心理影響,群體重大災害事件的創傷心理呈現出復合型的群體性傷害特征。重大災害群體創傷心理反應劃分為三個階段:警覺期,即受傷害群體對創傷和災難的感知覺、情緒、認知等心理過程的壓力反應階段;對抗期,即出現重大創傷后群體心理癥候群的急性應激心理反應階段;康復期,即群體創傷心理重新達到平衡狀態的階段。
首先,基于重大災害群體心理癥候群的心理過程、影響因素分析,重大災害群體創傷心理癥候群的形成受不同因素的影響,其社會支持系統、群體認知系統與生物免疫系統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群體心理障礙形成的內部網絡結構關系。其次,重大災害群體心理救助需要在一定的社會支持的基礎上,提升災區群體的安全感,恢復受災群體的心理平衡和功能。建立和健全災區群體安全感成為群體障礙心理援助的中心環節。“5·12”大地震后,國務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中明確規定,地震災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做好受災群眾的心理援助工作。這是災后心理援助在我國首次被納入制度化軌道。回顧汶川、玉樹地震災害重建中出現的群體心理傷害現象及其救助實踐,使受災群體最大程度上獲得安全感是十分有效的心理救助及災區社會秩序重建的堅實基礎。再次,從政府危機管理的角度出發,政府實施群體心理救助要體現出分階段、分層次、有選擇的災害心理救助的實施策略,提升群體心理救助能力。按照群體障礙心理過程內部結構關系與作用機制,圍繞受災區域群體幸福感形成的需要,進行具體的群體心理救助。
制定災后心理援助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負責心理援助的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范圍,建立災后心理援助常備組織,只是做好心理援助的必要條件,災區群體心理安全感的獲得才是關鍵目標,它取決于專業人員保障(應包括心理傷害評估、識別與心理干預評價等)、組織協調保障以及長期的綜合性社會保障措施等多方面的滿足程度。這也意味著,非常規重大災害的群體心理救助需要突出發揮政府社會管理的職能,運用社會保障等國家公共政策工具,針對災難中各個群體的心理傷害進行全過程干預,始終將加強社會保障等政策措施納入到心理救助的制度保障體系之中,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中實現強有力的干預作用,成為災區心理救助的安全保障,使災區群體在心理重建中快速獲得安全感,恢復社會秩序。
[1] 周介銘.關注災后心理創傷[DB/OL].(2009-05-11)[2011-05-05]http:∥www.ccyl.org.cn/zhuanti/zyzzxd/xlmm/200905/t20090511_238372.htm.
[2] 李雪英.PTSD的認知理論及認知行為治療[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9(2):35-40.
[3] 鐘玉蓮.地震后的心理應激與危機干預[J].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8(4):34-37.
[4] Pamela Winston etl.Federalism after Hurricane Katrina:How Can Social Programs Respond to a Major Disaster?In Assessing the New Federalism.Washington DC.:The Urban Institute,2006.
[5] 王玉玲,姜麗萍.災害事件對人群的心理行為影響及其干預研究進展[J].護理研究,2007(21):86-93.
[6] Hans Selye.The Stress of Life[M].New York:McGraw-Hill,1956:56-65.
[7] 吳 華,朱志珍.松花江洪水受災人群心理健康教育對策研究[J].中國健康教育,2001(7):422-423.
[8] 李 潔,林 杰.特大洪災對受災醫專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J].中國學校衛生,2003(5):456-457.
[9] 張 本.經歷大地震的開灤礦離退休干部心身健康狀況調查[J].健康心理學雜志,1999(7):51-54.
[10] Anita Williams Woolley,Christopher F.Chabris,Alex Pentland,Nada Hashmi,Thomas W.Malone.Evidence for a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Fac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Human Groups[J].Science,2010(6004):686.
[11] 劉效仁.災區心理干預需要制度和財力支持[DB/OL].(2009-05-11)[2011-05-20]http:∥www.ccyl.org.cn/zhuanti/zyzzxd/xlmm/200905/t20090 511_238372.htm.
[12] 張黎攀,錢銘恰.美國重大災難及危機的國家心理衛生服務系統[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4(18):394-398.
[13] 龔瑞昆,王紹玉,顧建華,張世奇.災時應急心理救助技術與方法——溝通技術[J].城市與減災,2003(5):15-17.
[14] 鄧明昱,李建明.危機事件集體減壓(CISD)[J].國際中華應用心理學雜志,2008(5):36-37.
[15] Albert Ellis.Overcoming Resistance:Rational-E-motive Therapy With Difficult Clients[M].NY:Springer Publishing,1985:132-145.
[16] 5·12汶川地震災區民眾心理重建還需10年[DB/OL].(2010-05-06)[2011-05-05]http:∥www.jianzai.gov.cn/aticles/4028815d286771ef01 286af5fbff00a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