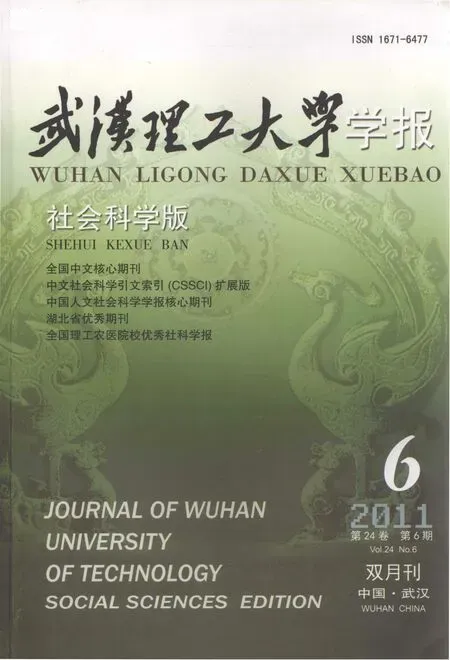藝術的核式結構論綱
姚紅玉,劉粵鉗
(1.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北京100875;2.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廣東廣州510630)
本文談論的藝術,在哲學史上始終是哲學家們不大愿意面對,卻又不得不努力將其納入自身理論體系的一個無法繞過的對象,而這份努力卻往往不盡如人意。從結構主義的角度究其原因,是因為以往對藝術的拓撲結構認識偏于線性化、平面化,從而無法解釋藝術現象的復雜性:在許多層面上,它都呈現出理性與感性、自律與他律、同一與相異等對立面的爭執、僵持與和解。
自然科學研究中,也不乏類似的對象,最著名的例子是照亮人類文明的光。
經典力學的研究對象被明確分為波和粒子兩類。惠更斯從宏觀世界出發,認為光是前者;而牛頓從微觀世界出發,認為光是后者;隨后是兩種學說長達數百年的爭論,直至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理論、德布羅意假說及薛定諤方程奠基的量子力學誕生。
在量子力學中,波粒二象性是指物質同時具備波和粒子的特性,換言之,用海森堡的話說,它使得同一種實體既以物質的形式出現,又以力的形式出現。盡管如此,如何正確理解波粒二象性依然是科學史上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之一,至今仍未完全獲致解決。
在筆者看來,波粒二象性從拓撲學的角度看,是由物質世界的普遍核式結構決定的;從哲學的高度看,反映的是整體與部分、連續與間斷的辯證統一。筆者認為,藝術也具有類似于物質世界的普遍核式結構,而且用該結構模型可以較好地闡明藝術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下文將對此作簡要論述。
一、藝術之核:Essentia Ethica①
對于物質世界普遍存在的核式結構,大至天體,小至原子,其質量的絕大部分集中于核心,以此論之,藝術的質量亦取決于它的核。
什么是藝術的核呢?筆者認為,是面向思的Essentia Ethica,在某些方面,它從拉康的Grand Autre(大他者)出發,經由薩特的être-pour-autrui(為他的存在),最后接近但不等同于列維納斯作為第一哲學的倫理本體——Autrui(絕對他者)②。
下面談談何謂Essentia Ethica。
首先,Essentia Ethica是面向思的,或者說是精神的。這就是說,它將“比物體更容易認識”③,而且人類的物質生活絕不會自然而然地就成為它的因,正如原子核外的電子云團的運動不會對原子核的構成和變化有什么決定性作用一樣。
其次,Essentia Ethica是類第一哲學的,或者說是類本體的。這就是說,它具有本體的許多特性,譬如客觀性、普遍性、抽象性和規范性,可又不像本體那樣只關注自身的存在,因其存在是足以自我論證卻永遠無法以有限語句確切言明的,正如原子核內的結構一樣。
再次,Essentia Ethica是內向倫理的,或者說其作用的指向是自身。這就是說,它首先是“為我(pour-MOI)”的,然后才是“為他(pour-AUTRUI)”的,最后才是“為你(pour-TOI)”的④。這個看法與列維納斯有聯系亦有根本的區別。
最后,Essentia Ethica并非靜止不變的,或者說是絕對運動的。這就是說,它對外呈現的穩態是相對的,在內部量變積聚到一定程度時,在外因的激勵下,它的內容會發生類似核裂變或核聚變的質的變化,反映到人類社會運動上往往會伴隨著社會形態的更替。
為了便于理解,接下來說說Essentia Ethica的由來。
西方哲學的淵源上,藝術從來都與倫理相關,但其關聯的方式各異。
亞里士多德傾向于把藝術看作是倫理的經驗物。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在深入思考了以“至善”(即幸福)為最終目的屬于任何存在物的既非“生產”亦非純思辨的“活動”之后,把他的倫理學與人的實踐聯系起來,并且進一步認為倫理學是討論最高科學——政治學最自然的出發點[1]。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強調藝術不同于認知真理的邏輯論證,其本性不過是“摹仿”人的活動,是創作者運用自身的美感天性在實踐中不帶實用或功利的目的去再現生活,并由此表述了真理[2]。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把“善”的個體性和群體性區別開來,從而在倫理學與政治學之間既劃清了邊界,又明確了兩者間最重要的聯系就是城邦的公民教育,而藝術是對公民進行倫理灌輸的最適宜的方式[3]。
斯賓諾莎則認為,無知是惡之根,藝術的倫理性在于它必須符合“上帝”(即作為物質與精神統一體的自然界,斯賓諾莎偷換并改造了該宗教語詞的所指)的意志(即自然的規律),所以他說:“人的身體的結構本身,就藝術性而言,實遠超過人類的技巧所能創造的任何東西,姑且不提我所已經證明過的,無限多的事物,無論我們從哪一屬性去觀察,都是出于自然的”[4]。
休謨把他的倫理學建筑在功利主義之上,認為人類的自由意志決定論地決定了道德不可能來源于辨別真偽的知性,而是體驗刺激的知覺的對象,“痛苦和快樂既是惡和德的原始原因,也就必然是它們一切結果的原因”[5]。藝術家在運用大量推理、論證和反思后所創作的帶上了人類智性的藝術品,展現的依然是以滿足人類情感需求為目的的道德的美。
與休謨相反,康德把倫理學分為:經驗的實踐人類學和理性的道德學,并把后者提升到形而上的地位,認為自在、自為、自律的善意志是“最高的善”,是“一切其余東西的條件,甚至是對幸福要求的條件”[6]。因此,在他看來,藝術的倫理在于將優美升華為崇高,將至善的定言命令式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嵌入藝術品。
康德哲學的五位后繼者: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叔本華和尼采,分別用既包含自身又包含自身之否定(即“非我”)的“絕對自我”作為精神與自然同一體的“絕對”的啟示,獨立存在且化身無限的自由意志,出于同情的“動機”以及作為“已死”“上帝”填充物的“權力意志”各自建立起了不同的倫理學,對藝術與倫理的關系自然也看法各異,但都沒有脫離康德哲學企圖以先驗存在物調和經驗與理性矛盾的大框架。
筆者認為,這與20世紀以前科學相對緩慢的發展有著直接的聯系:在科學革命的撞擊不足以動搖乃至終結哲學與神學時,對倫理與藝術的觀察和詮釋理所當然地會呈現出一定的局限性和連續性。
20世紀伊始,現象學誕生。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直接教導下,法籍立陶宛裔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受現象學與猶太教啟蒙,在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把倫理學作為第一哲學,并將其建構在將對象性解構后呈現出來的超越了理性的自我意識之上。筆者認為,列維納斯較徹底地反思和批判了數千年來西方哲學的主題——存在本體論,在這條道路上,他比乃師——回歸到亞里士多德的海德格爾走得更遠。因此,Autrui及其經驗化身Autre是重要的。
由于本文在某些根本觀點上揚棄了Autrui,對列維納斯的思想進行簡要的分析有助于進一步理解Essentia Ethica。
對于Autrui,列維納斯有兩個根本觀點:一是關于空間,他認為在異域中隱身著Autrui⑤,“我”認識“你”乃至認識世界不能無視它的作用,主、客二分法因而顯得不準確;二是關于時間,他認為時間⑥與Autrui密不可分,在某種程度上是同一個東西——二者都具有同樣的不可經驗性和無始無終的永恒性。這樣一來,Autrui與主體之間在一系列連綿的時間斷片⑦上彰顯的倫理關系就必然上升為第一哲學。這種說法雖然帶有現象學色彩,但顯然有別于胡塞爾將時間納入主體范疇,也有別于海德格爾將時間域與存在場等同的看法,表現了列維納斯為將猶太教義融入西方歐陸哲學體系的同時對雙方的繼承與反叛。
筆者認為,藝術雖然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一種相對獨立于歷史的、黑格爾式的意識形態,但卻不能無視這種獨立性本質上來源于無意識⑧,唯此,我們才能通過藝術的理性揭示藝術品具有恒久價值的原因。這樣,海德格爾時間式的Dasein,拉康拓撲式的Grand Autre,薩特主奴沖突式的être-pour-autrui就經由這無意識的通道到達了列維納斯時空一體化的Autrui,并就此衍生出了本文的Essentia Ethica。
必須指出,與列維納斯認為整體性意味著Autre之死是一個歷史的終結點不同⑨,死亡不屬于Essentia Ethica,因為Essentia Ethica本身就是歷史的Trieb⑩。因此,在Essentia Ethica中如同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等先哲那樣談論倫理的責任已經沒有必要。
二、藝術之核外云團:Vita Activa?
如同原子的質量主要地取決于穩固的核,電子繞原子進行著帶有自旋的公轉,概率論地呈現為核外云團。如果沒有核外的電子云團,那么眾多的原子也就沒法結合生成世界萬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藝術的外化運動比擬為Essentia Ethica的核外云團,它在核處于穩態時提供了藝術能量的表達。
這一核外云團到底是什么?抑或,應該是什么呢?對前一個問題,不同的藝術本體論會給出不同的回答;對第二個問題,在藝術的核式體系之下,藝術的核外云團應該也必須是Vita Activa。
首先,Vita Activa是面向行的,即面向人的活動的。阿倫特用自己最具特色的三分法將vita activa解剖為僅用于維持生存和繁衍的勞動(labor),有意識地應用智力和知識去改善生存與勞動方式的工作(work),以及不可預知亦不可逆——可用許諾和寬恕去部分地抵消這兩種影響——的行動(action)。筆者所引入的Vita Activa亦由此三者組成,但并不認為如阿倫特所言,這三種生活方式間的關系是一種排列順序固定的簡單鏈式結構,而應是一種零同倫的無限循環群的立體結構。事實上,這樣的理解恰是對核式拓撲結構唯一正確的群論解讀。
其次,Vita Activa是擁有無限維度的無限時空中一個屬人的、一般是連續統的有限區域,而藝術正是該區域在某維度真子集上的投影,直觀地看,也就是凝固了的、人的面向行的生活片斷。歷史借助藝術來凝固受到Essentia Ethica吸引和約束的Vita Activa以便被知識化,而這一過程就是藝術借助藝術品物質實例化的過程。
再次,Vita Activa以生活價值為根基,以對生活價值的反動為最終目的,換言之,以功利性為此岸,以Essentia Ethica為彼岸。當人類沉醉于此岸的狂歡而忘卻彼岸的存在時,藝術將成為預示Vita Activa解體和Essentia Ethica重構的第一聲驚雷。這一過程,筆者把它理解為愛因斯坦質能方程在藝術域必然存在的改寫形式,而這一改寫形式很好地揭示了藝術與生俱來的政治性。
最后,Vita Activa是絕對運動的,這種運動是它圍繞Essentia Ethica的公轉與自身內部粒子自轉的統一。Vita Activa的絕對運動性來源于Essentia Ethica的絕對無意識,因此它的絕對運動不僅決定了它的多樣化的實體性,也決定了它的多樣化的矛盾性。這樣,以往對藝術本體無休止的爭論就被它的自然核式體系終結了。
三、結 語
哲學史與科學史比較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哲學在為科學提供方法論指導的同時,自身的發展和完善必然也會受益于科學的新發現。因此,在哲學研究中完全可以借鑒科學研究的思路,正如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和維特根斯坦所做的那樣。
20世紀以來,科學的迅猛發展雖然沒有終結哲學,但哲學卻再也不能無視科學的進步;對于藝術而言,則更是如此。在現代性的沖擊下,藝術之核Essentia Ethica正悄然醞釀著一場劇變,正如杜尚的現成品替代塞尚的色彩和造型成為當代藝術的主流所預示的那樣。
是故,本文從拓撲學的視角出發,提出了藝術的核式結構,希望這一模型能更好地揭示藝術的本質。
最后,本文從倫理出發建構藝術的結構,不便言出的另一個考慮是基于本國的歷史現實:眾所周知,儒教在我國思想史上的統治延綿2000余年,至今基本沒有斷續?,因為“儒教同佛教一樣,僅僅是倫理。但是,與佛教截然不同的是,儒教僅僅是人間的俗人倫理”[7]。
注釋:
① 筆者引入的拉丁語詞匯,大致意思為“倫理本體”,但考慮到本文觀點并非形而上,則此譯又不盡然。
② 需指出,常有人將“他者”僅視作“autre”,并由此出發認為“他者”等同于帶有泛指意味的“他人”,故列維納斯倫理學的核心就是“對他人負責”。筆者認為此說法似有偏頗:一者大寫首字母后,Autre也可能是“我”自身(moi-même);二者列維納斯說到“責任”對本體論的消解時原話是:“Commandement dans la nuditéet la misère de l'autre,qui ordonneàla responsabilitépour l'autre:au-delàde l'ontologie.”(LEVINAS,第III頁)句中responsabilité后接pour而非de;三者列維納斯曾言:“L'absolument Autre,c'est Autrui.”(LEVINAS,第28頁),可見,Autrui為其倫理學最終的本原,即身披“邏各斯”長袍,無形無體無相,無所不知、無處不在且永恒存在的獨一無二的造物主——猶太教“上帝”(筆者認為,他就是“Il y a”中的Il,唯此方能將Autrui倫理學上升為第一哲學)。為免混淆,本文對兩者均使用原文,不作翻譯。另因列維納斯著作的漢譯本極少,本文所述有關他的思想及原話大都來自其著作的法文原版。
③ 參見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商務印書館1986版第22頁。雖然一般認為,笛卡爾是二元論者,但單就這句話而言,筆者并不認為和唯物論有什么本質沖突。
④ 這里的MOI,AUTRUI,TOI全詞字母大寫,用于借喻我、他、你,表示在筆者理論中的三個普遍存在,分別對應著先驗、超驗和經驗領域里企圖實現徹底主體化卻始終無法做到的一般對象。
⑤ 不少學者認為在此意義上,Autrui即主體間性,筆者認為這種說法社會學色彩過于濃厚,似乎不太符合列維納斯作為現象學者的出身與一貫強調規范的獨立實體性的本意。
⑥ 在很多時候,列維納斯又把死亡(mort)與時間(temps)劃了等號,認為autre的死亡可以引導我們認識Autre的死亡,進而認識到死亡是時間和Autrui之共通性的表現,換句話說,Autrui借助于死亡與時間的必然聯系為“我”所體會到。
⑦ 按筆者的理解,借用數學的說法,應該是某時刻任意小的鄰域——不見得必然是線性的。
⑧ 與拉康不同,筆者更愿意把這種無意識理解為脫離了時空限制的、無法“邏各斯”化的最終理性,而意識形態的稱呼太偏重于對這種最終理性在社會進化中表象的把握,是不夠準確的,因而也是容易引起混淆的。
⑨ 原文:“Dans la totalitéde l'historiographe,la mort de l'Autre est une fin,le point par oùl'être séparése jette dans la totalitéet où,par conséquent,le mourir peut être dépasséet passé,le pointàpartir duquel l'être séparécontinue par l'héritage que son existence amassait.”(參見LEVINAS,Totalitéet Infini:Essai sur l'extériorité.Le LIVRE de POCHE,Martinus Nijhoff.1961,第49頁)
⑩ 本文取洪堡特所用該德文詞義,即世界萬物的本原動因,而非弗洛伊德常用來表示心理沖動的引申義。
? 該概念來源于美籍德裔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所著The Human Condition(該書第一版于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問世。國內現有兩種漢譯本:一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竺乾威等譯本,書名譯為《人的條件》;二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12月出版的王寅麗譯本,書名譯為《人的境況》。筆者認為,從全書內容看,闡述視角主要地基于人類史的歸納,而漢語“條件”一詞按《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第1 352頁的首釋義:“影響事物發生、存在或發展的因素”,側重于演繹,因此后譯較妥帖。不過,漢語的“人”沒有單復數之分,而阿倫特向以關注“復數的人”——men,not Man——及認為她的condition“不僅是必要的條件,而且是使其成為必要條件的條件”——not only the conditio sine qua non,but the conditio per quam——自詡,此處的condition更接近于人類群體生活的狀況,故譯作《人類狀況》對普通讀者來說似更不易引起混淆)中引入的一個拉丁語詞匯vita activa,國內譯文多參照英譯本將其譯作active life的做法,譯為“積極生活”或“實踐生活”,但這樣似乎體現不出阿倫特用拉丁語以強調后置限定語的本意。考慮到海德格爾的名著《面向思的事情》及他和阿倫特的特殊關系對她思想的影響,本文將該詞首字母大寫為Vita Activa,并將之粗略意譯作“面向行的生活”,以示區別于阿倫特的理論,并更好地呼應于西方哲學中傳統的vita contemplativa(筆者認為可意譯作“面向思的生活”)。
? 在筆者看來,由于缺乏國教的背景,我國本土道教和泊來佛教的思想精華都在歷史的某些時段不得已以某種形式融入了儒教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因此它們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儒教的思想滲透力;而儒教對中華文明中創新libido的閹割正在于它把普遍性的倫理庸俗化為在世俗世界中作為生存手段的規則集合。非常遺憾的是,即便經過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歷次革命洗禮,真正認識到這一點的國人并不多。當然這也從反面佐證了國外學者把儒家稱為儒教的正確性。
[1]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 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4] 斯賓諾莎.倫理學[M].賀 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02.
[5] 休謨.人性論[M].關文運,譯;鄭之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331.
[6]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5.
[7] 韋伯.儒教與道教[M].王容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