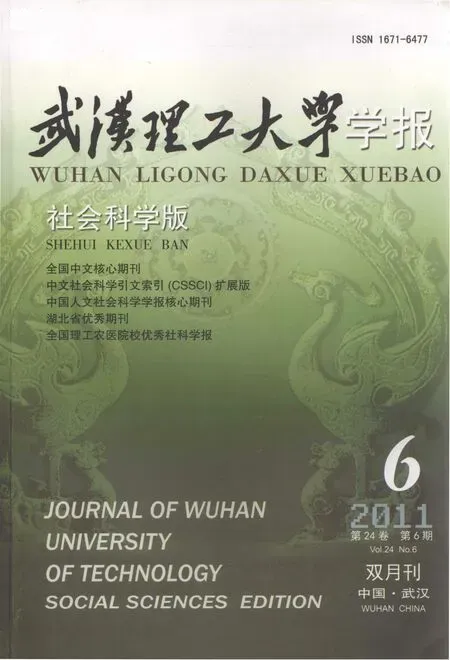娛樂的變態與變態的娛樂*
王銀芹,李 瑩
(1.孝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北孝感432000;2.北京中視電傳廣告有限公司,北京100022)
隨著互聯網技術應用的日益深入和普及,一些庸俗與低級趣味的變態現象被廣泛傳播和消費。這些行為本身就是對人們傳統娛樂觀念和娛樂消費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具體體現為娛樂的變態和變態的娛樂。
一、娛樂的變態
(一)娛樂的變態及其表現
本文提出的“娛樂的變態”是指:媒介為單純吸引受眾眼球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社會事件及其信息傳播中嚴重偏離正常軌道和價值標準,有意無意過濾事件本身的社會啟發意義,單純將社會新聞事件高度娛樂化傳播,甚至將其包裝成徹底的極端娛樂事件,或者對一些社會變態行為和事件過度追逐并放大為極端化娛樂事件的一種社會現象。
2007年的3月至4月間,有兩對人物曾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一對是被冠以“超級粉絲”的楊勤冀、楊麗娟父女倆;一對是號稱“史上最牛釘子戶”的楊武、吳蘋夫婦,他們都因為有強烈甚至極端的利益追求,并以其極端的行為方式而引起傳媒的圍觀和追逐。在一個多月時間里,全國各大報章、雜志以及主要網站紛紛跟蹤報道,各種評論也漫如潮涌。正是在對這兩件“大事”持續而亢奮的報道中,媒體自身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社會責任缺失和價值扭曲的怪圈,以一種無理性的狂熱鼓噪的娛樂心態,制造出一出出“媒介狂歡”的鬧劇,直接導致并擴大了娛樂的變態。
其一,楊麗娟事件。2007年3月22日,自《蘭州晨報》報道楊麗娟追星新聞之后,全國各類媒體迅速嗅出了其中的娛樂價值,“楊麗娟”甚至成為當時最熱的搜索項之一。在百度搜索中輸入“楊麗娟”,搜索結果顯示與其相關的新聞網頁就超過百萬。眾多平面和電視媒體,以及各大網站紛紛忙著開辟專欄,大量全景式跟進楊麗娟相關報道和討論,甚至也引起不少專家學者也將其作為一種現象來深入探討。就是這樣一個女生,從初中二年級開始便輟學在家,沉淪、癡迷于對所謂“夢中情人”劉德華的臆想癥中而不能自拔,既不工作也不談戀愛,對偶像劉德華的狂熱迷戀導致其自我世界的極端狹隘和封閉,脅迫家人傾家蕩產助其追星,最后將自己的父親逼上絕路,跳海自盡。內地和香港媒體同時對楊麗娟父親跳海事件給予了廣泛關注。不同的是,香港媒體普遍比較冷靜和理性,更多的是反思和批判;而內地媒體則如同發現娛樂金礦一般,派出大批娛樂記者全程跟蹤報道,大有狂追猛炒之勢。本應作為社會監督者和理性批判者角色的媒體完全墮落成為一群耍猴戲的吹鼓手。生怕楊麗娟父女幡然醒悟不再追星,他們不惜賣力起哄助威,煽風點火,還在幕后出謀劃策,資助其錢財,利用媒體的便利幫助父女倆辦理赴港手續,聯系“華仔天地”歌迷會,甚至答應幫忙聯系劉德華本人。正是在他們的慫恿、推動下,楊家追星欲望不斷得到鼓勵和強化,最后直接導致因面見劉德華的目的沒有達到楊父蹈海自盡。即使在楊父自殺慘劇發生以后,媒體依然沒有放棄這種極度亢奮的娛樂精神,依然緊緊纏住楊麗娟不放,將楊麗娟的點滴言行都做成極富娛樂色彩的“新聞”,將楊麗娟事件的娛樂價值發揮到極致。
任何新聞的價值——包括其時效價值和新聞總價值,總是有限的。沸沸揚揚的“楊麗娟事件”也不例外。眾多媒體在賺取了大量的“眼球經濟”之后,終于停止了對此事件連篇累牘鋪天蓋地般的追蹤報道[1]。然而,在這場娛樂新聞鬧劇中,媒體始終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無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在“楊麗娟事件”被極度娛樂化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太多媒體的身影。楊麗娟一家一貧如洗,如果沒有媒體的多方支持和鼓噪,他們追星的欲望恐怕還不至于無限膨脹。媒體廣泛而直接地全程介入直接將楊麗娟父女推上了一條追星的不歸路。在“楊麗娟事件”中,媒介不僅有制造新聞之嫌,更違背了新聞職業道德。
誠然,在“楊麗娟事件”的所有報道中,不能說媒體報道的情況是不真實的,但是這種真實很多是建立在有意識、有預謀地“制造”和“策劃”基礎上的,是一種“人為的真實”[2],更是一種真實的極端和變態。一旦媒介的娛樂報道走錯了方向,娛樂的變態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其二,重慶“最牛釘子戶”。一個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著一棟二層小樓,猶如大海中的一葉孤舟,工地四面全是高樓大廈,這樣的場景在現代化的都市里的確算是一個“奇觀”。因拒絕拆遷,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經網上流傳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3]。這就是所謂“最牛釘子戶”的來歷。
媒體在連續多天報道重慶“最牛釘子戶”后,“面對最后通牒,男主人奮勇攀登插旗守孤島”……極盡溢美、煽情的文字,再配上大幅帶有“沖擊力”的“奮守孤島”的照片——媒體幾乎毫無克制地動用了一切可能的熱情和手段,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件事的報道中來。該糾紛剛好事發于《物權法》剛剛通過之時,本來是具有一定社會典型意義和新聞價值的,但大量媒體將有關“釘子戶”的拆遷糾紛和利益訴求過于強化和扭曲,片面報道,過分張揚特定個人的“自由表達”權利,甚至將這場“拆遷糾紛”操弄成了一場通過渲染自我表演而賺取受眾“眼球”和同情心的T臺秀,基本不涉及對事件的理性分析和引導,完全喪失了媒體應具備的獨立和公正以及應盡的社會責任。這從媒體毫不吝嗇地大量使用“最牛”、“奮勇”等贊賞有加的措辭可以得到充分證明。顯然,正是這種對賺取受眾眼球的極度追逐,媒介有意識地將事件報道引入到了一種極度娛樂化的變態之中。
大眾媒介的首要任務就是監測環境,即要及時、全面、客觀、準確地向社會及公眾通報新近發生的事情和變化趨勢[4]。對“最牛釘子戶”事件的報道,媒介急于湊熱鬧,報道起來既不全面也不客觀,嚴重失衡。從全部報道來看,受眾從整個事件中獲取的信息并不完整。例如,這個拆遷工程是否手續齊全,程序合法?對其他拆遷戶是否都是按照國家標準進行補償的?對“最牛釘子戶”的補償標準是否低于國家標準?等等。這些信息對公眾了解事件真相從而做出正確判斷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拆遷本身手續不齊,或者拆遷補償缺乏公平合理,無疑“最牛釘子戶”就有權利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有權利通過正常途徑反映問題,作為政府也有責任維護“最牛釘子戶”的合法權益。相反,如果拆遷工程手續齊全,程序到位,補償適當,行為合法,被拆遷戶的對抗行為就缺乏正當性和合法性,那就是真正的“釘子戶”,不管他有多牛,當地執法部門必須采取措施進行強制拆遷。可惜的是,對如此重要的新聞背景信息,幾乎所有媒體在報道中都有意回避了,取而代之的是對楊武夫婦抵制拆遷、對抗拆的行為充滿褒揚和溢美之辭,且極盡煽情之能事,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讓公眾感受到真正的娛樂和快感。正是由于媒介不適當的過度關注和娛樂化參與,使“最牛釘子戶”夫婦騎虎難下,死撐硬挺地堅持下去,顯然媒介把這件新聞事件炒成了一個極端娛樂化的“猴把戲”。
(二)娛樂的變態產生的原因
其一,媒介對自身利益過度追求。隨著大眾媒介的多樣化和媒介競爭的日趨激烈,受眾并不是消極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新聞傳播活動最活躍的決定性因素。在新聞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受眾都在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地起著各種制約作用。在急劇的社會變遷和開放的社會聯系面前,受眾表現出旺盛的信息需求和盲目的信息選擇。因此所有媒介都面臨著一個傳播難題,即大眾的注意力分散,很難有信息能直接地持續地吸引他們。正如張朝陽所說:“在信息無限爆炸的時代,有一種東西是非常稀缺和有限的,那就是人們的注意力。”[5]因此,只有持續抓住受眾的眼球,傳媒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
正如評論指出:“楊麗娟瘋狂追星”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病態,不適宜在公共場合過度展現,更不能不顧社會價值瘋狂炒作。傳媒卻對她進行反復的聚焦、特寫、放大,不管形式上是對她表示支持和理解,還是抨擊她的癡狂,都是“圍觀起哄”的不道德行為,不能不說是一種讓娛樂變態的行為[6]。《人民日報》事后對“楊麗娟事件”發表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眾多傳媒熱衷于報道這件事的每一個細節和每個當事人的‘控訴’,卻唯獨忘了自己。事實上,將楊勤冀最終推下大海的,可能有幾只興奮的手掌,其中一雙用力最猛的,正是那些口水四溢的娛記和他們背后渴望吸引眼球、推高發行量的傳媒老總。”[7]
其二,媒介行業規范缺失。大眾媒介既有傳統媒介,也有新興媒介,它們都是社會信息傳播和溝通的重要平臺,影響日益擴大。前者包括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書籍等,后者則主要有計算機互聯網、電子游戲、衛星電視、手機等。正是這些媒介,不斷向公眾傳遞各種海量信息,并有意無意地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塑造和示范著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模式。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公眾對信息的依賴性日益增強,大眾媒介更顯得無所不在與無所不能,對公眾社會化、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都帶來了深刻影響。這其中不乏相當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媒介缺乏必要規范和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因此,加強媒介的行業規范建設顯得異常必要和緊迫。媒介規范不外乎兩個方面,即國家層面的宏觀管理和媒介從業人員的微觀自律。前者是指政府構建規范媒介行為的法律體系、方針、政策方面,是政府利用國家權力對媒介所實施的強制性控制和監督;后者是指大眾媒介從業人員的自律規范。大眾媒介的生存與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競爭和選擇,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法律的規范,以確保傳播價值符合國家利益和社會期待,但我國至今還沒有制定一部專門的全面的新聞傳播規范或者新聞法。這使得媒介行業往往為了經濟利益單純地依附于市場,不顧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德價值而忽視傳播活動應有的啟發性,鉆法律法規缺失的空子。因此,如何對其進行合理的引導和規范是我們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大眾媒介對公眾發揮著巨大社會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的正確發揮必須通過國家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來引導和約束,這是基礎的和根本性的。但社會的復雜性必然會導致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復雜性,因此不是所有的媒介行為都能通過法律條文來解決,缺乏完善的行業道德體系的規范是難以解決媒介信息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所有問題的。媒介行業不斷完善從業規范和行業自律公約來強化對自身行為的規范和約束是規范媒介行為和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方式。
在國家缺乏系列明確的有關媒介規范的法律法規情況下,加上媒介行業內部又缺乏完善的從業規范和自律意識,這就使得媒體在傳播活動中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約束。顯然,一切缺乏監督的權力都是非常危險的,媒介也不例外,娛樂的變態只是其危險影響的一個方面。因此,媒體在行使自己監督社會的權力的同時,更應該強化對自身的約束,這種監督才更有效,也更持久。
其三,社會環境影響。當前短視的造星手段和選秀節目甚囂塵上,對追星族的煽情與縱容,讓各種極端行為層出不窮,娛樂觀念也發生了極大的扭曲,從原來娛樂作品到娛樂藝人本身,莫名其妙的崇拜與追逐的背后卻是整個社會“娛樂”道德的惡化,使娛樂脫離了正常的軌道,失去了其愉悅人、啟發人的功能,導致了娛樂的變態。雖然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社會開放程度不斷增強,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不斷弱化而形成的社會寬容度增加,以及人們價值形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大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即使是當前社會環境下,如果媒介從業者能秉持職業道德,娛樂節目能多一份社會責任,新聞媒體能把握娛樂報道的正確方向,許多娛樂的變態悲劇都可以避免。讓娛樂驅除變態,回歸理性,需要全社會的努力。
如果說娛樂的變態是媒介傳播者沒有正確履行“把關人”的職責而傳播偏離正常軌道的娛樂信息或將新聞極度娛樂化來吸引受眾眼球的話,那么反過來,受眾對這種錯位的娛樂信息和極度娛樂化的新聞事件的高度追捧,就是變態的娛樂。
二、變態的娛樂
(一)變態的娛樂及其表現
所謂變態的娛樂,是指受眾為滿足自身娛樂消費的需要而對媒體通過偏離正常軌道吸引受眾眼球的極端炒作或極度娛樂化信息進行過度娛樂、消遣和欣賞的行為。媒介海量娛樂化新聞與信息帶給受眾全新的感受,吸引了眾多的人關注媒體,甚至使許多原本對新聞毫無興趣的受眾,也開始以新的眼光、新的心態感受新聞,感受娛樂。在此過程中,變態的娛樂也逐步被廣泛傳播和消費,并大有時尚化和潮流化的趨勢。下面筆者結合兩個具體案例對變態的娛樂進行探討。
其一,受眾對“芙蓉姐姐”的關注與消費。前兩年最火爆的網絡人物,恐怕要數“芙蓉姐姐”了。當時網絡處處刮起陣陣“芙蓉旋風”,她挺胸收腹翹臀的經典S照隨處可見,一大幫“蓮蓬”(所謂芙蓉迷)為此興奮不已。他們就像看猴戲一樣,津津有味地欣賞著“芙蓉姐姐”那些形態各異、造型夸張的玉照,回味她“驚為瘋人”的文字,不斷灌水、拍磚,盡管彌漫著嘲笑和謾罵,甚至以極大的熱情去考證她的身世和傳奇,恨不得將她幾代的血統都要“人肉”出來。正因如此,“芙蓉姐姐”現在已經無需親自策劃宣傳自己了,“蓮蓬”們享受著這些變態信息帶來的快感的同時,也成就了“芙蓉姐姐”在網絡上的知名度,并進而走進傳統媒體的版面,由虛擬世界的名人走進大眾的現實生活,甚至還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回報。例如,僅芙蓉姐姐個人網站廣告合作費報價就是每年100萬元——這,多么誘人!
事實上,“芙蓉姐姐”及“芙蓉姐姐”們在網絡上刮起的低俗文化之風,已經與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惡性的互動”,尤其是對正處在價值建構期的青少年,其負面影響是可怕的。在他們看來,網絡是個充滿魔力的神奇世界,誰都可以到里面秀一把,娛樂和消費別人甚至娛樂和消費自己都無所謂,即使是脫光了裸奔,即使是將自己的性生活公之于眾。那里沒有價值原則,沒有道德底線,沒有社會責任,只要你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只要你足夠出格,就有成名機會,且機會很大,成本很低。也許一不小心草根的你明天就會一夜爆紅,然后就是風光無限、出手闊綽的明星生活。借用一句廣告詞就是:“你不想試試嗎!”
其二,大眾對“惡搞”現象的追逐。惡搞是近些年才出現的詞。早期的來源恐怕還是伴隨著以周星馳為代表的港式喜劇進入內地而推廣開來。現在所說的惡搞,一般認為就是“惡劣的搞笑”,即通過惡作劇的方式取得喜劇性效果。尤其是在網絡迅速普及的情況下,以及網絡特有的傳播自主性和互動性,形成了一種以爆笑、搞怪、惡作劇為主要特征的另類創作風格[8]。
惡搞是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新型的娛樂方式,也是一種不同于原作的全新意義的再創作,它在中國的發展時間并不長。追根溯源,真正的平民惡搞狂歡應該始于21世紀初PS時代風行的小胖系列。此系列一出,立即成為網絡社區的第一圖片明星。PS時代之后隨即進入Flash動畫時代。Flash動畫以更為生動的形象和更具想象力的方式調侃并流傳。幾乎與此同時,真人惡搞時代接踵而來,芙蓉姐姐憑著自己開天辟地的“勇氣”及以此帶來的人氣,理所當然地成為真人惡搞秀的典范。此后,一大批模仿芙蓉姐姐的網絡惡搞人物相繼出現。2006年初以后,惡搞更是進入了一個集體狂歡的黃金時代,惡搞視頻《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無意中掀起了惡搞的高潮,胡戈也因此成為視頻惡搞的領軍人物。顛覆經典電影來諷刺當今現實,成為一種流行和時尚,惡搞短片因而風起云涌。由于惡搞文化愈演愈烈,商家迅速嗅到了其中的商機。2006年在黃健翔“解說門”事件中,其解說詞成為當時最熱門的彩鈴之一。惡搞消費帶來了可觀的真金白銀,網絡惡搞也逐步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當然也引起了不少的爭議。當今社會,任何具有爭議的事情往往更容易受到關注,也就更容易流行。
惡搞發展至今,很多情況下已經很難指出惡搞的具體意義和目的。多數情況下,惡搞的人只是把它作為一種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個人幽默的體現途徑,例如關于機器貓的惡搞和斯巴達300勇士大叔的惡搞,都屬于個人喜好和表達幽默感的一種途徑。從天涯、新浪、網易等國內主要門戶網站論壇留言來看,相當一部分網友對惡搞持支持態度,但過度過濫的惡搞對于娛樂圈來說絕對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倘若一定要說是一種態度,那就是一種有害無益的變態[9],對社會主流價值的構建顯然也是有害無益的。
(二)變態娛樂產生的原因
追逐和消費這種變態娛樂的受眾主要為年輕一族,而導致這個群體式追逐和消費變態娛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與上一代人不同,當代年輕受眾更強調個性與反叛。他們更排斥順從,更強調個性張揚和反叛精神。加上我國主流文化作品多半具有相似的內容和風格,不僅容易導致審美疲勞,也難以激發受眾的亢奮感。而“惡搞”就是顛覆經典,張揚個性,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特征。將傳統的虔誠、嚴肅、永恒、穩固、絕對、不可變更等神圣性“降格”,為傳統的高雅“脫冕”,從而在解脫羈絆和粉碎禁錮中獲得自由,以期將神圣世俗化,將嚴肅庸俗化,從而形成“語境矛盾”。而“語境矛盾”本身就有一種戲謔的成分,是黑色幽默的慣用手法。變態的娛樂就是以這樣一種極端的娛樂心態來制造和消費極端娛樂信息,讓他們自己在瞬間的極度亢奮中獲得快感和滿足,從而用一種極端來反抗和打破強大而無形的傳統從眾壓力,實現短時間的個性張揚和釋放。
其次,當今年青人面臨著更多更大的社會壓力。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越來越不可預期的前途,使當代青年面臨的生存壓力前所未有。“惡搞”以它強烈的娛樂功能,能較好地釋放人們生活中的緊張與疲憊。多數青年人面對現實時充滿無奈,對利益的追逐和競爭,人際交往日趨淡漠,他們既希望保持個性,又希望得到社會承認。不少青年人無力解決諸多現實問題,理想、抱負與現實的差距太大。當變態的娛樂浪潮洶涌而來時,他們似乎找到了“用武之地”——以“天之驕子”的濟世熱情、智慧和技術表現出強大的俗文化建構能力,實現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最高層次——“實現自我”的需要[10]。更多的年輕人則希望通過“惡搞”、“無厘頭”、“自我炒作”獲得快樂,釋放壓力,或者藉此出名,改變現狀。
再者,電腦與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為變態的娛樂流行提供了硬件環境。網上公開的圖像、音頻、視頻很容易通過一些軟件重新編輯并賦予新的表達主題,這為“惡搞”作品的草根創作提供了現實可能性,而互聯網則為這些惡搞作品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條件。作為一種高互動性媒體,網民很容易通過網絡平臺對“惡搞”作品進行再“創造”和再傳播,使“惡搞”作品在惡搞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加之網絡的虛擬性和隱匿性,現實生活中不愿意說的話或不敢做的事都可以在網絡上“瘋狂”地宣泄出來,也使“惡搞”更易偏離正常社會價值。基于精力和技術原因,目前網絡監管難度較大,這給變態的娛樂留下了廣泛的自由空間。
另外,意識形態控制的弱化及由此帶來的文化多元化為變態的娛樂流行提供了軟環境。在過去強調意識形態的時代,不高雅、不嚴肅的東西會被視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毒瘤而被嚴厲禁止,更不用說公開傳播了。隨著意識形態控制的弱化,文化多元化趨勢明顯,人們對于非主流文化的態度越來越寬容,盡管不一定贊成,但往往也不會干預,這為變態的娛樂提供了生存空間。
最后,信仰的缺失導致社會精神的空虛與無聊,由此而帶來的精神麻木為變態的娛樂提供了存在的精神土壤,使低級趣味有了可乘之機。在當前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我們以往奉為圭臬的一些精神信條轟然崩潰,最終導致信仰選擇的困惑與迷失。與此同時,主流精神和價值信仰的缺失使人們變得越來越浮躁,越來越急功近利,唯利是圖,每個人心里都倍感精神饑渴和焦灼,卻茫然不知所從,這給變態的娛樂進入大眾的生活及填補一時的精神空虛而大開方便之門。庸俗的精神快餐如同鴉片一樣,不斷麻木、侵蝕著大眾的精神信仰,并由此形成無聊——空虛——變態的娛樂填補——更無聊——更空虛的惡性循環。大眾媒介是擔負著營造積極健康文化環境的“中間人”,它應該也有責任帶領人們步出迷茫,引領人們尋找永恒的價值和精神家園。
三、對娛樂的變態與變態的娛樂現象的思考
第一,要強化媒介的社會責任,避免媒介方向迷失。利益驅動極易使媒體在追逐所謂熱點時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經濟利益是市場條件下現代媒介必須而且應當追求的目標之一,這一方面是媒介得以存在下去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刺激媒介不斷完善自我從而不斷贏得競爭、贏得市場、促進媒介自身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然而,無論在什么社會壞境下,單純的經濟利益都不應也不能成為傳媒活動的首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職業道德規范都把傳媒的“責任”放在該職業信條的首位[11]。傳媒的社會責任是媒介實現良性發展的立身之本。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特殊國情的國度,大眾媒介依舊承擔著社會教化的重要職責,在促進社會和諧與民族復興事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對主旋律的傳播具有強烈的示范功效,感染、鼓舞和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華夏兒女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與社會和諧努力拼搏;同時,大眾媒介及其傳播行為本身就是社會文化環境的組成部分,直接影響著社會風氣和公眾的價值取向,尤其是對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更是影響巨大。因此,大眾媒介無論如何都不能單純為了收視率、發行量而不惜漠視甚至放棄媒介自身的社會責任,這既會斷送自己,也會敗壞社會風氣。
當前我國社會處于劇烈轉型期,社會價值觀也出現了深刻變化,道德示范現象層出不窮。一些嚴重違背社會公共價值的“道德無底線”的個人行為屢屢出現,作為媒介,一方面要客觀、適度地對其予以報道,另一方面,更重要地是要通過正確而適當的評論加以引導,而不是盲目起哄,惡意炒作,更不能是非不分,顛倒黑白。實際上,真實可靠的信息傳播有助于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的實現,能增進社會理解和群體磨合,促進社會和諧進步,更有助于公眾增強對媒介的信任,從而贏得受眾,贏得市場,獲得長遠發展。
第二,要提高受眾自身的媒介素養,增強人們對信息的甄別和選擇能力。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在我國,溫飽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人們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關注和享受休閑娛樂活動。但是在此過程中,也反映出受眾自身媒介素養不高,信息甄別和選擇能力欠缺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受眾對海量信息缺乏必要的甄別與選擇能力。現代媒介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既為受眾獲取信息帶來了便利,同時也使受眾在面對海量信息時顯得茫然無措,尤其是在我國公民媒介素養整體不高的情況下。僅“楊麗娟事件”網絡新聞就多達100余萬條,而近期被熱炒的“郭美美事件”,其網絡新聞更是突破千萬條,還不包括浩如煙海的網絡留言、評論,以及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給予的長篇累牘的相關報道與評論。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受眾也只能跟著起哄湊熱鬧。正是在這樣一種受眾缺乏必要的信息甄別與選擇能力的情況下,受眾與媒介一起上演了一曲曲變態娛樂的狂歡,直到楊父蹈海自溺,家破人亡。
其二,受眾缺乏對媒介建構事實的獨立思考與理解判斷能力。李普曼在其著作《輿論》(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指出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擬態環境”中[12]。大眾傳播媒介正是通過自己的信息傳播行為為受眾營造了一個不同于客觀現實,但與客觀現實高度相似的環境,是它們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傳播來構建而成的。傳播媒介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天然的傾向性決定“擬態環境”不可能是客觀環境的原版重現,只能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象征性環境。在現實生活中,大眾通常容易順應媒體的不正確引導。
其三,受眾在應用現代傳播媒介時普遍存在不當使用行為,尤其是在現代網絡傳播工具的應用上。網絡媒體的自主性、互動性特征明顯,以往簡單和單向的信息生產與消費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僅信息生產與消費界限日益模糊,傳統的守門人制度趨于弱化,甚至出現了無法守門和無人把關的情形[13]。受眾在網絡世界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媒介的互動參與,并輕松擁有信息隨時隨地生產、傳播的自主權。而網絡虛擬空間帶來的責任虛化感,在部分受眾媒介素養欠缺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極端的不理性言行,形成信息傳播的失控,破壞傳播環境與社會和諧。曾經被個別網站當做搖錢樹的張鈺“性視頻”事件,以及前段時間網上爆炒的“接客門”視頻等,都是傳播媒介被不當使用造成的。
第三,要強化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信仰教育,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價值觀是支撐人們生活的精神支柱,它決定著人類行為的取向和方式,對人類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導引意義。加強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就是通過政府、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系統教育與影響,使受眾形成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價值評判和選擇標準。人類一切活動從根本上講都是立足于自身,都是圍繞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來進行的。信仰教育不但不例外,人生觀意義甚至更為明顯和強烈。作為一種精神價值,信仰反映的是人對人生的精神需求和終極把握。加強信仰教育有助于受眾對信息的正確判斷與選擇接受,有助于對庸俗低級趣味信息的自覺抵制,有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精神的構建與鞏固。
因為大眾媒介的影響力決定了它必然具備一定的權威性,傳播的內容具有公開性、顯著性,以及同類報道的強化和傳播時間的持續,容易形成信息疊加與累積,這種不斷提示和強調的意見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容易被認為是合乎潮流或民心所向的,從而裹挾更多受眾接受它,成為引導公眾信仰建構的主導力量。所以大眾媒介應多擔當指引健康向上輿論的風向標,為受眾形成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和主流信仰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豐富大眾的精神生活,讓大眾的生活不再麻木、空虛、無聊,讓低級趣味失去其滋生的土壤。
[1] 注意力的經濟觀[J].張 雷,編譯.國際新聞界,2000(4):37-40.
[2] 田 瑾.“楊麗娟事件”出爐幕后[J].記者觀察:下半月,2007(4):49-51.
[3] 聚焦重慶最牛釘子戶[EB/OL].[2011-07-15]http://news.sina.com.cn/z/cqzndzh/.
[4]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 老板新人類——訪北京搜狐公司總經理張朝陽[EB/OL].(2003-06-09)[2011-07-15]∥www.people.com.cn/digest/199910/rwxz.html/.
[6] 李曉玲.從“楊麗娟事件”看媒體的責任[J].傳媒觀察,2007(5):25-26.
[7] 李泓冰.誰害死了追星女之父?[N].人民日報,2007-03-30(5).
[8] 高字民.惡搞的文化闡釋[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86-88.
[9] 路 勇.惡搞,是一種什么態度[N].信息時報,2006-12-30(C4).
[10] 黃敬寶,莫曉紅.透視網絡惡搞:當流行文化時尚走向淺薄和粗鄙[J].中國新通信,2007(18):12-13.
[11] 申 凡,戚海龍.當代傳播學[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87.
[12] 周維維.淺析“擬態環境”形成的原因——對李普曼《公共輿論》中傳播思想的再開掘[J].才智,2011(27):307,345
[13] 王方群.傳媒素養是網絡文明的基石[N].北京日報,2006-08-07(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