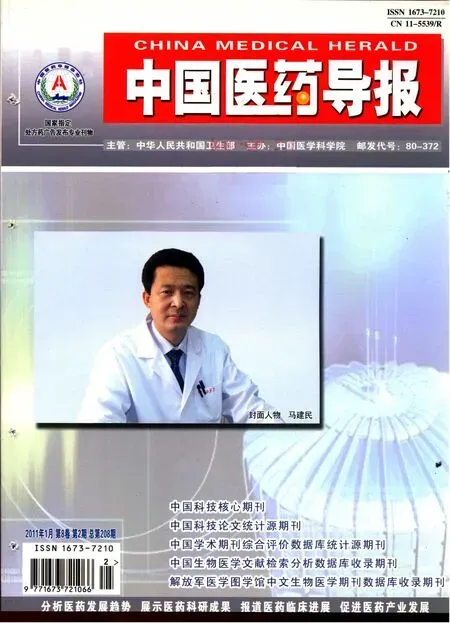葉霈智博士:將中醫抗癌進行到底——訪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中醫科葉霈智博士
文圖/《中國醫藥導報》記者 馮 婕
每一個真正熱愛自己事業的人,必定會把這個事業當作自己的信仰,并為之不斷地努力和奮斗。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葉霈智博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2006年,葉霈智畢業于北京中醫藥大學,并獲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博士學位。畢業后,他來到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中醫科工作,從事中西醫結合治療腫瘤的臨床和科研工作,并特別專注于中醫配合放化療、改善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期方面的臨床觀察和研究。
我國著名中西醫結合腫瘤、血液病專家陳信義教授是葉霈智在碩士、博士階段以及在東直門醫院實習期間的指導老師。陳信義教授開闊的臨床思維、嚴謹的治學態度、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以及對待病人的責任心,深深地影響著葉霈智。他回憶說,陳教授在年輕的時候,被同事們送了一個外號——“霓虹燈下的哨兵”。因為陳信義每晚都會花幾個小時在辦公室看書或查閱專業文獻。對此,葉霈智深有感觸,決心以老師為榜樣。他堅信,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去做,將來一定會有所收獲和成就。
在攻讀博士學位階段,葉霈智參加了首都醫學發展科研基金聯合攻關項目“浙貝母逆轉白血病多藥耐藥性臨床應用研究”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復方浙貝顆粒逆轉急性白血病多藥耐藥臨床研究”等科研項目,并榮獲2007年度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二等獎(第四完成人)。
葉霈智擅長運用中醫藥方法進行手術后調理,有效減輕放化療副作用,如腹部腫瘤術后胃癱、宮頸癌術后尿潴留、放射性腸炎等;并對中西醫結合治療老年、中晚期腫瘤有一定的研究。他說:“中醫在不同階段的治療配合是不一樣的,好比一場大戲里面有好幾幕,可能在頭幾幕里中醫只是一個配角,而后面就變成了主角。在放化療時,中醫就是一個小角色,僅負責緩解放化療的副作用,減輕術后的不良反應;但當放化療結束后,中醫治療就會轉變成一個主要角色,并且會長時間地起主導作用。”葉霈智始終認為,對于可能根治的惡性腫瘤患者,中醫藥治療可以與積極的抗癌治療(如手術和放化療)相互配合,以緩解癌癥及抗癌治療所帶來的不良癥狀,保障患者在癌癥治療期間的生活質量。

在葉霈智博士的個人主頁上,有不少他的論文精選和有關中醫抗癌的醫學科普文章。其中,在一篇名為《腫瘤頑固性呃逆的用藥思路》的文章下面,記者看到了網友這樣的留言:“我爸爸是胃切除手術后出現頑固呃逆,經腫瘤醫院的醫生醫治,也是以上面的第二種方法治好的!”這“第二種方法”即文中所說的“丁香配伍郁金,相反相成”。然而,中藥“十九畏”中明確提出“丁香莫與郁金見”。記者對此頗感興趣,好奇地問:“是什么促使您在臨床用藥上去突破傳統呢?”葉博士說:“這個嘗試是受我國知名腫瘤專家王沛的影響,也結合了我過去看到的相關文獻。”他在臨床過程中發現,虛寒之呃逆在丁香柿蒂湯基礎上加用郁金,常可獲良效,且未發現不良反應。此外,他還例舉了幾味中藥:如生半夏除了能降逆、止嘔,還對腫瘤有很好的軟堅、散結、化痰作用,可適當配伍生姜,但煎煮時間要長;再如,臨床上經常遇到附子同用半夏和貝母,而中藥“十八反”中提到“半蔞貝蘞芨攻烏”。葉霈智說,附子是植物的側根,烏頭是主根,二者具有共性,因此理論上附子同用半夏和貝母應該會有毒副作用,但這幾年中,許多患者三藥同用,卻未發現有毒副作用。
葉霈智不僅在中藥配伍上敢于突破傳統,在用藥劑量上也敢于打破常規。一名患淋巴瘤的、做了幾次化療的患者,由于腦部已受淋巴瘤侵犯,機體消耗過大而臥床不起。葉霈智給其第一次治療的黃芪用量就達100 g。他說:“需要補氣的癌癥患者黃芪可用到40~60 g,如果病人氣虛比較明顯,我會用到150~160 g。”他還主張少用炙黃芪,用量過大容易上火,或有其他副作用。又如茯苓,常規用量為9~20 g。曾經有一位食管癌病人,晚上返大量白色痰涎,吃下去的東西全被痰液頂了出來。葉博士給其用了60~90 g的茯苓,效果甚佳。又如代赭石,作為降逆止嘔的藥,一般用量為20~30 g,腫瘤治療用量可達 50~60 g。 附子一般用量為 6~9 g,但葉博士曾經用到200 g,多的甚至用到300 g。他總結認為,附子對于一些重病患者,有時候必須突破常規用量;但是,“要突破常規,一是要根據別人的經驗,二是要自己親身去試驗。”
葉霈智博士還認為,中醫藥在腫瘤根治性治療方面不是強項,但在處理癌癥相關癥狀方面則具有較好的療效,可以彌補西醫的不足,有效提高生活質量,它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優勢成為這個舞臺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