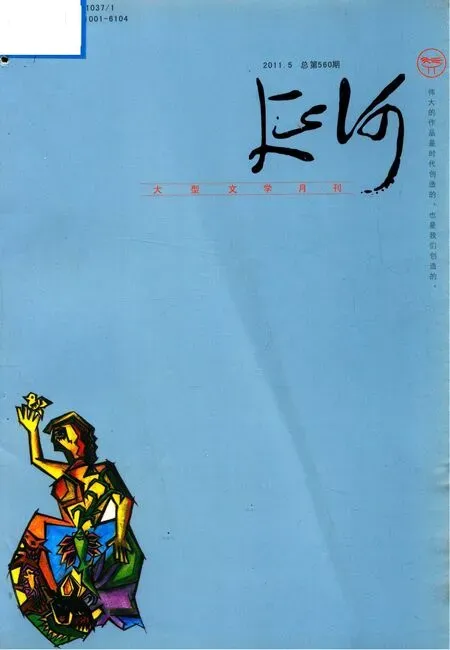時尚 消費時代的第207根骨頭
馬小鹽

時尚大師圣羅蘭與他的第207根骨頭
第207根骨頭
2008年6月,法國時尚界傳奇人物圣羅蘭去世。法國報刊在發布這一令人喪氣的訃聞的同時刊登了一則有關圣羅蘭日常生活的趣聞,說圣羅蘭幾十年如一日地戴著一副從不更換的眼鏡。一位在時尚界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花樣百出的設計大師,為什么對一副拙樸的眼鏡如此癡情?在我看來,這則趣聞不但充滿了矛盾修辭法,更涉及到了時尚符號學的根本。時尚的秘密何在?時尚的秘密就在圣羅蘭與他的眼鏡之中。
常戴眼鏡的人,會發生這樣的錯覺,他會把自己的熟悉的那款眼鏡誤認為是自己身體上的一部分,它是他的第207塊骨頭,而非身外之物。圣羅蘭亦然。要知道,消費時代,人們消費的不是物的使用價值,而是物的剩余價值、夢幻價值、符號價值。這些價值由電視、電影、網絡等媒體輪番轟炸喃喃絮語的廣告所催生。圣羅蘭這一時尚品牌的系列產品不僅僅是用來蔽體的衣服,用以飾面的化妝品,用以噴灑的香氛等等,它更給消費者傳遞著這樣的時尚信號:使用圣羅蘭產品,你就成了貴族。你會變得高貴、優雅、藝術、富有。圣羅蘭作為一個時尚造夢人,引導且催眠著消費者進入他所締造的貴族式時尚仙境,使得購買者迷醉于“圣羅蘭品牌眩暈”里不能自拔,而他自身卻超然物外。這是時尚巫師的魅惑本能。與原始部落相比,消費時代的時尚大師替代了原始部落里巫師的魅惑職能:信徒虔誠下跪膜拜,巫師手握神秘權柄與上天相連相通。信徒在巫師的指導之下消費各種各樣的物,巫師卻堅守著某一確定不移的品質。在圣羅蘭與陪伴他一生的眼鏡之間,存在一個這樣的真理:時尚這個詞匯雖然妻妾成群的擁有頗多能指,所指卻匱乏到如君王般高貴。圣羅蘭的眼鏡就是圣羅蘭對時尚的轉喻。它有且只有一個,它咄咄逼人的宣告著這樣的旨諭:我即時尚。
有一位詩人朋友,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總是戴著墨鏡。墨鏡成了他與這個世界的邊界。這令我想起了亦有佩戴墨鏡癖的電影導演王家衛。墨鏡于他們已經成了一個符號,一條與外界隔離的邊界線。他們躲藏在烏黑的鏡片之后窺視別人,而別人無法穿越那兩片烏云去窺視他們。墨鏡在此既有一種類似于偷窺的攝影鏡頭般的功用,更起著噴射墨汁的章魚的自我保護效應。然而,最令我好奇的是像王家衛和我朋友此類不分白天與黑夜般戴墨鏡的人,偶爾摘掉眼鏡會給觀看者造成什么效應?要知道一個總被神秘遮掩的部位,驀然裸露出來,其驚駭度絕對不下于一部恐懼片的驚駭度。曾見過一位戴墨鏡者,突然在我的面前摘下墨鏡來,將我嚇得不輕,并覺得自己莫名的受了侮辱,因他眼光里有一種類似于露陰癖患者的病態神情:露陰癖患者以暴露他們的生殖器來驚嚇人,戴墨鏡者以暴露他們傷口般的眼睛來嚇人。
一些男人戴眼鏡與一些女人戴文胸的功用相同,是技術性的。這些物件是身體的修辭。眼鏡是對眼睛、鼻梁、整個臉部的修辭。文胸是對女性乳房的修辭。對于女人而言,文胸是身體上外延出去的建筑性陽臺。此陽臺專門用于陳放、烘托、美化、修飾、放大《圣經》里所贊美的鴿子般潔白的女性乳房,并四周裝飾滿蕾絲花邊、蝴蝶結、小緞帶等等可愛的人造物,一若建筑陽臺上掛滿了藤蔓纏繞、香味混雜、姿態各異的花卉盆景。2010年春節聯歡晚會,素以“乳名”稱霸江湖的臺灣女演員林志玲就因這修飾性陽臺的意外拆遷,胸前頓失奇觀色彩(由慣稱的D杯縮水為B杯)。而毫無“乳名”的笑星蔡明卻因古典緊身衣與聚攏文胸的恰當使用,忽獲豪放“乳名”。男性網民因而驚呼:2010春晚最大的魔術,是志玲姐姐的胸跑到蔡明阿姨那里去了!
很多人都有第207根骨頭。這一根骨頭是人類贈送給自己的禮物。上帝造人,并從亞當的軀體里取走第207根骨頭造了夏娃,人類自此后一直對上帝此舉耿耿于懷,他們與上帝為敵,他們要找回屬于自己的那一根骨頭,他們孜孜不倦的想借外物恢復自己的第207根骨頭。于是,具有原創精神的作家的第207骨頭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作品里獨特的風格。具有天籟之聲的歌唱者的第207骨頭不是他所唱的歌曲,而是他獨一無二的發音特質。具有創造精神的時尚大師的第207根骨頭不是他設計的時尚產品,而是他鼻梁上從不遺棄的眼鏡。消費時代的消費者也有第207根骨頭,只不過他們的這根骨頭在不同的時間,呈現出不同的容貌。他們是被蠱惑、被引導、被放牧的信徒。他們在時尚巫師們的牽引之下,借著各種各樣的時尚之物,不停的置換著那一根永遠無法確定卻渴望擁有的第207根骨頭。
黛塔的軀體
在后現代社會,身體不僅僅是身體,身體是一件上帝賜予的鑲嵌滿神奇之物的器皿。這器皿盛載著各種各樣語意復雜的文化符碼。世界首席舞娘黛塔?范?提思(Dita Von Teese)的軀體,便是這樣一本厚厚的百科書籍。因無論她的軀體穿衣還是不穿衣,皆宛若中古時代的羊皮卷一般書寫滿令人驚異的時尚圣經。
黛塔使得脫衣舞成為一種純粹的表演藝術。在晶瑩的大酒杯前,她身著鑲滿鉆石的塑身內衣,披掛一如即將出征的女皇,表演一場命名為《沐浴》的脫衣舞蹈。與麥當娜身著塑身內衣在舞臺上高歌的含義截然不同,麥當娜強調的是女人有內衣外穿的權利,塑身內衣在黛塔的身上歸還了它原本便具有的古典語意:女性的軀體,是被修剪的軀體。女性的胸、腰肢、臀,該細則需細,該肥則需肥,但無論肥瘦皆需花枝般修理的合于古典審美。黛塔在音樂聲里打開香檳,肆意脫衣。脫光了的黛塔的玉體鳥兒一般棲進酒杯。香檳、沐浴、清洗,潔白晶瑩的肉體盛放在酒杯里,與酒嬉戲,欲醉不醉。軀體在翻滾,軀體在舞動,四肢在招搖,酒液在翻溢,每一個動作都在曖昧暗示請君享用,請君迷醉,實則卻在遠遠相拒。性的盛宴,由觸覺游戲轉為純粹的視覺游戲,眼睛代替了手指,刺激著力比多的分泌。
脫衣舞娘黛塔是一道文化景觀。每次出席上流社會的聚會,雪膚、紅唇、黑發、豐臀肥乳、腰肢纖細的黛塔比明星貴婦們呈現出更為高貴的穿衣品味。她的衣著總是合體得當,她的發型與配飾總是恰如其分。她站立時尚的當下,將古典時代的審美迎回。中國女星范冰冰最近的穿衣風范便很明顯地在模擬黛塔的審美。如果說華裔女星白靈能把香奈兒穿成舞娘服,那么黛塔則可把舞娘服穿成香奈兒。她,充滿誘惑卻不可褻瀆。是的,脫衣舞娘的不可褻瀆。巴特說脫衣舞實際上是一種將性進行完全祛魅的表演。在舞臺上邊跳脫衣舞邊進行沐浴的黛塔證實了這個真理。齊澤克說古典愛情故事的美麗皆建立在貴婦人的不可觸碰之上,貴婦人實際上是男人塑造的不可觸碰的想象物。黛塔亦驗證了這位哲學家的觀點。黛塔的魅力就在這里:她能將古典貴婦的形象以脫衣舞女的身份幽靈般再現至后現代社會。無論貴婦人還是脫衣舞女郎,二者皆是被蓄意誘導、隔離、審查、消費的身體。這身體宛若收藏在博物館里的價值連城的上古玉器,我們只能透過冷冰冰的玻璃層觀看,卻無法真正觸摸它們的軀體。

貴婦與蕩婦的綜合體:黛塔

擁抱地球的麥當娜喻示著女權時代的到來
如果說夢露是嬰兒面孔蕩婦身軀,那么黛塔則是貴婦與蕩婦的混合體。夢露的性感是孩子氣的,黛塔的性感是女人味的。夢露之所以成為全世界男人的性偶像,是因她豐滿的身軀與天真的臉龐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夢露的面孔寫滿了迷途少女的常見詞匯。即若白色長裙被風旋起,她的笑容都無邪的令人心碎。天真的眼眸,微張的紅唇,沒心沒肺的笑容,都在告訴男人:我是個孩子,我迷路了,請你給我指引。給這樣的女人充當耶穌完全可以喚起大多數男人潛在的英雄主義。夢露的美是迷途羔羊的美。相比夢露,黛塔的美是危險的。黛塔的臉與肉身并不相悖,她的面貌與她的身軀同一。她的面孔告訴男人:我,是個女人。我,很妖媚。我,也很高貴。我,完全可以像操縱脫衣舞道具一樣嫻熟的操縱你。征服我,是你的榮譽。一言以譬之,夢露的魔術在召喚都市人群中擦身而過的牧羊人,黛塔的魅力則在召喚消失在歷史縫隙中離我們遠去的騎士。
鞋之神話的終極
在童話故事里,小腳一直是女性美的一部份征徽。格林童話《灰姑娘》里的那只玲瓏水晶鞋,我們可以將之當作西方古典男性用以衡量女性美的一個標尺:在某個尺度內,就可以美至做王妃,在某個尺度外,就排除了做王妃的機遇。《灰姑娘》里的水晶鞋與中國的三寸金蓮意義相類,在腳的審美趣味上,東方男性與西方男性可以說是臭味相投,殊途同歸。
巴爾扎克有篇與《灰姑娘》相應成趣的童話叫《驢皮記》,講的是一位公主因其父的亂倫式愛戀,被迫披著驢皮離家出走流浪荒野。一日她在不曾穿披驢皮的情形下與一位王子相遇,王子愛上了她,并撿到了她手上所戴的戒指。與《灰姑娘》里的情節相同,這位王子為了找到他的心上人,就許諾誰戴上了這枚戒指誰就是他的新娘。我不清楚是什么緣故使得這個故事不如灰姑娘般廣為流傳。是因故事涉及到了亂倫的禁忌,還是人們對女性纖細手指的審美比不過對腳部的審美?千百年來,人們對女性的腳的大小的深切關懷,遠遠超過了女性軀體的其他部位。

貝克漢姆之妻辣妹所穿的無跟高跟鞋
日本的藝伎文化將女性植物化表達的最為徹底,那些當時名氣最盛的藝伎,藝名往往是:松、竹、梅。從男性植物化女性的角度看,植物性女子的軀體除腳之外的其他部位,完全可以當作植物的葉莖花來審視。而腳,卻是可以行走的柔軟器官。海倫的私奔,使得男人們審視這柔軟器官的時候,多了三分警戒。他們非常明白,一株能夠行走的旖旎植物,既魔幻又有許多潛在的危機。中國人辱罵一個女子的最惡毒的詞匯便是破鞋。鞋而破之,顯然在說明此鞋的存在對腳的毫無禁錮。這個詞匯一語道明了鞋之于女子貞操的刑具本質。西諺云:婚姻如同鞋子,合不合適只有自己知道,說這句話的想必是位深諳鞋子威力的男性。因此,三寸金蓮與高跟鞋在東西方兩個向度,皆以美的名譽,發揮著男權意識形態要將女性的腳足根須化的威力:植物的根須特征便是細小、向下、長且深的扎入大地。
東方的男權意識形態比較愚笨。三寸金蓮純然依靠肉體摧殘的方式將女性的腳足縮微變形為馬鈴薯般的塊莖植物。西方的男權意識形態卻在依賴科學,他們借助外物對女性的身體進行修辭。高跟鞋就是一種將女性的軀體拔高、變細,使之在行走時變得更為緩慢輕盈,從而篡改人體比例的修辭術。然而,男性將女性的腳足根須化發揮的最為淋漓盡致的卻是在19世紀出現的唯美至極的芭蕾舞鞋。我們只要觀看一些芭蕾舞的足尖舞片斷,便能明白。那些精致窈窕的女人們,穿著輕紗,掂起腳尖,將腿腳完全幻化為兩根根須般的細線,在舞臺上跳躍、歡奔,表達著仙子般的輕盈與活潑。而那細薄的足尖,卻若植物的根須,離地一霎之后,墜落下來,似乎要深深地植入大地。
美國艷星麥當娜的造型,開啟了女性最為徹底的自我植物化的先河。這些自我植物化的手段包括:曖昧迷離的臉龐(花蕾)、完全裸露的身體(花莖)、捆綁般的網格絲襪(花枝)、高若尖刀的鞋子(花根)。這個將自我完全花蕾化、每一寸肌膚皆幻化為性器的女人,通過利用而非屈從于男權意識形態的方式,完成了女性對男權意識形態的顛覆,從而成為自身與男人們的王。這是個有趣的悖論:女人們積極的迎合著男權意識形態,男權意識形態卻因這過度的迎合而分崩離析。傀儡的操縱者反轉為被傀儡所操縱。近日看到幾幅新穎的時尚圖片,英國歌星辣妹穿著一款無跟高跟鞋出席于某一重大社交場合。這款鞋子看上去完全是芭蕾舞鞋的變異。它的整個重心移于腳尖,所穿之人的軀體傀儡般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提高,行走起來宛若音樂盒上那技藝超群的芭蕾舞星,永遠的掂著腳尖,體態輕盈,御風而行,處于美的凝固之中。
從貝克漢姆之妻辣妹的一款無跟高跟鞋里,我看到了未來鞋子的走向。無跟高跟鞋將是女性鞋之神話的終極。麥當娜的成功是所有現代女性的榜樣。現代女性就是要以輕靈而植物化的足尖,舞在男權意識形態的審美舞臺上。這舞步即在愉悅以男性為主體的主流審美,又在摧毀男權意識形態的堡壘。芭蕾舞鞋式的無跟高跟鞋,悄悄的唱響了女性足部根須化至利刃化的蛻變之歌,亦進一步唱響了男權文化日漸衰落的挽歌。

色情而受虐的Enchanted Doll
Enchanted Doll的魔法所在
最近一種名叫Enchanted Doll人偶紅遍網絡。Enchanted Doll譯過來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人偶。在欣賞這類人偶的精致之余,我感興趣的是這類人偶的魔法之所在。頗多喜愛者說這人偶令她們吃驚,凝視它們的眼睛,你會覺得這些人偶也富有靈魂。但是,觀看人偶之母Marina Bychkova所有的作品,你會發覺,這些由陶瓷燒制而成的身高不過三十多厘米的所謂具有魔力的人偶,統統具有這樣的共性:她們眼神哀怨,宛若破損的晶瑩傷口。她們軀體色情,肉身上遍布滿女性性高潮來臨時的紅暈。她們關節外露,骨骼與肉身同處共一凝視。她們瘀痕斑斑,宛若正在朝某一假想人物遞交女性受虐申請書。
據我所知,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偶是以女性這一性別作為原型。這告訴我們,即若在玩具的文化意識形態中,女性,亦屬于這樣一個種屬:玩物。從色情的角度看,女性成為玩物,與女性的容貌與軀體比起男性來更具有觀看意義有著密切關聯:她們的臉蛋涂脂抹粉,她們的軀體曲線優美,她們的靈魂撲朔迷離。所有現存的文學作品告訴我們,女性是迷。女性之所以是迷的原因在于,女性不但具有性誘惑力,還具有與性一樣的令人迷惑的本質。女性比男性更接近性本身。如果說男性這個詞匯的詞根重點在于男字上面,那么女性這個詞匯的詞根重點則在于性。
比起美國的芭比娃娃的塑料材質,新近流行的日韓SD、DSD娃娃的高級樹脂基質,Enchanted Doll原材料上就技高一籌,它以瓷為底。眾所周知,瓷器是由泥土燒制而成。從神話學的意義上看,人類亦誕生于泥土。瓷的底子,是賦予模擬人類的人偶生命力的最佳材質。瓷的光滑,瓷的白凈,瓷的脆弱,令人偶之美更接近于現實生活中的女性之美,要知道在傳統審美觀里美麗的女性本該如此:她們皮膚光滑宛若瓷器,她們肌體白皙一塵不染,她們嬌小脆弱風不可吹。所有這一切,都在告訴我們,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是弱者。Enchanted Doll的第一個魔法,便來源于它幾乎以假亂真的仿女性肌膚的材質。Enchanted Doll是女權時代的人偶對傳統女性美的致敬、追憶,更是最后一瞥。
為了使得人偶更富有靈氣,Enchanted Doll采取了人偶工藝的傳統球形關節。為了防止陶瓷磨損和破壞,在關節處加墊了灰色的絨布。人偶肢體運動的設計難度,反而賦予這些人偶與別的人偶截然不同的骨感。是的,骨感,這個時代是個講究骨感的時代。最好瘦到骨頭外露,骨頭與肌膚共處同一視覺。現實美女們沒有做到的事,Enchanted Doll做到了。要知道,人,是個二元生物,日常生活的人類大多處于二元的環境。白天替換黑夜,男人熱愛女人,皮膚覆蓋骨骼。皮膚是現象,骨骼是本質。皮膚是表面,骨骼是內里。Enchanted Doll則是現象與本質處于同一水平面:我們看到這些人偶的肌膚,更看到了她們的骨頭。這些骨頭提醒她們與人類的不同,她們處于生與死的邊界。她們既是死的(裸露的骨),又是活得(栩栩如生),她們是一群處于臨界點的生物。在人偶這里,表面與內里沒有任何對立,表面就是內里,內里就是表面。現象之后一無所有,這正是后現代哲學的核心所在。恰恰是這一點,構成Enchanted Doll的第二個魔法之源。
所有喜歡Enchanted Doll的人都喜歡這些人偶的眼睛。她們眼神瀲滟,似乎正在吁請著什么,又似乎要含淚哀訴。這眼神看上去更像開裂的晶瑩傷口,而非眼光本身。是的,看到這樣的眼神,沒有人不被喚起心中僅存的憐憫。這些小可憐兒,她們受傷了,且傷害很深。但是,她們受的是什么樣的傷害呢?縱觀這些十多厘米高的精靈,她們目光水靈,軀體粉紅,肌膚緋緋。這樣的眼神不是正常女性擁有的眼神,這樣的肌膚亦不是正常女性該本擁有的肌膚。只有在女性短暫的性高潮后,她們的眼神才會如此晶瑩,她們的肌膚才會靈光一現的呈現出如此令人心動的粉紅。女人最懂女人,設計師Marina Bychkova將女性千分之一秒的此時此地式的色情之美,完全潑灑至這些骨骼外露的人偶軀體之上,使得性與死亡這一古老聯盟再次以視覺的方式直接呈現在觀看者眼前。這是一種深邃的移情。我甚至懷疑設計師本人便是一位女同性戀者。由此可見,將色情之美琥珀一般凝固是Enchanted Doll在揮舞它的第三個魔法之杖。
有人驚嘆Enchanted Doll那些綴滿了珠寶的頭飾、衣物、鞋子。這有什么驚嘆的呢?它們沒有任何魔力。它們都是修飾物,是形容詞,是副詞,是脫衣舞娘的道具。當巴特感嘆法國脫衣舞是性的祛魅時,他不曾看到這些人偶。這些人偶實實在在的在召喚性,敘述性,吁請性,并言說著性本質:虐與被虐。即若脫掉最后一層衣服,她們仍舊穿著比香水更為曼妙的性與死亡的混搭之衣。她們是色情本身。Enchanted Doll是縮微版的性傳奇。我相信,所有的Enchanted Doll的持有者,給這些人偶穿衣服、脫衣服之際所享受到的快感,不下于觀看任何一場脫衣舞娘的精彩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