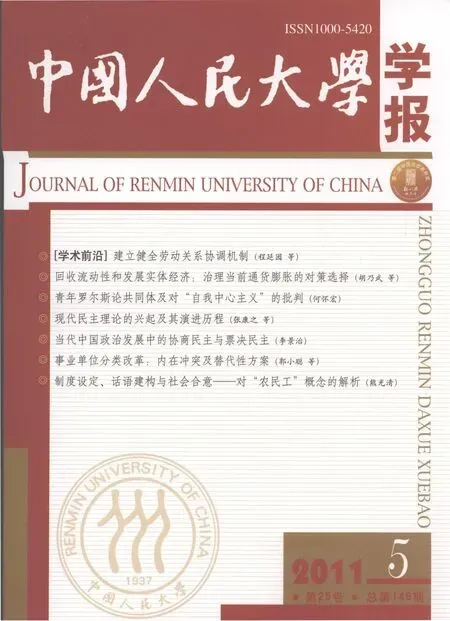韓非子與現(xiàn)代性——一個(gè)綱要性的論述*
白彤東
一、韓非子的時(shí)代:中國向“現(xiàn)代化”之轉(zhuǎn)變?
傳統(tǒng)中國哲學(xué)的合法地位是一個(gè)在當(dāng)代中國哲學(xué)界存在廣泛爭(zhēng)議的問題。有些人承認(rèn)傳統(tǒng)中國哲學(xué)與西方哲學(xué)不同,但為了論證前者的重要,他們指出它是哲學(xué),只不過是不同于西方哲學(xué)的獨(dú)特哲學(xué)傳統(tǒng)。但是,一些批評(píng)者常常反駁說,中國思想只是不同于西方近現(xiàn)代思想,而與古代西方思想非常相似,比如天人感應(yīng)思想與西方中世紀(jì)的思想。由此,中西思想之分就被描繪成了古今思想之別,并且,基于一種進(jìn)步觀念,中國思想(因?yàn)樗徽J(rèn)為屬于古代)也因此被貶低。當(dāng)然,有趣的是,也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和言必稱希臘與經(jīng)學(xué)的中國的施斯特勞斯主義者中的一些人,在以古今之分來解釋中西之別的同時(shí),試圖以論證古優(yōu)于今來為中國哲學(xué)辯護(hù)。在其他地方,筆者批評(píng)了基于未經(jīng)哲學(xué)反思的進(jìn)步觀對(duì)古代思想的貶低,以及我們?cè)谡務(wù)撝形髦畡e時(shí)常有的大而化之的傾向。筆者同樣也不同意那種“反動(dòng)的”(對(duì)外來壓力的反動(dòng)的)對(duì)古代的盲目推崇。不過,這篇文章的重點(diǎn)并不在于直接處理這些大問題,而是要通過對(duì)韓非子及其所處時(shí)代的一些初步研究來展示:第一,在所謂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中國已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經(jīng)歷了向“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變。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的諸子百家中很多學(xué)派實(shí)際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應(yīng)對(duì)現(xiàn)代性問題,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可能并沒有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第二,與其他同時(shí)代的思想家相比,由于韓非子最好地理解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變的性質(zhì),所以他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gè)“現(xiàn)代”思想家。如果這些猜測(cè)成立的話,那么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的“古代”中國思想可以很容易地與現(xiàn)代相關(guān),因?yàn)槟菚r(shí)的思想家和我們都在處理一樣的問題,即現(xiàn)代性問題。這些討論也會(huì)加深我們對(duì)現(xiàn)代性本質(zhì)的理解。第三,如果這種關(guān)聯(lián)成立,那么,通過對(duì)韓非子的批評(píng),我們也許能夠發(fā)現(xiàn)今天一些主流思想的問題。
韓非子生活在戰(zhàn)國末期。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充斥著社會(huì)與政治上的混亂和轉(zhuǎn)變。在這一時(shí)代之前的西周的政治架構(gòu)是一個(gè)封建的、金字塔般、擴(kuò)張的系統(tǒng)。周王(尤其是最初幾代的周王)分封(“封土建國”)他們的親戚、忠實(shí)和能干的臣下(很多人同時(shí)也是周王的親戚)、前朝的貴族等。這些人成為他們被分封的諸侯國的統(tǒng)治者。這些諸侯國中的一些是在周帝國的邊遠(yuǎn)地帶,因此他們可說是向這些“蠻夷”之地的軍事殖民。[1](P57)這些事實(shí)上的殖民地的建立有助于帝國勢(shì)力的擴(kuò)張。當(dāng)這些諸侯國通過蠶食其周圍的“蠻夷”之地得以擴(kuò)張后,它們的統(tǒng)治者常常會(huì)做與周王類似的事情,即分封他們的親戚與親信。就周帝國來說,周王統(tǒng)領(lǐng)諸侯,諸侯統(tǒng)領(lǐng)大夫,大夫統(tǒng)領(lǐng)家臣,而家臣統(tǒng)治他們屬地的民眾。因此,在每個(gè)層級(jí)上都是一個(gè)主子統(tǒng)領(lǐng)有限的臣屬。這一現(xiàn)實(shí)使得統(tǒng)治者通過個(gè)人影響和以宗法為基礎(chǔ)的禮俗規(guī)范來統(tǒng)治成為可能。但是,也許是因?yàn)樽谧宓募~帶經(jīng)過幾代以后被削弱,而更可能是因?yàn)橐蝾I(lǐng)土擴(kuò)張和人口增長(zhǎng)使得禮俗不能再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用,并且整個(gè)周帝國已經(jīng)擴(kuò)張到當(dāng)時(shí)的極限從而使得內(nèi)斗變得很難避免,所以這種等級(jí)、宗法系統(tǒng)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漸趨瓦解。在春秋時(shí)代,與從前不同,周王只被給予了名義上的尊重,他實(shí)質(zhì)上變成了諸侯之一,并且是實(shí)力很弱的一個(gè)。諸侯國的疆界不再被尊重,通過吞并戰(zhàn)爭(zhēng)七雄終于產(chǎn)生,也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的戰(zhàn)國時(shí)代。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諸侯國乃至后來七雄的統(tǒng)治者不得不直接統(tǒng)治領(lǐng)土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存亡以及這些君主在其國內(nèi)的存亡完全依賴于他們的實(shí)力。
上述這種轉(zhuǎn)變與歐洲從中世紀(jì)到現(xiàn)代的轉(zhuǎn)變有很多奇妙的相似之處。歐洲中世紀(jì)的政治架構(gòu)也是封建的、金字塔般的,每一級(jí)都處于小國寡民的狀態(tài),其約束方式也是宗法。但是,這一架構(gòu)在歐洲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變中也漸趨瓦解了,從中產(chǎn)生的廣土眾民的國家試圖通過戰(zhàn)爭(zhēng)獲得統(tǒng)治地位。當(dāng)然,中西的轉(zhuǎn)變還是不同的。比如,歐洲中世紀(jì)以前有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這給予他們的轉(zhuǎn)型以獨(dú)特的哲學(xué)、政治、文化資源。與春秋戰(zhàn)國時(shí)的中國不同,歐洲作為一個(gè)整體也沒有“天下共主”式的對(duì)自身文明的統(tǒng)一和連續(xù)的想象。中世紀(jì)歐洲也沒有世俗君主享有如周王那樣高和長(zhǎng)久穩(wěn)定的地位。教皇的位置相對(duì)穩(wěn)定,但其是否有公認(rèn)的天下共主的地位是有爭(zhēng)議的。中國的轉(zhuǎn)變的一個(gè)驅(qū)動(dòng)力量是農(nóng)業(yè)革命,這使得它也許不像西方轉(zhuǎn)變之始的商業(yè)革命,并且也肯定遠(yuǎn)不如西方轉(zhuǎn)變后期的工業(yè)革命那么劇烈。歐洲在向現(xiàn)代化轉(zhuǎn)變的同時(shí)伴有領(lǐng)土擴(kuò)張(移民與殖民),而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華夏文明已經(jīng)基本達(dá)到了當(dāng)時(shí)條件允許的領(lǐng)土界限。歐洲的“春秋戰(zhàn)國”也沒有能夠達(dá)到中國所達(dá)到的統(tǒng)一,盡管它們確實(shí)成功地打了兩場(chǎng)“世界”大戰(zhàn)和很多較小規(guī)模的戰(zhàn)爭(zhēng)。但是,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與西方現(xiàn)代化的轉(zhuǎn)變的相似性是清楚和深刻的。與封建制度一起消失的是貴族階級(jí)和他們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土地的貴族專有繼承和舊有的公田系統(tǒng)被廢除,土地自由買賣隨之興起。在西方則出現(xiàn)了臭名昭著的英國圈地運(yùn)動(dòng),貴族禮法的消逝也帶來了相應(yīng)的種種變化。比如,錢穆先生指出,與封建等級(jí)搖搖但未墜的春秋時(shí)代的戰(zhàn)爭(zhēng)相比,戰(zhàn)國時(shí)代的戰(zhàn)爭(zhēng)是殘忍與丑惡的。[2](P88-89)軍隊(duì)被平民化了,貴族的行為準(zhǔn)則也消逝了。戰(zhàn)爭(zhēng)服務(wù)于對(duì)資源的爭(zhēng)奪,并成為以砍腦袋為目標(biāo)的殘忍的“競(jìng)技”運(yùn)動(dòng)。
總而言之,中國從西周到春秋戰(zhàn)國之變與西方從中古到近現(xiàn)代的變化有所不同,但它們又有著不可否認(rèn)的相似性。如果西方的轉(zhuǎn)變被稱作“現(xiàn)代化”的話,那么這種相似就意味著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已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化。這一猜測(cè)也許會(huì)讓我們重新審視現(xiàn)代化,理解現(xiàn)代性和古今之別的本質(zhì)。在中國與歐洲的封建制中,在它們的金字塔的每一層級(jí)上,都只有常常是由宗法關(guān)系組織起來的幾百或幾千個(gè)人的共同體。也就是說,每一級(jí)都是一個(gè)實(shí)質(zhì)上的寡民之小國,或“高度同質(zhì)的熟人共同體”。而在現(xiàn)代化轉(zhuǎn)變之后出現(xiàn)的國家都是廣土眾民的陌生人社會(huì)。這似乎是個(gè)不重要的變化,但在政治上大小很重要。比如,當(dāng)一個(gè)共同體很小(“小國寡民”)的時(shí)候,基于一種對(duì)善的整全和相互分享的理解的道德和行為準(zhǔn)則是可能的,但是,當(dāng)這個(gè)共同體太大以至于不應(yīng)再被稱作共同體的時(shí)候,除非使用行之有效的壓制手段,否則這種道德與準(zhǔn)則作為獨(dú)尊的整合社會(huì)的紐帶不再普遍適用,因而在非壓制的情形下價(jià)值多元就不可避免。這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gè)基本事實(shí),一個(gè)為一些西方近現(xiàn)代思想家和韓非子所共同把握的事實(shí)。①關(guān)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如何理解多元性與共同體大小的關(guān)系,參見周濂:《政治社會(huì),多元共同體與幸福生活》,載《第12屆中國現(xiàn)象學(xué)年會(huì)會(huì)議論文》;周濂:《最可欲的與最相關(guān)的——今日語境下如何做政治哲學(xué)》,載《思想》第8輯,237~253頁,臺(tái)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2008。我們這里的論斷并不是要否認(rèn)韓非子與現(xiàn)當(dāng)代自由主義者的分歧,這在下文會(huì)有論述。這里,我們的問題就變成:什么可以替代道德成為一個(gè)國家的黏合劑?這是一個(gè)西方近現(xiàn)代與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shí)的思想家們都努力回答的問題。一個(gè)相關(guān)的共同問題是:當(dāng)金字塔式的封建架構(gòu)消失后,新的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其統(tǒng)治階層如何產(chǎn)生?對(duì)這個(gè)問題的回答,西方思想家(比如支持平等和大眾教育的啟蒙思想家)和古代中國思想家(比如認(rèn)識(shí)到所有人潛能上平等和支持某種形式的大眾教育的儒家)似乎也很相像:在“現(xiàn)代”條件下,我們需要一種向上的可流動(dòng)性,使得以前的平民成為官僚(“士”),并在這個(gè)階層中進(jìn)一步升遷成為可能。但是,這些思想家對(duì)如何實(shí)現(xiàn)這種向上流動(dòng)性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韓非子反對(duì)儒家教育,而偏向于以軍事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基礎(chǔ)的賢能政治。因此,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中國思想家與西方近現(xiàn)代思想家在思想上的相似也許反映了他們面對(duì)類似問題的事實(shí)。比如,筆者曾論述過,《老子》與盧梭都看到了現(xiàn)代化的問題,認(rèn)為現(xiàn)代化的結(jié)果會(huì)很糟糕,并因此都呼吁回到小國寡民的時(shí)代。[3](P481-502)又如,中國曾經(jīng)被一些歐洲啟蒙乃至近代思想家當(dāng)做他們的理想和社會(huì)政治變革的方向的原因,可能不僅僅是這些思想家用曲筆的方式,借這個(gè)中國來批評(píng)現(xiàn)實(shí),而是由于春秋戰(zhàn)國之變與歐洲現(xiàn)代化之間的相似,使得哪怕是簡(jiǎn)單化甚至被曲解的中國思想也引起了歐洲思想家的共鳴。②Hobson,John M.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這是最近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的一項(xiàng)有趣工作。謝文郁也指出了中國思想對(duì)康德的可能影響,參見謝文郁:《康德與君子》(未刊稿)。我們研究這個(gè)問題不應(yīng)該只是為了一種文化自尊,而是應(yīng)該通過揭示其背后的、深刻的原因,加深對(duì)現(xiàn)代性以及現(xiàn)代各種制度安排的理解。
簡(jiǎn)而言之,我們這里的一個(gè)判斷是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所經(jīng)歷的可能是西方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預(yù)演。這個(gè)判斷預(yù)設(shè)了對(duì)現(xiàn)代性的一種理解,即“古代”到“現(xiàn)代”之變化的實(shí)質(zhì)是(或部分地是)建立在血緣繼承基礎(chǔ)上的、在每一層級(jí)上都是高度同質(zhì)的小國寡民的熟人共同體的封建等級(jí)制的瓦解與異質(zhì)的廣土眾民的陌生人社會(huì)的出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在這種轉(zhuǎn)變下的各種政治、社會(huì)問題。有些學(xué)者可能會(huì)完全不接受我們對(duì)現(xiàn)代性的這一理解,而認(rèn)為現(xiàn)代性應(yīng)該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平等、自由、權(quán)力合法性等觀念,從而否定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所經(jīng)歷的變化是現(xiàn)代化。這里,我們首先要澄清,上面那些大膽的論斷并不預(yù)設(shè)中西的現(xiàn)代性沒有任何區(qū)別,也不否認(rèn)中西間的這種巨大轉(zhuǎn)變有其微妙甚至(時(shí)間與地域上)混亂的地方,它只是預(yù)設(shè)中西的現(xiàn)代性有足夠的類似。比如,上面已經(jīng)提到,西方的現(xiàn)代性有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資源(比如自由、民主等觀念),而中國沒有。但是,即使就這些差別本身而言,我們還要考慮,它們中的一些可能只是在深層相似上的表面差別而已。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在西方現(xiàn)代化過程中也是逐漸出現(xiàn)的,而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shí)的土地自由買賣也是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中市場(chǎng)化的表現(xiàn)。平等本身是一個(gè)復(fù)雜的概念。先秦儒家大多認(rèn)為人們?cè)跐撃苌鲜瞧降鹊?或至少應(yīng)該是“有教無類”。這與西方啟蒙運(yùn)動(dòng)以來的大眾教育思想相呼應(yīng)。韓非子也提出了法律面前(除了人主之外)人人平等的想法,而西方憲政之初,君主也常常是不受法律約束的。基于血緣的貴族制在中國的瓦解也造成了人們職業(yè)選擇上的自由,而我們下面將討論的韓非子對(duì)思想多元性的理解也觸及了自由問題。關(guān)于權(quán)力合法性的問題,在“古代”(歐洲的中古與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之前),統(tǒng)治者權(quán)力也有其合法性基礎(chǔ),只不過它是訴諸某種神意。權(quán)力合法性的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在不再訴諸這種神意,或用韋伯的術(shù)語來說,現(xiàn)代經(jīng)歷了去魅的過程。西方是以社會(huì)契約、民主政治來表達(dá)這種變化的。在中國,西周時(shí)“天命”已經(jīng)被“人化”了、民意化了,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泰誓》),而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進(jìn)一步發(fā)揮了這種權(quán)力合法性來自于滿足人民物質(zhì)與精神需要的思想。①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的政權(quán)合法性雖然強(qiáng)調(diào)民意,但它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精英作用,它對(duì)民意的理解(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人民的物質(zhì)與倫常需要)也與當(dāng)代西方民主國家的理解不同。參見白彤東:《舊邦新命:古今中西參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學(xué)》,21~94頁,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這些現(xiàn)代化的表現(xiàn)和處理方式雖然不同,但它們可能只是面對(duì)類似問題時(shí)的不同處理方式,而不是問題不同、話語不同的不可通約的理論與觀念。另外,作為西方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重要的、看似獨(dú)特的世俗化(去基督教化)過程,也許是上述一些根本變化的合力(新的權(quán)力基礎(chǔ)與權(quán)力架構(gòu)的要求、不可避免的多元化、民眾教育的提高等)外加西方中古之現(xiàn)實(shí)的結(jié)果(宗教及其組織是維系歐洲中古封建制的重要紐帶),而不是現(xiàn)代化的本質(zhì)特征。
如果上面的理解是對(duì)的,那么說中國春秋戰(zhàn)國的思想在古今之分上屬于古代就是錯(cuò)的。在這個(gè)意義上,黑格爾和韋伯對(duì)中國古代思想的評(píng)判就也是錯(cuò)誤的。而將中國古代思想標(biāo)為“兩千年封建專制的糟粕”就更糟糕。我們先撇開“糟粕”這個(gè)情緒性字眼不談,中國秦以降的兩千年的歷史既不封建也不純?nèi)皇菍V频摹"诖呵飸?zhàn)國之后的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專制君主(皇帝)與士人精英階層的張力的結(jié)果。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雅思貝爾斯這樣的思想家把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的思想和與其近乎同時(shí)的古希臘、古印度思想放到一塊稱之為“軸心時(shí)代”的思想[4],這種說法也忽視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與其他思想的一個(gè)關(guān)鍵不同,即中國先秦思想是關(guān)于現(xiàn)代化的思考,因而已經(jīng)偏離了古代思想的范疇。在這個(gè)意義上,同情儒家的當(dāng)代學(xué)者,如羅哲海,也以軸心時(shí)代的思想來理解儒家[5],因而也就犯了與雅思貝爾斯一樣的錯(cuò)誤。從春秋以降,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思想與實(shí)踐可能一直在處理現(xiàn)代性問題,并對(duì)其提出不同解決方案。在這個(gè)意義上,傳統(tǒng)中國政治理論與實(shí)踐的歷史不但不是糟粕,還是我們當(dāng)今反思現(xiàn)代性問題的重要資源。
韓非子可能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第一個(gè)意識(shí)到并明確闡明時(shí)代變化本質(zhì)的思想家。在這個(gè)意義上,他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gè)現(xiàn)代思想家。因此,對(duì)他思想的研究也就對(duì)現(xiàn)代性諸問題的思考有著重要意義。
二、韓非子的政治哲學(xué)?
在考察《韓非子》之前,讓我們首先回應(yīng)一個(gè)問題:它是不是一部政治哲學(xué)著作?其作者是不是一個(gè)政治哲學(xué)家?海外學(xué)者A.C.Graham將韓非子思想描述為“非道德的統(tǒng)治國家之技藝的科學(xué)”(amoral science of statecraft),而Paul Goldin批評(píng)了這個(gè)說法[6],并正確地指出了韓非子的著作與西方政治哲學(xué)著作的區(qū)別。比如,韓非子有時(shí)給統(tǒng)治者甚至大臣教授無恥的自我保護(hù)的技巧,而這種厚黑之學(xué)在霍布斯與洛克的著作里似乎是找不到的。但是,在另一部通常被認(rèn)為是政治哲學(xué)著作(有些人會(huì)說它是西方近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的奠基之作)中,即在馬基雅維利的《君子論》中,我們可以找到類似的教授。在其他一些西方政治哲學(xué)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類似于上述的厚黑教導(dǎo)的蹤跡。
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韓非子》及中國思想史上的很多文獻(xiàn)確實(shí)與西方傳統(tǒng)中的政治哲學(xué)文獻(xiàn)不同。前者常常不是為了純粹的理論討論而寫,而是對(duì)統(tǒng)治者的具體建議或是與其他大臣與政策顧問的爭(zhēng)論之記載。錢穆先生指出,在秦以后的時(shí)代,也許是因?yàn)槿寮业南蛏狭鲃?dòng)思想的貢獻(xiàn),有思想的學(xué)人常常成為統(tǒng)治精英的一部分。[7](P21)這與春秋戰(zhàn)國之前和中世紀(jì)(乃至近現(xiàn)代的大部分時(shí)期)的歐洲不同。因此,過去中國的知識(shí)精英就可以把他們的政治思想和理論付諸實(shí)踐,而沒有太多需要將它們變成脫離現(xiàn)實(shí)的理論。錢穆先生沒有指出的一個(gè)事實(shí)是,中國士人于政治的深深卷入,也使得他們沒有理論探討所必需的閑暇。實(shí)際上,盧梭的一段話可以用來支持錢穆先生的說法:“人們或許要問,我是不是一位君主或一位立法者,所以要來談?wù)撜文?我回答說,不是;而且正因?yàn)槿绱?我才要來談?wù)撜巍<偃缥沂莻€(gè)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就不應(yīng)該浪費(fèi)時(shí)間來空談要做什么事了;我會(huì)去做那些事情,否則,我就會(huì)保持沉默。”[8](P46)
與此不同,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政治思想家居于政治權(quán)力的核心。這一點(diǎn)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已經(jīng)發(fā)生了。比如,西方也許與權(quán)力核心最接近的思想家之一馬基雅維利,他的政治地位也不及身為韓國諸公子的韓非子。據(jù)《史記》載:“秦王見《五蠹》、《孤憤》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對(duì)于這種政治地位,馬基雅維利和其他西方政治哲學(xué)家恐怕難以企及。
當(dāng)然,這一辯護(hù)只是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很多思想家的作品與西方不同,并暗示,如果被剝奪了參與現(xiàn)實(shí)政治的機(jī)會(huì),中國思想家也會(huì)寫出與西方政治哲學(xué)著作相似的作品,而它并沒有說明中國傳統(tǒng)中的這些文獻(xiàn)是政治哲學(xué)文獻(xiàn)。但是,如果我們把哲學(xué)當(dāng)做反思的工作,從而把政治哲學(xué)當(dāng)做對(duì)政治事務(wù)的系統(tǒng)反思,我們可以看到,《韓非子》中確實(shí)包含有這樣的思考。韓非子和傳統(tǒng)中國的很多其他政治思想家都有著在最高層的政治實(shí)踐,并因而可以用之以對(duì)政治進(jìn)行反思,這就有可能彌補(bǔ)他們于建立在閑暇之上的思辨的缺失。筆者并非要否認(rèn)《韓非子》包含厚黑術(shù),實(shí)際上,這部書很可能是這類書籍的上乘之作。筆者在這里只是論證它包含應(yīng)當(dāng)是屬于政治哲學(xué)層面的思想。
三、韓非子之死與“法家”思想的命運(yùn)
另一個(gè)對(duì)韓非子思想的重要性的攻擊集中在韓非子及分享他的想法的人與國家的命運(yùn)上。盡管韓非子對(duì)政治有著深刻的理解,但最終還是成了昔日同窗李斯之政治迫害的犧牲品。反諷的是,據(jù)《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李斯說服秦王逼迫韓非子自殺的論辯有著儒家而非法家的味道。看起來,李斯并不相信韓非子所論證的,統(tǒng)治者可以通過賞罰使臣下變得忠誠。李斯自己也最終被秦二世殘酷殺害。通過韓非子支持的政策來使秦國強(qiáng)大的關(guān)鍵人物商鞅也最終不得好死,通過實(shí)行這種政策而最終統(tǒng)一中國的秦朝也沒有延續(xù)多久。所有這些歷史事實(shí)被那些不喜歡韓非子思想的人(比如儒家)用來說明韓非子政治思想的邪惡本質(zhì)與不足。①比如,明代的張鼎文寫道:“非之書未行,止于獄司;斯之術(shù)已用,遂至車裂。天道之報(bào)昭昭哉!”參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122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筆者雖然高度同情儒家的政治哲學(xué),但是我不得不說,這種對(duì)韓非子及其政治哲學(xué)的批駁太過廉價(jià)。韓非子在《難言》、《說難》、《孤憤》諸篇中展示了他對(duì)能讓君主聽從正確建議的困難的深刻理解,因此,有些人就說他不能遵循他自己的哲學(xué)。②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余獨(dú)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后人趙用賢也指出:“韓非子非死于不自免于說難,而死于悖其術(shù)。”(陳奇猷,前引書,1226頁)清代梅曾亮指出,韓非子不知道他不應(yīng)該挑明君主不想為人所知之術(shù),因而招致身死。(同上,1257頁)但是,他的悲劇結(jié)局也許只是展示了“得君行道”的巨大困難,這一困難在某些情形下超越了此種技藝的大師的掌控。③王世貞指出,管仲與韓非的命運(yùn)之別在于時(shí)機(jī)的不同。(陳奇猷,前引書,1228頁)一般來講,一個(gè)人不能遵循自己的哲學(xué)雖然很反諷,但并不能證明其哲學(xué)是錯(cuò)誤的。至于秦朝的命運(yùn),也許是秦朝所帶來的政治變動(dòng)太過劇烈,以至于不能為它在短時(shí)間內(nèi)消化。“暴秦”確實(shí)在它建立不久就被推翻了,但起義軍及漢朝早期的重回封建的努力也迅速失敗,被修正的秦制后來實(shí)際上也為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所大多遵循。事實(shí)上,一些看起來是儒家的政治安排,比如科舉,可能也包含著韓非子的遺產(chǎn)。過去很多思想家對(duì)韓非子的政治哲學(xué)及其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的角色已經(jīng)多有反思,我們今天討論韓非子的哲學(xué)及其在傳統(tǒng)中國的命運(yùn)時(shí),也應(yīng)繼續(xù)這種心平氣和的思考。
四、韓非子:第一個(gè)現(xiàn)代思想家?
下面,我會(huì)給出與現(xiàn)代性問題相關(guān)的韓非子一些主要思想的概述。首先,如前所述,我認(rèn)為現(xiàn)代性的一個(gè)關(guān)鍵特征是:人口膨脹、封建諸侯向“蠻夷之地”擴(kuò)張接近極致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對(duì)日漸有限的資源的爭(zhēng)奪,導(dǎo)致封建的、金字塔般的政治結(jié)構(gòu)瓦解,替代它的是廣土眾民的大國。在著名的《五蠹》篇里,韓非子展示了他對(duì)這些變化的理解。比如,他指出“古”、“今”的一個(gè)關(guān)鍵區(qū)別在于,“古者……人民少而財(cái)有余,故民不爭(zhēng)。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cái)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故民爭(zhēng),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因此,“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知之患也”(《韓非子·王蠹》)。可見,韓非子的關(guān)注焦點(diǎn)明顯不是道德是否存在與真實(shí),而是道德是否有效。事實(shí)上,他承認(rèn)我們?nèi)祟愂悄軌蛏拼说摹K赋?“穰歲之秋疏客必食。”但在這句話前,他說:“饑歲之春幼弟不餉。”(《韓非子·王蠹》)在這一章和其他章節(jié)里,韓非子有力地展示了道德的無效,并論述說,為了管理民眾的行為,法律方式和制度安排是關(guān)鍵,而專注于道德培養(yǎng)是危險(xiǎn)的誤導(dǎo)。為了讓法律與制度的安排有效,民眾必須被平等地對(duì)待,而他們的貴賤與親疏不應(yīng)被考慮。官爵的授予應(yīng)該純粹基于一個(gè)人在農(nóng)、戰(zhàn)中的成就。通過這些,韓非子支持一個(gè)建立在平等基礎(chǔ)上的國家(君王除外),倡導(dǎo)基于具體、實(shí)在的成就、允許向上流動(dòng)性的賢能政治。用這些成就而不用道德來衡量賢能是因?yàn)?道德不僅無效,而且還很混亂,會(huì)被任意解釋,從而也就制造了不同的權(quán)力中心而使國家不穩(wěn)定。這里包含著韓非子另外一個(gè)反對(duì)儒家德治的論辯。道德在大的共同體里不可避免地會(huì)變得多元,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變得無效。在《顯學(xué)》一章中,韓非子指出,孔子、墨子死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儒墨兩家“俱道堯舜”,但是“取舍不同”,給出的政治建議常常截然相反。可是,我們無法審核三千年以前堯舜的原意,而在這種無參驗(yàn)的情況下,我們也無法斷定哪一家、哪一派的解讀是對(duì)的。韓非子認(rèn)為“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韓非子·王蠹》),它(比如儒家的道德形上學(xué)或后來的宋明理學(xué)乃至新儒家所看重的心性之學(xué))無法“為眾人法”,因?yàn)椤懊駸o從識(shí)”這些“上智所難知”的道德論說。與此相對(duì),智慧德行有如孔子這樣的“天下圣人”不過有“服役者七十人”而已,而“下主”的魯哀公“南面君國,境內(nèi)之民莫敢不臣”(《韓非子·王蠹》)。
由上述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韓非子有很多洞見是為后來的西方近現(xiàn)代乃至當(dāng)代的思想家所分享的。他給出了大的共同體里道德價(jià)值多元之不可避免的原因,也理解使用簡(jiǎn)單與普遍可理解的東西(比如賞罰)的必要。①參見Bentham,Jerem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 les of M orals and Legislation.New York:Hafner Press,1949。該書開宗明義,認(rèn)為痛苦和快樂是人類的唯一的和最高的主子。由于他有這種理解,他可以說與當(dāng)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爾斯是比肩的。②比如,Raw ls,John.Political L 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在該書中羅爾斯給出了他的多元主義論述。至于他們之間的區(qū)別,我下面會(huì)加以論述。與之相對(duì),很多西方近現(xiàn)代思想家簡(jiǎn)單地歌頌?zāi)切┩ǔUJ(rèn)為是卑微的東西(比如短期的物質(zhì)利益),在打倒老上帝的同時(shí)又立起了新上帝,而并沒有理解我們?yōu)槭裁床坏貌磺笾谒鼈兊脑颉_@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進(jìn)而否認(rèn)價(jià)值的實(shí)在。與他們的意見相左,但可以說與他們一樣頭腦簡(jiǎn)單的是很多現(xiàn)代道德保守主義者。他們看到了古人競(jìng)于道德而今人爭(zhēng)于氣力,但是并沒有明白這個(gè)變故的深刻理由。他們哀嘆現(xiàn)代人的道德淪喪、道德相對(duì)主義、道德虛無主義,并攻擊那些他們以為推動(dòng)和歌頌了這些潮流的近現(xiàn)代思想家,好像這些所謂的推動(dòng)者導(dǎo)致了今人的道德淪喪。這反映了思想者的傲慢,以為思想者在這個(g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影響。基于這種傲慢,這些保守主義者似乎覺得,如果這些“推動(dòng)者”能被保守主義者的圣戰(zhàn)所摧毀的話,如果我們重新培養(yǎng)出古代的紳士階層的話,那么世界的秩序就會(huì)得以重建。這兩類人雖然各執(zhí)一端,但是在對(duì)古今之別之實(shí)質(zhì)的無知上卻是共同的。
當(dāng)然,韓非子對(duì)道德多元不可避免的解釋與當(dāng)代自由主義者中有頭腦的思想家的理解還是有區(qū)別的。韓非子的論述只給出了道德多元的現(xiàn)實(shí)條件,而這些條件的充分性有待考察。更重要的是,他沒有給出多元性的可欲性。與此相對(duì),現(xiàn)當(dāng)代自由主義者強(qiáng)調(diào)自由選擇的可欲性,而現(xiàn)代普及教育也增大了自由選擇的現(xiàn)實(shí)可能性。這種自由選擇的可欲性是多元性的可欲性的一個(gè)基礎(chǔ)。換言之,對(duì)自由主義者來講,統(tǒng)一思想是不可欲的,而韓非子的觀點(diǎn)是它既不可能也不有效。但是,韓非子還是認(rèn)為思想的多元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對(duì)多元性的承認(rèn)完全可以到此為止。這種基于無奈的承認(rèn)可能會(huì)在多元主義與道德一元的信念之間構(gòu)筑一座橋梁。
有人會(huì)反駁說,大國里解決思想多元問題可以由極權(quán)主義來實(shí)現(xiàn)。但是,韓非子本人似乎并不覺得這是可能的。他關(guān)注的不是統(tǒng)一思想,而是統(tǒng)治者需要用那些每個(gè)人都不得不聽從的東西(即賞罰)來控制所有人。他關(guān)注的是控制人的可以參驗(yàn)的行為,但并不在意控制人內(nèi)在的想法。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韓非子與現(xiàn)當(dāng)代自由主義者又有不同,即從思想的多元性出發(fā),韓非子并沒有給自由與權(quán)利留下太多空間。不過,如果我們想想西方近代早期政治哲學(xué)家,比如馬基雅維利①馬基雅維利是不是一個(gè)現(xiàn)代思想家、是不是第一個(gè)現(xiàn)代思想家,這是一個(gè)有爭(zhēng)議的問題。參見Ivanhoe.“Han Fei Zi and Mo ral Self-Cultivation”,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orthcoming,2011。和霍布斯,對(duì)控制的強(qiáng)調(diào),他的這種取向也許會(huì)顯得不那么扭曲。更重要的是,他確實(shí)有一個(gè)合理的擔(dān)憂:價(jià)值的多元會(huì)帶來國家的不穩(wěn)定。他的這一擔(dān)憂似乎也為他所處的時(shí)代乃至中國及世界歷史的大部分現(xiàn)象所支持。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不是韓非子,而是自由主義思想家欠我們一個(gè)解釋,解釋我們?yōu)槭裁船F(xiàn)在可以同時(shí)擁有多元性和穩(wěn)定。這恰恰是羅爾斯在他的晚期哲學(xué)里試圖回答的問題。[9]但是,他的回答是否充分是可以考究的。比如,羅爾斯也許忽視了一點(diǎn),即現(xiàn)代技術(shù)的發(fā)展(比如通訊)使得國家緊緊控制地方乃至個(gè)人事務(wù)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很反諷的是,當(dāng)今自由民主國家所享有的自由與多元也許是建立在韓非子渴望的但是無法想象的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基礎(chǔ)上的。沒有集權(quán),也沒有自由。因此,自由的理念可能確實(shí)是西方現(xiàn)代性的一個(gè)獨(dú)立貢獻(xiàn),但是我們可以擁有它這個(gè)事實(shí)是對(duì)韓非子的駁斥與辯白。只有在韓非子的擔(dān)憂被他所不能預(yù)見的技術(shù)發(fā)展所解決以后,他所忽視的自由才成為可能。當(dāng)然,在沒有自由民主的現(xiàn)代國家,它的集權(quán)與極權(quán)也超過了韓非子的想象。
與現(xiàn)當(dāng)代自由主義者不同,韓非子沒有給出對(duì)統(tǒng)治者(除了國家興亡之外)的任何制約。但是,與西方很多近現(xiàn)代思想家類似,韓非子為法律的絕對(duì)權(quán)威和法律面前(除統(tǒng)治者之外)人人平等辯護(hù),這為現(xiàn)代的憲政播下了種子。②像我前面提到的,西方憲政之初,有些君主也是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對(duì)韓非子與憲政主義的一般討論,參見Schneider,Henrique.“Legalism:Chinese-Style Constitutionalism?”,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orthcoming,2011。
五、韓非子、儒家以及韓非子與自由主義者邊緣化道德的問題
因?yàn)轫n非子的思想對(duì)我們理解現(xiàn)代性是如此關(guān)鍵,所以考察他的思想如何與其他學(xué)派的思想互動(dòng)就可能是一項(xiàng)卓有成效的工作。一個(gè)有趣且重要的問題是它與《老子》的關(guān)系問題,但本文會(huì)專注于韓非子與儒家政治哲學(xué)的關(guān)系問題。
與《老子》的世界觀一致,韓非子也論辯說統(tǒng)治者應(yīng)該遵循自然,人為的東西(包括儒家的道德)只會(huì)毀了一個(gè)國家。他也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在一個(gè)廣土眾民的國家里,基于微妙與深刻的哲學(xué)教導(dǎo)的道德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因此就不能成為統(tǒng)一國家的政治系統(tǒng)的基礎(chǔ)。也就是說,儒家建立道德國家的理想雖然美好,但是不切實(shí)際與無效的。因此,如果我們希望保持他思想的完整,就無法用儒家思想改造韓非子。但是,儒家思想里有無空間來采取韓非子的一些主張并加以修正呢?
筆者認(rèn)為,儒家不僅可能而且還有必要吸收韓非子的一些主張。如上所述,春秋戰(zhàn)國時(shí)的一個(gè)關(guān)鍵問題在于,基于出身的封建等級(jí)制趨于瓦解的背景下,該如何設(shè)計(jì)一個(gè)政體來直接管理領(lǐng)土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的國家。對(duì)于這個(gè)問題,儒家的解決是重建等級(jí)社會(huì),但是它不再基于出身與血緣,而是基于儒家道德(包括官員的能力)。但是,在韓非子看來,儒家德治或禮治的理想是建基于已經(jīng)消逝的政治現(xiàn)實(shí)之上的,無法滿足新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我想,儒家對(duì)這一挑戰(zhàn)可以有兩種回答。第一,儒家可以希望回到小國寡民時(shí)代,回到高度同質(zhì)化的熟人社會(huì)以便重建道德。但是,如果我們不認(rèn)為讓韓非子所處的或我們所處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回到小國寡民狀態(tài)是可能的或可欲的,并且如果我們想讓儒家的一套政治哲學(xué)在現(xiàn)有大多數(shù)國家都已經(jīng)是廣土眾民的現(xiàn)代世界還適用,我們就必須正面回應(yīng)韓非子的挑戰(zhàn)。我的一點(diǎn)初步的想法是儒家可以采納韓非子的一些處理廣土眾民的大國不可或缺的制度上與法律上的設(shè)計(jì)。比如,雖然在理想狀況下,孔子希望不用刑罰,但是在非理想的世界里,他并不反對(duì)刑罰的應(yīng)用。①《論語》2.3,12.19與13.6節(jié)和《大學(xué)》的第三章討論的是理想的或規(guī)范性的案例。而在13.3節(jié)中,孔子指出法律手段應(yīng)被禮樂所指導(dǎo),這就暗含了他并不反對(duì)應(yīng)用法律手段,可謂其在非理想世界中的態(tài)度。儒家不僅僅是被動(dòng)采納韓非子的制度設(shè)想,還可以在制度與法律之上給出儒家的道德指引,并在制度與法律之下(之外)建立道德以便支持制度的穩(wěn)固。這種道德建構(gòu)對(duì)大國的良好運(yùn)作會(huì)起到關(guān)鍵作用。
但是,這種儒家的改良與韓非子的一個(gè)基本判斷相違背。他認(rèn)為,在大國里倡導(dǎo)儒家價(jià)值就不可避免地毀了國家,其原因是價(jià)值多元和德治的無效。不過,也許有一種更薄版本的道德,它可以“薄”到讓持不同的整全的道德觀的人所采納,成為他們的“重疊共識(shí)”,它也不對(duì)民眾的道德心與智慧有過高的要求。儒家對(duì)日用人倫的很多考慮是可能符合這種設(shè)想的。比如,不管一個(gè)人的信仰如何,多數(shù)人可能會(huì)認(rèn)識(shí)到家庭穩(wěn)定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的好處,而家庭穩(wěn)定是儒家道德關(guān)心的一個(gè)核心問題。就韓非子的以上智之人難知的微妙之言來為眾人法的攻擊來說,從一開始,儒家就致力于發(fā)展出一些為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社會(huì)底層人士所能理解的實(shí)踐,而對(duì)這些民眾的要求,也常常不比韓非子承認(rèn)的豐年時(shí)候款待陌生人的愛心高太多。
如此理解道德及其作用,也會(huì)對(duì)西方自由主義者(比如羅爾斯)的一個(gè)想法構(gòu)成挑戰(zhàn),他們堅(jiān)持區(qū)分私德(古代人的道德)與公德(現(xiàn)代人的道德),堅(jiān)持將前者推到所謂背景文化里去。②對(duì)這個(gè)想法的一般性的批評(píng),參見Chan,Joseph.“Legitimacy,Unanimity,and Perfectionism”.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2000,29(1)。但是,從上面的理解出發(fā),我們可以論辯說,也許可以有更薄的、可以在公共領(lǐng)域里存在的“古人的”的道德,它不導(dǎo)致壓迫(與以賽亞·伯林所說不同)但又對(duì)國家的運(yùn)作很重要。儒家因素可以滲透到傳統(tǒng)的中國政治制度中,并且能為持有不同的整全觀念(比如佛道)的人們所接受這個(gè)事實(shí),也許就暗示著有些儒家因素是可以薄到足以成為擁有多元價(jià)值的民眾的“重疊共識(shí)”的。有如儒家因素也許修正了只用韓非子想法的局限,從而強(qiáng)化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一樣,發(fā)展類似的因素也許對(duì)今天自由民主社會(huì)的局限會(huì)有修正作用。
儒家對(duì)韓非子思想的另外一個(gè)重要的補(bǔ)充是關(guān)于政權(quán)合法性的問題。韓非子擔(dān)心穩(wěn)定問題,從而不支持多元。現(xiàn)代自由民主社會(huì)除了通過集權(quán)維護(hù)國家穩(wěn)定外,還通過民主選舉所表達(dá)的民眾認(rèn)可來維護(hù)穩(wěn)定。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也認(rèn)為民意的認(rèn)可是政權(quán)合法性的基礎(chǔ)之一。并且,通過士人對(duì)人主的監(jiān)督,我們也可能找到一個(gè)不通過國家興亡的激烈手段來淘汰不合格人主的辦法。這有可能反而促進(jìn)了政權(quán)的穩(wěn)定。
綜觀中國歷史,與韓非子的初衷相違,儒法互補(bǔ)可能是歷朝政府的指導(dǎo)哲學(xué)。比如,儒家從支持更適合小國寡民的舉孝廉到接受更適合大國的科舉就是對(duì)韓非子思想的一個(gè)整合的努力。傳統(tǒng)中國所采用的官僚體系源自于韓非子的設(shè)計(jì),但這個(gè)體系又有不可否認(rèn)的儒家色彩,不同的朝代也曾嘗試過不同的混合,有些混合的結(jié)果明顯是壞的。韓非子的強(qiáng)勢(shì)政府與儒家對(duì)道德的看重,有時(shí)候就混合成了比韓非子想要的更專制的政治制度,用韓非子的制度來控制韓非子并不太關(guān)心的思想。評(píng)估這些混合的好壞優(yōu)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政治史、儒法關(guān)系。這種評(píng)估工作,從我們對(duì)韓非子與現(xiàn)代性之間關(guān)系的論證中可以看出,還可能會(huì)為當(dāng)今世界政治制度的改良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1][2]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3]白彤東:“How to Rule without Taking Unnatural Actions(無為而治):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Laozi”.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9,No.4/October,2009,481-502.
[4]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 istory.Translated by M ichael Bullock.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 td,1953.
[5]Heiner Roetz.Confucian Ethics of the A xial A ge.A lbany,NY:Suny Press,1993.
[6]Paul Goldin.“Persistent M isconcep tions about Chinese‘Legalism’”.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orthcoming,2011.
[7]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
[8]Jean-Jacques Rousseau.On the Social Contract w ith Geneva M anuscript and Political Econom y.Edited by Roger D.Masters and translated by Judith R.Masters.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78.
[9]John Raw ls.Political L iberalism.New Yo 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