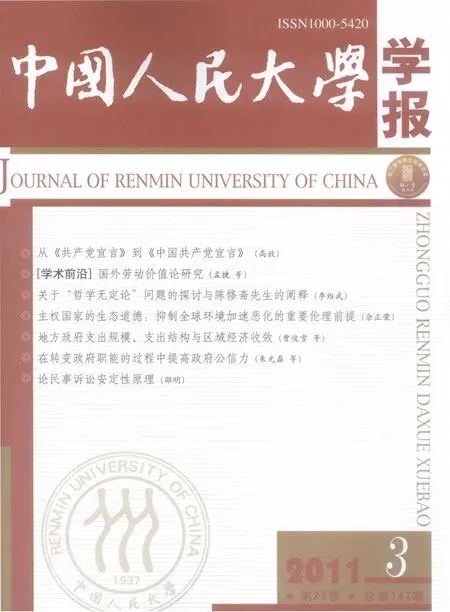從《共產黨宣言》到《中國共產黨宣言》——兼考證《中國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和譯者
高 放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來臨之際,我們重溫黨史上第一份文獻《中國共產黨宣言》很有意義。《中國共產黨宣言》是在1920年11月直接由《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催生的。這份文獻已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冊。[1](P547-551)以往學界對此不夠熟悉,研究不夠充分。現把我近年來學習心得寫出,并對其作者和譯者做些考證。
一、《中國共產黨宣言》的產生、內容、意義和欠缺
馬克思、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這篇劃時代的經典文獻,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于1848年2月24日在倫敦問世。這篇文獻(譯成中文約2.5萬字)第一次闡述了科學世界觀、歷史觀與社會觀,指明了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巨大進步作用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強調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發展規律,分析了當時歐美資本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發展態勢,提出了無產階級進行革命、奪取政權和建設新社會的任務,揭示了共產主義政黨的特點及與其他各類政黨的關系,劃清了科學共產主義與當時形形色色非科學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潮的界線,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①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ander Verinigt Eüch!”如果直譯應為“所有國家無產者,聯合起來”,我認為可意譯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無產者”狹義專指現代產業工人。1848年時只有西歐北美十幾個國家有“無產者”,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還沒有“無產者”。“勞動者”不僅包括工人和廣大體力勞動者,也包括腦力勞動者,還包括所有主要以勞動獲得報酬的人員。參見拙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74種中譯文辨析》,載《文史哲》,2008(2);《“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譯語可以改譯》,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8-03-17,《探索與爭鳴》,2009(2)。的戰斗口號。《共產黨宣言》由于飽含極其豐富的卓越思想,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具有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吸引力、影響力和號召力。
雖然在歐洲1848年革命失敗后的險惡環境中,共產主義者同盟被迫于1852年11月17日解散,但是《共產黨宣言》在19世紀50年代后卻連續不斷出版德文版并被譯為英、法、俄、波、意等國文字廣為傳播。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寫道:“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2](P256)也就是說,它已變成世界《共產黨宣言》了。
隨著19世紀末日本、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無產階級的出現,《共產黨宣言》也傳播到東亞并產生重大影響。1904年11月13日,日本《平民新聞》周刊第53號發表了堺利彥和幸德秋水從1888年英國人賽·穆爾從德文翻譯的英文版再轉譯為日文的《共產黨宣言》(第三章未譯)。1906年3月,堺利彥在他主編的《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再次刊登《共產黨宣言》全譯文(補譯了堺利彥和幸德秋水早先略去未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三章)。1907年即出版了該書日文單行本。同年,署名蜀魂的中國留日學生把該書譯為中文在東京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1908年1月,留日學生創辦的《天義》報第15期發表民鳴從日文翻譯的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寫的序言,同年2—5月該報第16—19期又連載民鳴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全文。同年,《天義》報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中譯本。這些在東京刊出和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文和中譯本,在中國知者甚少。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出現部分中譯文。如1919年4月6日《每周評論》第16號發表舍(即成舍我)摘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同年11月1日出版的《國民》雜志第2卷第1號刊出李澤彰摘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年底北大學生羅章龍從德文譯的《共產黨宣言》節本曾經有油印本流傳。到1920年8月,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了陳望道從日文本并且參照英文本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兩個月之內就印刷兩次,迅即售缺。隨后多處翻印,廣為流傳,快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在《共產黨宣言》的直接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宣言》應運而生。中國第一批共產黨人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俞秀松、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楊明齋,共八個人,1920年8月間,在上海組成中國共產黨組織,隨即發展到十幾個人,11月制定了一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的文件。這篇宣言只有大約2200 字,分為三個部分,標題分別是: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共產主義者的目的、階級爭斗的最近狀態。文中重申了《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揭示的階級社會是階級斗爭歷史的原理,指出:“階級爭斗從來就存在人類社會中間,不過已經改變了幾次狀態,因為這是以生產工具的發達為轉移的。”[3](P548)文中表示堅信《共產黨宣言》所闡明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規律以及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的結論,強調無產階級努力的發展和團聚“會使資本主義壽終正寢的”[4](P548)。遵循《共產黨宣言》的指引,文中宣告中國要建立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領導勞苦大眾,開展階級斗爭。文中較為系統地概述了《共產黨宣言》指明的共產黨奮斗目標:要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共有共用,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度和階級,要使國家政權消亡,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社會,為此首先就要組織階級爭斗,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要從資本家手里獲得政權并把政權放在工農大眾手里,要由無產階級民主選舉出來的最優秀的代表來制定建設共產主義的辦法,發展生產事業,等等。文中還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三年的實踐經驗來印證《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觀點,指出:要使工農從資本家手中獲得政權,就“正如1917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其他國家階級爭斗的趨向是“向著與俄羅斯的階級爭斗一樣的方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一面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余勢力作戰,一面要用革命的辦法造出許多共產主義的建設法”,“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資本家的勢力都消滅了,生產事業也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開始活動了,那時候的無產階級專政還要造出一條共產主義的道路。”[5](P550)全文用“共產黨”7次,用“階級爭斗”14次(另用“階級沖突”1次),用“無產階級專政”8次(另用“勞農專政”1次),用“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社會”16次,用“資本家”、“資本主義”、“資本制度”28次,提到“俄國”、“俄羅斯”有10次。文中未出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社會”。
中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共產黨”等詞都是于19世紀70、80年代日本人采用繁體漢字譯為日文的,到20世紀初又被中國人移植到中文書刊中。中國人也有不采用日文譯法者,而自己獨創譯名。1958年,我從上海出版的《國聞周報》1927年9月4日出版的第4卷第34期查到厚照寫的《嘉爾·馬克思傳略》一文,其中把“共產主義”譯為“公共主義”,把“共產黨”譯為“公共黨”。現在看來,這種譯法更準確,更符合古拉丁文communis和德文Komm unism us原意。“公共黨”,表明這個黨的奮斗目標不是只追求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是要管好公共資產,增加公共產品,發展公共事業,擴大公共服務,完善公共選舉,厲行公共決策,加強公共管理,嚴密公共監督,提高公共理性,弘揚公共精神,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造福公共大眾。①我把這個新見解寫進我領頭主編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大受讀者歡迎。
《中國共產黨宣言》還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即一國不能建成共產主義。文中說:“我們設想俄羅斯在她的領土之內,單獨可以建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這是大錯而特錯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既即時(原文如此——引者注)不能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衛自己,抵抗國內外的仇敵,這是很顯明的。”“這并不是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征,而且這種階級爭斗的狀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要經過的。”[6](P550)這就是說,當時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深信,俄國不可能單獨一國建成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會僅在俄國一國勝利,而且必將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取得勝利。
現在看來,含有上述重要內容的這份歷史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第一,它第一次亮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第一次又是唯一以《中國共產黨宣言》命名的中共黨史上的第一篇歷史文獻。它表明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群眾的新型政黨已經在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出現,它即將發展為全國性的政黨。它區別于民國以來成立的形形色色的各種政黨,有崇高的理想、明確的目的、偉大的胸懷、嚴密的組織、革命的行動,預示著將使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第二,它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與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列寧主義的核心思想結合在一起,以最簡明的概括與表述,展示給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于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7](P1470),“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8](P1471),這是完全符合實際的論斷。現在有人認為十月革命只是給我國送來了列寧主義,這是有悖事實的偏見。
第三,這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當時并沒有在任何報刊和任何場合公開發表,只是供早期共產黨員內部學習,也使要爭取并發展其入黨的對象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有具體的了解和明確的認識。它在北京、廣州、濟南、長沙、武漢等地共產黨組織中的散發與傳播,對提高早期共產黨員和接近共產黨人士的思想覺悟、政治水平和理論素養,無疑很有幫助。
第四,它為1921年7月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立,起了促進和奠基作用。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大都讀過這份宣言,在黨的“一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綱,看來是吸收了這份宣言的基本思想與要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以《中國共產黨宣言》為藍本,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作了更具體的發揮和更切實的規定。
《中國共產黨宣言》這份歷史文獻,也存在缺點。毛澤東于1958年6月間從中共中央秘書局1958年6月3日編印的《黨史資料匯編》第1號上讀了這篇從英譯稿譯回中文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后,曾寫了一段重要批語:“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則是基本正確的。但土地國有是不正確的。沒有料到民族資本可以和平過渡。更沒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總罷工,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是農民戰爭。”[9](P296)這幾句言簡意賅的批語,既肯定了這份歷史文獻作為黨的革命綱領“是基本正確的”,又指出它在革命階段、土地綱領、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以及革命斗爭主要形式這四個方面存在認識錯誤或不足。
我在這里要補充說明的是,這四個方面的欠缺、差錯,根源在于我國第一批共產黨員當時對俄國革命的經驗還了解不夠(俄國1917年革命是在二月先進行民主革命,后來在十月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還以為俄國革命的經驗具有普遍意義,中國也要照搬(如總罷工、土地歸社會共有、用強力消滅資本家階級)。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宣言》起了開天辟地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要點的歷史作用,但是還未能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中國共產黨自己獨特的主張。這份歷史文獻只有一處提到“在封建國家的時候,階級爭斗也是一樣的存在;但是與在資本家的國家下面的階級爭斗是有分別的,因為資本家的國家下面階級爭斗是格外緊迫,其勢足以動搖全世界”[10](P548)。僅有這句話似乎是聯系到中國實際,然而并未展開,筆鋒又轉到資本主義世界去了。
我在學習中還發現這份歷史文獻有幾處不確切的提法。如說“共產主義者主張廢除政權”,“要是私有財產和賃銀制度都廢除了,政權、軍隊和法庭當然就用不著了。”[11](P548)還有,文中提出“共產主義者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12](P547),而并不是首先收歸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其實只有當國家消亡后生產工具才能收歸社會公有。這些說法表明這份歷史文獻的作者多少還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輕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意是指體現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和意向,國家要管理好經濟與社會,促進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無產階級專政既可避免社會無政府狀態,又要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破壞民主。文獻中還說:“當了資本家被打倒了之后,這些產業組合(即工會——引者注)就變成了共產主義社會中主管經濟生命的機關。”[13](P549)這顯然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想用工會(在法國叫工團——引者注)來取代國家直接管理企業的主張。這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我在這里指出這些差錯,對于辨認這份文獻的作者至關重要。
瑕不掩瑜,我們不能苛求前人。《中國共產黨宣言》以簡明宣言的形式最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思想引進中國,提高了第一批共產黨員的思想認識,促進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立,它好比橋梁、引擎,其振聾發聵、啟蒙的歷史作用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二、《中國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和譯者考證
我在學習《中國共產黨宣言》的過程中,發現對這份歷史文獻的作者和譯者都有不同看法。對此,需要盡量考證清楚。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14](P52)和第一卷上冊(2002年版)[15](P81)都肯定寫明《中國共產黨宣言》是由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起草的。至于誰是起草者,史學界多認為是出于陳獨秀的手筆,或者認為是以陳獨秀為主的幾個人合擬的。這可以舉出幾本史書為證。葉永烈著《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這樣說:就在1920年11月“創辦《共產黨》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陳獨秀執筆,‘小組’的筆桿子們參加討論,起草了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宣言》”[16](P153)。朱文華著《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評傳》說:“也在這年11月間,陳獨秀與其他黨員一起又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17](P158)奚金芳寫的《一代偉人陳獨秀(1879—1942)先生幻燈片解說詞》提到:“47-7。圖為中國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寫)。”[18](P299)但三者均未寫明他們所依據的材料出處。《林茂生自選集》中收入林茂生和唐寶林合編的《陳獨秀年譜》,其中說:1920年11月陳獨秀“主持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織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19](P92),注明材料出處是:《“一大”前后》(一)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和施復亮:《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文章中都提到陳獨秀和他們醞釀起草黨綱、黨章的問題。11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第1號《短言》,據當時毛澤東致蔡和森的信說,“即仲甫所為”。“對照李、施的回憶和《短言》的內容,與《宣言》基本一致。似可斷言此宣言在陳獨秀主持下起草的。”[20](P124注398)年譜編者在注中較為謹慎地說“似可斷言”。我認為,如果另從上引材料查明與《中國共產黨宣言》不一致之處,似可斷言此宣言并非陳獨秀執筆或定稿的。這一點,下面還要加以證明。
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宣言》是出于共產國際和俄共來華使者維經斯基(Voigiw ski,又譯魏金斯基)手筆。楊奎松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中寫道:“從1921年(應是1920年之誤——引者注)11月維經斯基代為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宣告‘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征’之日起……”[21](P7)。楊奎松教授掌握史料豐富,著作豐碩。他在這里所說的維經斯基代為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事,注明材料出處是參見瞿秋白著《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22](P161)。我通查瞿秋白所著全文,并無這種說法。由于楊奎松是很有社會影響的學者,以至日本學者也相信他的這一說法有可能性。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有這樣的說法:“近年來,楊奎松通過尚未涉獵的未公布的中國共產黨史資料,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他指出魏金斯基可能參與了起草《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宣言》是由魏金斯基協助上海組織起草的,或者是代為起草的。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楊奎松沒有提示任何根據。”[23](P237)楊奎松提示參見瞿秋白著《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可是其中沒有找到任何根據。再查《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書中第一部分收錄維經斯基著述45篇,并無他代筆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第二部分收錄的董必武、蔡和森等11人寫的回憶與評論文章中也未提到他參與起草宣言,只有包惠僧提到“當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一致主張成立中國共產黨……于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草案”[24](P438)。“據陳獨秀在廣州時對我講,這份黨綱草案是陳和吳廷康(又譯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注)在上海起草的,不是從俄國帶來的”[25](P440)。可能正是根據這個材料,在全書第三部分楊云若、王福增編寫的《維經斯基在華活動紀事》中寫道:1920年5—8月維經斯基建議陳獨秀本人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推舉陳獨秀為書記,“并由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商議后草擬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以統一思想”[26](P462)。但是現在無法證明:這個黨綱草案就是11月間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即便兩者是同一個文獻,說這個宣言是維經斯基代為起草的,也還是不夠確切。
2009年10月,我十分驚喜地讀到《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應出自李大釗手筆》一文。作者馮鐵金是河北省唐山市豐南區委黨校原副校長。他經過細心考察與印證,發現《中國共產黨宣言》中的觀點和用語習慣多出自李大釗文稿,而與陳獨秀的文稿差別很大。由此他得出《中國共產黨宣言》不是陳獨秀所寫、應當是出自李大釗手筆的新看法。他列舉出《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所用的“經濟現象為最重要”、“最高的理想”,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贊揚,實行“(總)同盟罷工”等都是當時李大釗文章中的用語,而在當時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找不到的。馮鐵金認為《中國共產黨宣言》既然是出自李大釗手筆,那么它必定是早期北京共產黨組織而不是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文件。可惜他在文中只列舉出北京共產黨組織于1920年7、8月間草擬出一個黨綱要點,而這個黨綱還是張國燾7月間由京赴滬時從陳獨秀與維經斯基處得來的。由此可見,北京的黨綱并非北京黨組織自己獨立草擬的,它只是在參照上海黨綱的基礎上制訂的,其中添加上李大釗文章中采用過的詞語。這樣,不但無法確證宣言是北京共產黨組織草擬的,而且無法確證北京的黨綱即是《中國共產黨宣言》文本,更加無法確證宣言出自李大釗的手筆。我細讀馮鐵金的文章后感到:他考證宣言不是出于陳獨秀手筆,這一點是可信的,然而他斷言宣言出自李大釗手筆,則論據還欠充分。
我再去細讀李大釗當年的文章,發現他不僅盛贊十月革命的勝利,而且完全肯定新型蘇維埃國家政權和1918年的蘇俄憲法以及憲法中規定的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創舉。例如,他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號發表的《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中說:蘇俄“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中央統治會議”,“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么事都歸他們決定。”“這是Bolsheviki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27](P114-115)李大釗于1919年8月17日發表于《每周評論》第35號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中寫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張慰慈是當時北京大學著名政治學教授——引者注)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28](P232)1918年7月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蘇俄憲法明文規定:“全部土地為全民財產……全國性的一切森林、蘊藏與水利……實驗農場與農業企業均宣布為國有財產……作為使工廠、礦山、鐵路和其他生產及運輸手段完全轉歸工農蘇維埃共和國所有的第一步驟。”[29](P179)李大釗顯然贊同這些生產資料收歸工農蘇維埃國家所有的辦法。他認為這些經濟措施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他這樣說:“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部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30](P233)李大釗的這些言論,表明他這時已經堅決反對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可見,《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所主張的“廢除政權”、“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共有”,不歸工農國家所有,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要使工會“成為主管經濟生命的機關”,這些觀點顯然與李大釗的思想相悖。
由此可見,宣言既不會是出自李大釗手筆,也不會是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所寫。那么,這份宣言的執筆者究竟是誰呢?
筆者以為,我們只要悉心細讀張國燾的回憶錄和有關文稿,就不難作出一些推斷。在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中寫道:1920年7月他由北京到上海與陳獨秀連續交談了兩個多星期關于建黨之事。“陳獨秀先生這樣表示: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要做邊學邊干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決定。”[31](P90-91)可見,當時陳獨秀并沒有想要制定《中國共產黨宣言》,至于制定黨綱草案也是7月以后之事。8月間上海共產黨組織建立,選舉陳獨秀為書記。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于當月在上海出版,初版印一千冊,很快被一搶而空。這促進了上海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積極開展活動,隨即擬定了黨綱草案。既然馬克思、恩格斯執筆的《共產黨宣言》是1847年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文獻,所以上海共產黨組織草擬的黨綱很自然名為《中國共產黨宣言》。最近從俄羅斯檔案館新發現張國燾在1929年為莫斯科中山大學講課而寫的《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其中說:“北京小組成立(在上海之后),于1920年七、八月間,由李守常、張松年和我三人商量籌建(叫北京共產黨)。張松年不久赴法,我與守常與無政府接洽,他們也贊成馬克思,階級斗爭,一共有八人。決定黨綱如下:①共產黨原則……②共產黨目的……這個黨綱由陳獨秀從伍廷康得來,寫成中文,又有下面幾條:1)無(產階)級專政,2)國際組織,3)不準做官。”[32]北京共產黨組織擬定的黨綱,除李大釗、張國燾為主外,還吸收了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參與,而且這份黨綱也參照了上海草擬的黨綱;而在上海,是由維經斯基(即伍廷康)提出原則意見,再由上海共產黨組織集體討論后寫出黨綱草稿。很可能北京共產黨組織擬出的黨綱傳到上海后,上海黨組織又對原黨綱作了修改。上海黨組織于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之際創辦了《共產黨》月刊,11月23日把擬定的黨綱以《中國共產黨宣言》的名義印發給上海、北京、武漢、廣州、長沙、濟南等地黨組織,作為早期黨員和擬發展的新黨員的學習材料。
這樣看來,這份宣言就很難說是由陳獨秀或李大釗某一個人執筆完成的,很可能是1920年8—11月間,由上海和北京早期黨組織集體討論、反復修改制定的。北京黨組織于1920年9月成立,第一批黨員也是八個人,即李大釗、張松年(張申府)、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還有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隨后加入上海黨組織的袁振英也曾經信奉過無政府主義。所以在宣言中殘留有“廢除政權”、生產工具不收歸國家而“收歸社會公有”、使工會“成為主管經濟生命的機關”等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痕跡。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還講到:1921年春天,“我首先草擬了一個黨綱政綱草案,題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將經由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等等。”[33](P129)“馬林看了這個文件(由張太雷譯成英文),卻提出了較嚴格的批評,表示這個草案在理論的原則上寫得不錯,主要缺點是沒有明確地規定中共在現階段的政綱。他指出這個文件表示中共將支持民主的民族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能在中國迅速建立起來,這是對的;但似乎沒有說明如何實現的具體步驟。”[34](P130)共產國際于1921年春把維經斯基調回蘇俄,改派馬林為駐中國代表。馬林于6月3日抵達上海,14日才搬進公共租界。估計張國燾把《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英文譯稿交給馬林當在6月下旬。這份“成立宣言”的內容大部分與《中國共產黨宣言》相同或相近,估計張國燾在起草成立宣言前也是見過那份宣言并且參照宣言的。當然,成立宣言又增添了新內容,如中共的組成、中共支持民主民族革命、要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家,這些是原來宣言中所沒有的。不論宣言或成立宣言,都存在理論沒有聯系中國實際或聯系實際很不夠的缺點。1921年7月中共一大所通過的第一個綱領更進一步聯系中國實際,具體規定了黨的任務。
再說《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譯者究竟是誰。很可惜這份宣言的中文稿本在國內迄今沒有發現蹤跡。而宣言的英文稿本,大概是維經斯基于1921年春奉調回國到共產國際遠東局任書記時帶回伊爾庫茨克的。也正是在這一年秋天,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在1922年初召開一次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團體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派張太雷前往蘇俄參與籌備工作。張太雷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保存的中共文件中偶然發現有一份曾經由他譯為英文交給維經斯基的《中國共產黨宣言》稿本。胡華教授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卷中有一篇林鴻暖依據很多調查采訪寫成的《張太雷》傳,文中寫道:1922年“12月10日,太雷還把他目前翻譯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回譯成中文,并寫了譯者的說明,發給了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中的共產主義者組織討論”[35](P75)。這里指明宣言是張太雷從英文回譯為中文。可惜,這樣重要的論斷長期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中國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是1957年蘇共中央從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檔案中選出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譯稿前面的譯者附言只用英文署名Chang(張),并未寫明張太雷。這份宣言最早只刊登在中共中央秘書局1958年6月3日編印的《黨史資料匯編》第1號上,當時極少人能看到。它第一次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一),作為全書的首篇。該書編者在譯者Chang之下加上如下的注:“據初步考證,這個譯本可能是參加遠東民族會議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主要成員翻譯的,而代表團主要成員中姓張的只有兩個人,一是張國燾,一是張太雷,但寫這個說明可能性比較大的是張太雷,因他不僅負責大會的組織工作,而且負責英文翻譯,在這個時期他翻譯了不少東西。”《“一大”前后》(一)第1版是1980年7月出版的,當時編者注這樣寫可以說是盡心盡力了。該書1985年2月第2版是增訂版。編者在1984年6月寫的增訂說明中說:“這次出版,一是訂正了第一版的一些錯漏;二是增補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料。”[36](前言)可惜上述1982年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卷中的《張太雷》傳沒有引起編者注意,以致編者注還是保留原樣,只說譯者“可能性比較大的是張太雷”,而沒有明確肯定。
1989年出版的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在附錄中收入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令人遺憾的是,編者卻在注釋中寫道:“這個譯本,根據附在本文前面的譯者《致同志信》的時間和內容初步判定,是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張國燾翻譯的。”[37](P551)這個注釋判定譯者是張國燾,完全排除了張太雷翻譯的可能性。
我認為這個“初步判定”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如下:第一,譯者“張”譯文的時間是1921年12月10日。張國燾在11月初就到達伊爾庫茨克并在那里待到12月底,而且他是當時中共代表團團長,為何在他的回憶錄中從未提及有關這份宣言之事?如果是他親自翻譯為中文的話,他怎么會不提及呢?第二,即便他在那里找到宣言英文稿,他一定會找當時也在該地的英文程度比他高很多的張太雷譯為中文。如上所引,6月間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也是由張太雷譯為英文交給馬林的。第三,張國燾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在中共一大上未獲通過,沒有公布。他可以徑自再提交代表們討論,用不著再去回譯更早發布的那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第四,更加重要的是,7月間中共一大已經制定了正式的黨綱作為全黨行動指南,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張國燾完全沒有必要把籌備建黨時期的宣言再譯為中文提交參加遠東大會的中共代表討論。第五,張太雷當時也在伊爾庫茨克參與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團體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他很容易從當時在該地負責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的維經斯基處看到他頭年底譯為英文的宣言稿。第六,更加重要的是,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張太雷受中共領導人委派參加這次大會,直到8月才回國。因此張太雷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他不知道大會已經制定了正式的黨綱,8月后他即參與籌備遠東大會之事。到12月他感到很有必要再把宣言回譯為中文,供中共代表討論,以便將討論結果供“中國共產黨的參考和采納”[38](P547)。實際上,7月間中共一大制定了正式黨綱之后,這份宣言已經是明日黃花,完全用不著再討論了。事實上,在遠東大會的中共代表團中也未曾討論過。基于以上六條理由,筆者以為這份宣言不可能是張國燾譯的,只能是張太雷譯的。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這部文獻的正規性、權威性和公開性,其編者注釋也都有廣泛深遠影響,《中國共產黨宣言》“初步判定是張國燾翻譯的”這一難以成立的說法,曾多次被眾多學者所引用。例如,石川禎浩和馮鐵金的著述以及《新湘評論》2011年第1期選錄《中國共產黨宣言》原文時把有關譯者的這一條注釋[39]也照錄了。
拙文以上的論述和考證,如果對于當今重新學習中共黨史上首篇文獻《中國共產黨宣言》有些幫助,則幸甚!
[1][3][4][5][6][10][11][12][13][37][3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8]《毛澤東選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16]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7]朱文華:《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評傳》,青島,青島出版社,1997。
[18]奚金芳:《一代偉人陳獨秀(1879—1942)先生幻燈片解說詞》,載《紀念陳獨秀先生逝世60周年論集——陳獨秀與20世紀學術、思想、文化》,全國第七屆陳獨秀學術研討會籌備處編印,2002。
[19][20]《林茂生自選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1]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22]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0。
[23]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4][25][26]《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27][28][30]《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9]《人民日報》圖書資料組編:《憲法問題參考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31][33][34]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32]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的講課稿(1929年)》,載《百年潮》,2002(2)。
[35]林鴻暖:《張太雷》,載胡華主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
[36]《“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一),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9]《中國共產黨宣言》,載《新湘評論》,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