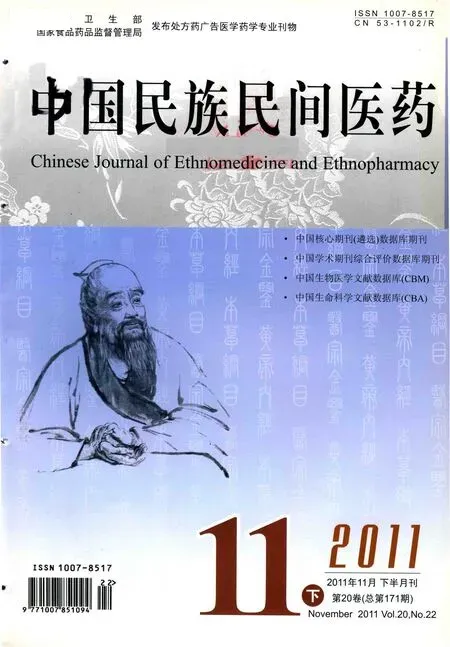試議中藥之毒
沈錦華
江蘇省如皋市人民醫院藥劑科,江蘇 如皋 226500
俗話說“是藥三分毒”,即便是純天然,中草藥也并非就全無毒性。中藥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而總結出來的,大部分中藥的安全性已是毋庸置疑,但不少的中藥確實具有一定毒性,故需要對中藥的毒性進行全面的認識和評價,并合理應用。
1 中藥毒性的認識
1.1 中藥毒性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中藥毒性的概念,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逐步發展的認識過程。早在周朝,《周禮·天官·冢宰》就有記載:“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此時的毒性是藥物用以指治療疾病的性質;秦漢期間,醫藥實踐經驗逐漸積累,先秦諸子百家,尤其陰陽五行家的思想也滲透到醫藥學領域中,產生了以“四氣五味”為主的藥性理論,認識到毒性就是藥物的氣味偏勝之性,即使在沒有病邪存在或本來陰陽平衡的狀態下,中藥的偏性作用于人體則可能表現為毒性,[1]魏晉之后,毒的含義逐漸演變成專指那些藥性強烈、服后容易產生毒副作用甚至可致死的藥物;唐代《新修本草》對部分藥物進行了“有毒”或“無毒”的標記;明代《本草綱目》中,專列毒草一類,記載有毒中藥57種;近代中藥毒性多指藥物的有毒成分,如馬錢子有大毒,其毒性成分為番木鱉堿;細辛中含有毒的揮發油,其中黃樟醚的毒性較大,為致癌物質。
1.2 中藥毒性的分級
《神農本草》記載藥物350多種,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主養命而無毒;中品主養性,無毒或有毒;下品主治病而多毒,不可久服。《素問·五常政大論》篇載:“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其中大毒是藥物毒性劇烈的,常毒藥的毒性次于大毒,小毒藥的毒性小,無毒藥即平性藥。現代醫學多沿用傳統的經驗進行分級,將有毒中藥分為劇毒、大毒、中毒和小毒四級,也有學者[2]按照用藥后不良反應的情況將毒性分為急性毒理、慢性毒理、遺傳毒性、皮膚毒性、心臟毒性等多個方面。
1.3 中藥毒性與藥性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藥性與毒性是對立統一的,中藥毒性既有對人體不利的一面,也有治療疾病的一面,運用得當便可治病,達到起死回生之功效,但若是用之不當,不僅不能治病,有可能傷害身體,甚至造成死亡。
因此,對中藥的客觀認識,分析毒性產生的原因,制定相應的控制毒性的措施是保證用藥安全的關鍵。
2 中藥毒性產生的原因
不少中藥具有毒性,使用不當,危害巨大,但是藥物的毒性是可以克服,甚至能夠變毒為寶,起到更好的治療作用。探究中藥毒性產生的根源是做好預防中藥毒性工作的前提,一般而言,中藥毒性產生與以下因素有關。
2.1 品質混亂
盡管我國藥用資源豐富,但長期以來,藥物同名異物、異名同物的現象導致中藥的品種十分混亂,如品種混淆致使誤將商陸當人參、關木通當木通致中毒;南五加皮屬五加科植物細柱五加的根皮,無毒;而北五加皮屬蘿藦科植物杠柳的根皮,有毒,一旦混用后果不堪設想。另外,現代科技的發展,環保意識的落后,使得我們生存的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尤其是農業操作殘留的農藥已使中藥含有毒元素、重金屬元素嚴重超標,造成中藥質量下降,毒性增加。
2.2 辯證不準
病有寒熱虛實之分,藥有寒涼溫熱之性,治病投藥需遵循辨證施治的原則,按理、法、方、藥的程序選用藥物。但臨床上因辨證不準、寒熱錯投、攻補倒置導致的案例時有發生[3]。如明為脾虛泄瀉,反用大劑黃連導致溏泄加重;雖為血虛,但兼便溏;仍用大劑當歸,致使溏泄不已。
2.3 配伍不適
中藥的配伍應用是中醫遣方用藥的主要形式,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則進行組方,意在減毒治病[4]。為保證配伍合理,古人總結出了“相使相須相畏相反”、“十八反”、“十九畏”和“七情合”等對中藥毒性趨利避害的應用要訣。《神農本草經》中有云: “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臨床實踐證明有些藥物配伍不當會產生毒性或增強毒性,如山豆根與大黃配伍可出現中毒癥狀;附子與麻黃配伍則產生毒性。
2.4 炮制不當
炮制可以消除中藥毒性,傳統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加熱法、水源法、制霜法及加輔料法等,而炮制失當就會產生劇毒[5]。如烏頭有祛風除濕、溫經止痛的功效,藥典規定其炮制方法為用水浸泡至無干心,再蒸或加水煮沸,但臨床上因服用烏頭生品或炮制失度的烏頭類中藥而導致中毒者比比皆是;朱砂本身有毒,但有清心鎮驚,安神解毒的作用,一般水沸入藥,火煅則析出劇毒的水銀。
2.5 用法有誤
2.5.1 用量過度 古人有言:方藥不傳之秘在其劑量也,用藥量之多寡,當隨證而定。各種藥物治療疾病都有一定的劑量范圍[6]。中藥的毒性通常與劑量成正比,過量是引起毒性反應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如肉蓯蓉補腎助陽藥力和緩,用量宜大,少則藥力不濟,難以取效;藥典中記載木通無毒性,但使用過量亦可導致腎中毒、腎功能衰竭。
2.5.2 用藥時間過長 冠心蘇合丸[7]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常用中成藥,具有寬胸理氣止痛的功效,2004年以前生產的冠心蘇合丸含有青木香,是馬兜鈴科馬兜鈴的根莖,其主要化學成分為馬兜鈴酸及其衍生物,長期服用導致慢性中毒。
2.5.3 煎煮不當 煎煮時間的長短對中藥的有毒無毒也有影響。如臨床用烏頭、附子等強調先下久煎,目的在于使藥中所含的劇毒的雙酯型生物堿,生成毒性較弱的單酯型烏頭堿,以減小或消除毒性,若煎煮時間不夠,所含烏頭堿未被分解為毒性較小或接近無毒的烏頭次堿或烏頭原堿,即可毒害人體,甚至斃命。
2.6 劑型不明
《神農本草經》有言:“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煎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并隨藥性,不得違越。”因丸劑在體內吸收較慢,故無毒之品多用丸散劑,可緩解其毒性。草烏、雪上一枝蒿,若以酒為溶劑,服后也極易引起中毒。
2.7 中西混用
現在很多醫者用藥強調中西醫結合,但殊不知有些中西藥混用會適得其反。如五味子、烏梅等酸性藥物中含有枸櫞酸、蘋果酸等成分,若與磺胺類藥物同服則使其溶解度減小,易在腎小管中產生沉淀,引起結晶尿、血尿等癥;而堿性中藥如澤瀉、威靈仙等,與阿司匹林,胃蛋白酶等酸性藥物同用后發生酸堿中和,以致藥性減弱。
2.8 個體差異
個體因體質強弱程度不同,對藥物毒副作用的耐受力也有差異。一般素體強健的人可選用作用峻烈或有毒之品,藥量可稍加;而體弱、年老、嬰幼患者,則應盡量選用藥性平和之品;婦女應根據生理變化而選藥,妊娠期的用藥者,應慎用辛熱滑利、破氣攻下、破血逐瘀藥,禁用毒烈藥,以免損傷胎兒乃至墮胎;若處在哺乳期,對有毒之品亦當慎用,以免有毒成分從乳汁排泄,傷及嬰兒。
2.9 其他 除中藥品質混亂、辯證、配伍、用法、劑型、中西藥物混用、個體差異等因素易產生中藥毒性外,貯藏不當、給藥途徑變換、以次充好、亂用藥材等其他因素,也是產生中藥毒性不可忽略的原因[8]。
3 中藥毒性合理運用的措施
張隱庵在《本草崇原》中曰:“甚至終身行醫,而終身視附子為蛇蝎,每告人曰,附子不可服,服之必發狂而七竅流血,服之必發火而癰毒頓生;服之彼內爛五臟,今年服之,明年毒發。”附子作為為回陽救逆第一品藥,但若因炮制、用法用量不當則易引發中毒,重者甚至死亡[9];斑蝥屬劇毒藥,中毒劑量為0.6g,致死劑量為1.5g,當運用合理時則可以治療肝癌。對中藥的毒性進行合理評價,正確辨證論治,合理炮制配伍,準確用藥方可發揮中藥毒性獨特的治療作用。
3.1 科學評價,監督管理
3.1.1 科學評價 中藥是一個以偏糾偏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中藥毒性的科學評價尤為重要,只有正視藥物藥性,合理應用,方能達到治病的目的。以附子為例,古今醫家并不因附子有大毒而回避不用,反而通過探討其適應證、炮制、配伍、劑量、患者體質等內容科學的評價其毒性,為其現代應用提供了科學依據。
3.1.2 監督管理 除了對中藥的評價外,還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為權威、為法律依據進行中藥的使用,開具中藥處方的人應是具有國家衛生部頒發的具有中醫行醫資格的執業醫師。在當下的經濟社會中,有醫生為迎合病人要求而濫用補藥,某些藥廠或媒體更是為利潤所驅使,通過電視報章宣傳中藥無毒副作用的錯誤觀念,誤導病人過量、重復或錯誤用藥,造成藥物中毒。這些現象都需要相關部門加強監督管理和制止,避免中毒事件的發生。
3.2 確保來源,對癥下藥
3.2.1 來源可靠 中藥同名異物者較多,因此從中草藥的源頭抓起,實施GAP,大力發展道地藥材,藥材產地應經常進行地質、水質、溫度、氣候的觀測,藥材的采收應合適宜,貯藏和加工應妥善,以確保藥材質量。
3.2.2 對癥下藥 《內經》提出:“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的治療原則。即提倡準確辯證,對癥下藥,如違反這些治則,均可導致各種不良反應[10]。《本草綱目》有言:“藥物,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失宜,參術亦能為害”。如百合,為甘寒滑利之品,風寒痰咳,中寒便滑者忌服。痰濕內蘊,中滿痞脹,腸滑泄瀉者忌服蜂蜜。
3.3 配伍合理,炮制得法
3.3.1 配伍合理 所謂“藥有個性之特長,方有合群之妙用”,即說明了藥與藥之相互關系,因配伍不同而作用有異。“七情”有言, “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如附子有毒,配伍甘草使用,可以減輕其毒性;麻黃湯中選用加入甘草以減緩麻黃、桂枝的發汗峻烈之性。通過方劑的組方原則進行指導,合理配伍,使各種藥物間互相影響,可以降低或消除毒性,減少中藥的毒副作用,提高療效。
3.3.2 依法炮制 依法炮制是降低或消除中藥毒性的必要措施,某些中藥的毒性成分也是有效成分,既要降低毒性又要保持療效,因此掌握好中藥的炮制方法對其藥效的發揮十分重要。如生半夏有毒,但用生姜、明礬制后,其毒性減低,止嘔效果更好;甘遂、大戟、芫花用醋制后,毒性減低;朱砂水飛后減少毒性成分游離汞的含量,常山經酒或醋制后減輕對胃腸道的刺激作用;黃連苦寒,用苦寒之性強,用酒、姜或吳茱萸則可緩和其苦寒之偏性,使之寒而不滯。
3.4 劑量適宜,因人而異
3.4.1 劑量適宜 應用中藥時,一般應從小量開始,逐漸加大用量,有不少中藥有蓄積毒性作用,如朱砂、苦杏仁、桃仁、郁李仁等,使用這一類藥物時應適可而止,中病即止。大黃、麻黃等,雖然不是毒性中藥,但在不合理應用的情況下,亦會不同程度的損傷人體,而另一部分藥物,如山藥、薏苡仁等臨床使用時雖可大劑量應用,但也不能盲目地無限制投藥,這同一個健康人長期暴飲暴食也會損傷脾胃的道理是相同的。
3.4.2 用藥因人而異 古語有言“承則為治,亢則為害”,因此可推測,在符合辨證論治的狀態下,中藥的中毒劑量、半數致死量以及最大耐受劑量等均應為變量,即中藥的毒性是隨機體狀態或疾病狀態的變化而變化的[11]。因此,在用藥前應明確中藥的具體成分,哪些成分為毒性成分;其次,在患者用藥前,應詳細詢問,掌握患者對所開藥物是否有過敏史;再者,醫生應根據患者的病情和患者性別、年齡、體重,正確施治,安全、合理的使用中藥,為患者更好地服務。
4 小結
中藥的毒性確實存在,應用中藥時發生中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并沒有可怕到因噎廢食的地步。中藥的藥效物質與毒效物質的是有機的組合體,藥、毒效物質可能既存在性質上的簡單對立,又存在著復雜的辨證統一,應對中藥毒性和藥性辯證看待,其關鍵是對其毒性的認識、掌握用藥原則,將毒性轉化為有利于治療的積極因素。同時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建立質量控制標準,做好藥物不良反應監測,繼續探索中藥增效減毒新方法,以保證中藥應用的客觀性、合理性和科學性。
[1]利順欣,王世勛,試論中藥之毒[J].遼寧中醫學院學報,2003,5(2):163.
[2]宋小莉,2009年中藥單味藥及其有效成分毒理學研究概況[J].山東中醫雜志,2010,29(8):574~575.
[3]王雪英,造成中藥毒性的因素與對應方法[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09,3(7):170~171.
[4]白宇乾,謝英,丁舸,等,方劑配伍三要素及對中藥毒性的影響[J].中醫雜志,2008,49(3):282.
[5]黃益群,龔千鋒淺,談幾種常見中藥的毒性與炮制的關系[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10,22(3):44~46.
[6]孫立靖,論中藥的毒性及臨床應用[J].中國中醫急癥,2009,18(9):1538~1539.
[7]史文慧,59例馬兜鈴酸腎病的報道[J].藥物流行病學雜志,2008,17(2):101~102.
[8]趙民生,曹秀虹,預防中藥毒副作用的方法[J].2010,7(7):11~14.
[9]鄧家剛,范麗麗,從對附子的爭議來探討有毒中藥毒性問題[J].河南中醫,2010,30(9):925~927.
[10]趙紅玉,周春祥,基于藥、毒效成分辨證關系探討有毒中藥研究思路[J].中草藥,2008,39(11):1601~1604.
[11]孫利民,從“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談中藥毒性[J].中醫雜志,2009,50(9):858~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