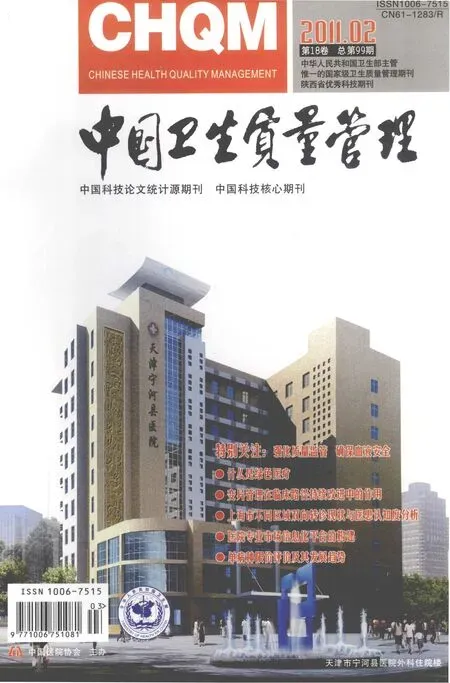核酸檢測技術在血液篩查中的應用評估及建議
◆ 顏秀娟 邱昌文 石慶秋 謝家日 羅必泰
責任編輯:吳小紅
輸血相關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核酸檢測(Nucleic Acid Test,NAT)是一種新興的血液傳染病檢測方法,能顯著縮短血液感染病毒的“窗口期”,降低經輸血傳播疾病的風險。但目前關于是否在我國開展NAT血液篩查的爭議較大。南寧中心血站血液檢測實驗室作為廣西NAT血液篩查試點實驗室,于2010年11月進入試運行階段。文章結合工作實踐,對開展NAT血液篩查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1 必要性
1.1 現行血清學檢測模式不能保證血液安全
輸血傳播疾病以病毒傳播為主,在我國最引人關注的為 HBV、HCV和HIV。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要求,采供血機構對獻血者的病毒血清學檢測模式為:用2種不同廠家的EIA檢測試劑篩查HBsAg、抗-HCV、抗-HIV[1]。雖 然 這 種篩查模式極大地降低了輸血傳染疾病的風險,但由于EIA檢測的是抗原和抗體,存在“窗口期”、病毒變異以及低水平攜帶者等漏檢[2]。“窗口期”是指從感染病原體到血液中可檢測標志物的時期。病原體標志物為抗體或抗原。HBV、HCV和HIV的“窗口期”分別為50~60d、70d 和 40d[2]。有文獻表明,美國90%以上輸血傳播HIV和HBV以及75%以上輸血傳播HCV的危險性均來自“窗口期”感染獻血[3]。血清學檢測HBsAg、抗-HCV和抗-HIV陰性不能排除HBV、HCV和HIV感染。研究報道表明,EIA檢測合格的獻血者中,HCV RNA陽性比率為 0.01% ~0.19%,HBV DNA 陽性比率為0.4%~0.92%;在 HBV暴露率 70% ~90%的地區,獻血者中有7% ~19%為HBsAg陰性HBV感染者,而HB-sAg陰性HBV DNA陽性血18%可導致輸血后乙肝感染[4]。我國是乙肝高流行區,HBsAg攜帶者率為9.09%,HBV 流行率高達 60%[5],抗-HCV 陽性率達 3.2%[6],艾滋病亦處于快速傳播階段。因此,如果按照現行血清學檢測模式,傳染性病毒經輸血傳播的形勢非常嚴峻。
1.2 檢測試劑敏感性不夠易造成漏檢
近年來,患者因輸血感染乙肝、丙肝或艾滋病而向法院起訴要求血站和醫療機構予以賠償的案件不斷增多。究其原因,檢測試劑敏感性不夠而造成漏檢是重要原因之一。造成EIA檢測假陰性的原因有“窗口期”感染、免疫靜默感染、病毒變異等。不同病毒感染的“窗口期”長短不同且存在個體差異,并與檢測方法及所用試劑的敏感性有關。避免漏檢的方法是增加檢測標志物和檢測項,包括抗原檢測和核酸檢測2個方面。在病毒感染早期,病毒抗原蛋白的出現要早于抗體,可縮短“窗口期”。可增加的抗原檢測項有:(1)HCV核心抗原檢測。增加此項檢測可縮短HCV感染檢測“窗口期”約 40~50d。但 HCV核心抗原檢測試劑昂貴,多為進口,國產試劑靈敏度和特異性有待提高。(2)HIV-P24抗原檢測。P24抗原檢測法較抗體檢測可使窗口期縮短1~2周。但單獨的P24抗原檢測只能用于早期輔助診斷和病情監測[7]。第四代 HIV EIA為 HIVP24抗原和抗體聯合檢測試劑,但由于同時把抗原和抗體包被在反應板上,存在相互干擾的可能,檢測的特異性和敏感性都會受到影響[8]。另外,研究表明,HBV隱匿型感染是一種HBV抗原抗體陰性,HBV DNA低水平復制的慢性無癥狀乙肝病毒感染廣泛存在于普通人群中,是HBsAg篩查漏檢的主要原因。因此,在 HBV感染高度流行、抗-HBc不可行地區,HBV NAT篩查是非常必要的[9]。
2 可行性
2.1 NAT自身敏感性極高
NAT是一系列直接檢測病原體核酸技術的總稱,主要原理是使用物理、化學和生物學方法,通過靶核酸直接擴增或其附帶信號擴增的方法,讓看不見的極微量的核酸變成直觀的光電或可視信號,從而判斷標本中是否存在相應的病原體。其敏感性極高,可大大縮短檢測“窗口期”[10-11]。美國 2000年血清學檢測HIV和HCV的輸血感染機率分別低于1:25萬和1:130萬。NAT技術的應用,使得HIV和HCV因“窗口期”感染的機率降低到 1:200~400 萬[1],極大地降低了經輸血傳播疾病的風險。另有研究發現,NAT檢測可將HBV、HCV和 HIV EIA檢測的“窗口期”分別縮短為約25d(縮短45%)、59d(縮短 89%)和 11d(縮短50%),還可檢測出因病毒變異、免疫靜默感染、人工操作錯誤等漏檢的污染血液[11],可有效預防經輸血傳播疾病。
2.2 現實需要
近年來,我國乙肝、丙肝及艾滋病感染人群呈明顯上升趨勢。獻血者中感染或攜帶上述病原體的比例較高,臨床用血安全面臨巨大挑戰。引進NAT血液篩查技術,可進一步提高血液安全性,減少輸血感染事故的發生,從而增強公眾對醫療衛生行業乃至對政府的信心,進而保障社會穩定。到 2010年 6月,北京、上海、杭州、大連、深圳等地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已開展NAT血液篩查檢測;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及廣州亞運會均引進NAT血液篩查技術,以提高用血安全性。NAT血液篩查技術的優越性已引起國家衛生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2010年全國醫政工作會議指出,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主要是通過血液傳播,NAT血液篩查技術相對傳統酶免技術而言,具有速度更快、靈敏度更高等優勢。會議將北京、上海、廣州等地15所采供血機構確立為我國內地首批核酸檢測試點單位。NAT血液篩查技術在我國的推廣與應用將成必然趨勢。
3 建議
3.1 開展成本效益與血液殘余風險度分析
由于NAT試劑價格比常規血清學檢測試劑要貴得多,因此在探討我國是否需進行NAT血液篩查時,必須對血液殘余風險度進行評估。輸血后病毒感染的殘余風險度評估是一種借助數學模型的前瞻性研究。研究表明,實施核酸檢測篩查血液的發達國家,輸血后傳播病毒的殘余風險度要低于沒有實施核酸檢測的發展中國家[12]。但對于我國來說,這3種病毒的流行病學特征與國外不盡相同,照搬國外檢測模式,存在成本與效益的問題。國內部分血站在血液篩查中對EIA檢測陰性的血樣進行3種病毒三聯核酸檢測,都檢出了一定比率的HBV抗原陰性DNA陽性的血樣,少有HCV和HIV檢出的報道,因此在我國采用此種方法進行篩查的成本與效益需進行更深一步地評估。
3.2 檢測模式及試劑選擇
NAT試劑本身的質量及采用何種檢測模式,直接關系到該項技術的實際作用[13]。最初應用 NAT篩查血液時,一般采取混樣檢測模式以降低成本,但匯集樣本數越多,漏檢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國際流行趨勢是盡可能小樣本混樣或單個檢測。是否匯集或匯集樣本數為多少取決于所用試劑的靈敏度,還與當地獻血人群中病毒感染者的陽性率以及病毒載量攜帶者的比例有關。目前,國外多采取小樣本混樣或單人份NAT檢測;國內試行核酸血液篩查的血站引用技術各有不同,混樣規模從50人份到 5 人份不等[10]。
臨床診斷和血液篩檢是兩個不同的應用領域,血液篩檢試劑的要求比臨床診斷更高。所以,開展NAT血液篩查時應注重試劑本身的質量。應選擇靈敏度高、重復性好、特異性好的試劑,尤其是對HBV NAT試劑的靈敏度要求應比HCV及HIV NAT高,以防止低拷貝的病毒陽性的血液漏檢。目前,國內開展NAT血液篩查多采用進口試劑,國產NAT試劑尚未廣泛應用,主要是因為試劑靈敏度和特異性較低。迄今為止,正式通過美國FDA認證的試劑僅有2種,即Roche S201 MPX 6人份混合檢測及Chiron ProcleixTMA技術。但進口試劑的高額成本也限制了其應用。因此,研發出適合我國國情的高靈敏度、低成本的NAT血液篩查試劑是國內采供血機構開展NAT血液篩查的前提。
3.3 實行標本集中化檢測
NAT檢測不但試劑昂貴,而且對基礎設施、檢測環境、人員培訓和管理模式等都有較高要求,成本很高。目前,有些國家實行標本集中化檢測,優勢很明顯。但在我國要實施標本集中化檢測,還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試點和妥善解決。集中化檢測模式可以充分利用資源,提高檢測質量和檢測效率、降低檢測成本,可逐步試行。具體做法可采取打破行政區劃及隸屬關系,實行地域管理。現代化的交通及通訊為實現這種模式提供了基礎,發達地區可優先考慮采取這種模式。以南寧中心血站為例,血站作為廣西首府城市血站,即將開展的標本集中化檢測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實驗室建設、自動化檢測設備購置、人才引進及人員培訓等均得到了很好地落實,為開展NAT檢測提供了有利條件。
3.4 有符合技術要求的實驗室
核酸血液篩查技術是精密的檢驗技術,易受環境影響。因此,需建設一個符合技術要求的實驗室,以保障檢驗結果的準確性。實驗室建設時應注意:血清學檢測實驗室應與NAT實驗室分開,各自獨立為2個實驗室;NAT實驗室的建設應符合《臨床基因擴增檢驗實驗室管理暫行辦法》相關規定,并符合基因擴增檢驗實驗室區域設置原則。NAT各工作區域必須嚴格按照單一方向進行,即試劑儲存和準備區→標本制備區→擴增反應混合物配制和擴增區→擴增產物分析區,以防止人員、儀器設備、血樣、試劑等交叉污染。
3.5 實驗室質量管理體系的建立
對NAT檢測的質量管理直接關系到該項技術的實際應用效果。如果沒有全面的質量管理,NAT篩查血液不僅可能會漏檢,還可能會出現大量假陽性問題。當大量假陽性結果出現后,不僅拆分復查工作費時費力,還會影響正常發血。血液標本的質控是整個檢測過程的最關鍵的控制點之一,對血液檢測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為確保血液標本的質量,需建立完善的標本留樣和處理程序,以保證采集標本的完整性,即正確采集、貯存、運輸并正確離心分樣等[14]。同時,通過建立標準操作規程,規范NAT檢測人員的操作,嚴格執行防污染措施,可避免樣品間的交叉污染和擴增物的污染。
總之,新方法、新技術的應用要考慮檢測成本、試劑與儀器設備的配套、人員技術的培訓以及對現行法律修訂的跟進等。但隨著NAT篩查試劑質量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以及我國血液篩查模式的轉變、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經費的落實,我們堅信,血液NAT篩查在我國將有著廣闊的前景。
[1]中華人民共和國.GB18467-2001,獻血者健康檢查要求[S].2001.
[2]陸志檬,韓永年.進一步控制經血傳播的病毒感染[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01,24(3):135-136.
[3]文國新,美黑麗.血液感染性安全問題的現狀與展望[J].中國輸血雜志,2006,19(4):332-334.
[4]葉賢林,曾昭鑒.乙型肝炎病毒核酸篩查近展[J].中國輸血雜志,2007,20(6):537-539.
[5]梁曉峰,陳園生,王曉軍.中國3歲以上人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學研究[J].中華血液學雜志,2005,26(9):655-658.
[6]戴志澄.中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M].北京:北京科技文獻出版社,1997.60-68.
[7]楊 振,祁自柏,于 洋,等.窗口期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樣品抗原檢測意義分析[J].中國預防醫學雜志,2008,9(9):793-797.
[8]金 燕.艾滋病的檢測技術及其研究進展[J].旅行醫學科學,2007(13):1-5.
[9]葉賢林,周一炎,楊立新,等.血液HBV DNA全自動檢測及基因分型分析[J].中國輸血雜志,2005,18(2):94-96.
[10]任芙蓉.核酸檢測技術在國內外血液篩檢中的應用[J].北京醫學,2008,30(8):561-564.
[11]王 迅,鄭 嵐,張 穎,等.核酸擴增技術(NAT)在上海血液篩查中的初步應用[J].中國輸血雜志,2003,6(3):157-160.
[12]張孝山.NAT技術篩查血液后輸血傳播病毒感染的殘余危險[J].中國醫學檢驗雜志,2006,7(2):138-140.
[13]葉賢林,曾昭鑒,楊寶成,等.國產核酸擴增(PCR)試劑在獻血者血液HBV DNA篩查中的應用研究[J].中國感染控制雜志,2007,6(5):301-306.
[14]顏秀娟,李 忠,李 彬.血站檢驗科關鍵控制點質量管理的探討[J].基層醫學論壇,2009,13(2):156-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