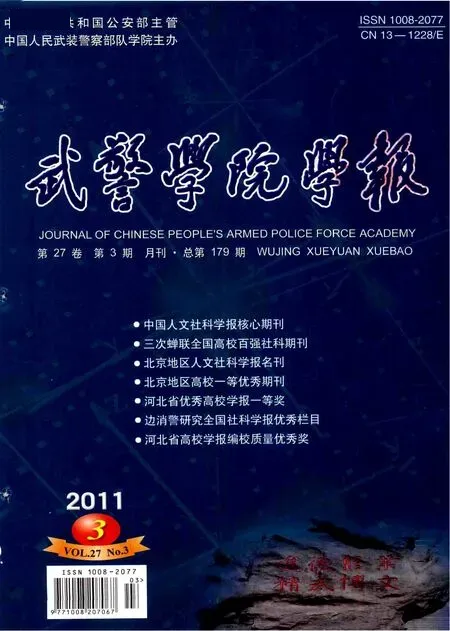吳起戰爭觀淺議
●田照軍
(工程兵指揮學院,江蘇徐州 221004)
吳起的戰爭觀在先秦兵家中是最為系統的,這主要體現在他對戰爭的起因、性質、戰爭與政治的關系等問題的論述上。吳起對這些問題的系統論述,極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戰爭理論,并對研究當代戰爭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戰爭的起因
戰爭觀是軍事思想的基石和出發點。在吳起之前,孫子在這一問題上已有較為系統的理性認識,提出了“慎戰”和“備戰”并重的戰爭觀念,但孫子對戰爭的起因和性質并未論及,這是一個較大的遺憾。而吳起則已經開始注意探討戰爭的起因問題,并初步區分了不同戰爭的性質。
吳起認為,戰爭的爆發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列國爭雄兼并的條件下,戰爭乃是普遍的社會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引發戰爭的原因有五個方面:“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吳子·圖國》)“爭名”,指各諸侯國爭奪霸主之名,這是春秋時期許多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爭利”,指爭奪土地、人口等利益。吳起所參加的魏、秦兩國爭奪河西地區的一系列戰爭,大多屬于“爭利”之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對戰爭的掠奪性目的做了精辟的論述:“以前進行戰爭,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掠奪性戰爭一直是西方國家的傳統,他們把侵略看做是一種自然法則。雅典人認為:“我們的目的和行動完全適合于人們對神祗的信仰,也適合于指導人們自己行動的原則。我們對于神祗的意念和對人們的認識都使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范圍內擴張統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制造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制造出來之后,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律的人。我們發現這個規律早就存在,我們將讓它在后代永遠存在。”[1]“積惡”,指諸侯列國交惡成仇。如公元前685年,魯國趁齊桓公即位不久,出兵伐齊,被齊國打敗。齊桓公于次年攻打魯國,被魯軍大敗于長勺。長勺之戰即是齊魯兩國“積惡”的結果。“內亂”,指列國內部勢力爭權奪利。如戰國初年的晉陽之戰,就是晉國內部幾大勢力集團的相互兼并、爭權奪利的“內亂”之戰。“因饑”,指由于饑荒導致民眾起義或被敵國乘虛而入。如公元478年,越王勾踐趁吳國大旱之機發動攻勢,在笠澤之戰中一舉消滅了吳軍主力。
可以說,吳起的五種戰爭起因,基本上概括了中國古代戰爭的全貌,盡管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未能揭示戰爭爆發的階級本質和深刻的社會原因,但吳起的戰爭起因論徹底沖破了‘天命觀’的陰霾,提出了具備樸素唯物主義特征的觀點,因而還是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的”[2]。
二、戰爭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戰爭觀把戰爭性質劃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兩種,而吳起根據戰爭的動因,將戰爭性質劃分為五種,這就是“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吳子·圖國》),顯然,在這五種戰爭中,只有“義兵”是正義戰爭,其他都是非正義戰爭。吳起還進一步對五種戰爭進行了解釋,即“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同上)。所謂義兵,就是為名而戰,禁暴除亂;所謂強兵,就是恃借兵強而征伐別國;所謂剛兵,就是因怒而興師;所謂暴兵,就是因貪利而拋棄禮儀所發動的戰爭;所謂逆兵,就是不顧國內危機和人民疲憊,興師動眾而發動的戰爭。
吳起通過對戰爭性質的界定,從而得出了對待不同戰爭的辦法,他說:“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同上)他認為要制止義兵,就要通過說“禮”折服它。這里的“禮”是指周王室規定的處理諸侯國關系的法則或規定,論“禮”的過程,也是政治解決爭端的過程;對待強兵,要用謙讓使對方悅服。比如城濮之戰中,晉文公“退避三舍”即是一種謙服的策略。通過退讓,晉文公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所謂“軍退臣犯,曲在彼矣”,又將楚軍引至城濮預設的戰場,贏得了軍事上的先機,從而為戰爭勝利奠定了基礎。謙讓是一種政治謀略,是避免矛盾升級的有效辦法。但是謙讓不等于無原則地退讓,否則這樣去制止戰爭與戰敗就沒有什么兩樣;對待剛兵,必須用言辭說服他。這里的剛兵,也就是孫子所講的怒而興師和慍而致戰。通過言辭,擊中要害,既能制止戰爭,也糾正了對方的錯誤,避免了因怒興師而招致失敗的厄運;對待暴兵必須用計謀制服它。因為暴兵想通過武力實現掠奪的目的,通過計謀,最易使對方的圖謀落空,此外暴兵者最近功利,利益遮擋了他們的雙眼,這就為計謀運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對待逆兵要用威力壓服它,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威懾力量。因為逆兵多存僥幸心理,只有威懾才能使對方改變戰略意圖。以上五種戰爭的性質或不同戰爭類型,由于動因不同,具體的謀略運用也不同。吳起在闡述這些問題時,其落腳點是如何不戰而勝或謀攻而勝,這也為我們研究當代戰爭理論提供了寶貴的研究方法。其實,在戰爭實踐中,戰爭的性質有時難以明確區分,制敵方法也難一概而論,無論用哪一種方法,都要以一定的軍事實力作為后盾,否則不僅不能降服敵人,還會為敵人所制。
吳起明確認識到戰爭會消耗大量的財物,殺戮大量的民眾,招致深重的災難。因此,他極力反對擴大戰爭。他說:“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同上)吳起明確指出了使用武力要注意把握“度”,靠多次發動戰爭取得勝利不是福,而是禍;不是利,而是弊。以此王天下者少,亡天下者多。這一觀點,極大豐富了古代戰爭理論。
三、戰爭與政治
吳起總結和吸取了歷史上國家興衰的經驗教訓,認識到要鞏固和加強封建主義的政治統治,就要使政治與軍事相輔為用。他說:“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吳子·圖國》)吳起以歷史上承桑氏國君,只有文德而廢除武力,使國家滅亡;有扈氏國君,只恃眾好勇而不修文德,使國家喪失的教訓,告誡魏文侯要以史為鑒,要“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內修文德”就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教化萬民,親和萬民,這樣治國安民,才能使民眾與當政者齊心協力,以此國可以治,民可以安,戰可以勝,守可以固。吳起說:“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亭。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啟于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后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戰,則士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矣。”(同上)吳起認為,只有先教百姓,親近萬民,才能和服萬民,用萬民而造大事,以萬民齊戰,才能取勝。如果一個國家上下、軍民出現了“四不和”,就不能興兵作戰。“和民”之要,在于“修文德”,即用道、義、禮、仁“四德”來教育、規范人民。修好“四德”,做到“四和”,就使軍政、軍民團結,軍隊內部團結,齊心協力,行動一致,英勇殺敵,無往不勝。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選賢才、重賢能。當魏武侯問吳起“愿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時,吳起的回答是:“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同上)就是說,要選拔重用那些有道德、有才能的賢人,使之擔當軍政要職,以利于治國安民、領兵打仗,對于那些無德、無才的不肖之人,不要提拔重用,這樣軍陣就鞏固了。同時要安民田,親官吏,使民有田宅,安居樂業,親近統管他們的各級官吏,以利于發展生產,增強國力,鞏固國家。
“外治武備”就是要加強國家軍事力量的建設,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吳起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軍治軍思想,舉凡教育訓練、軍紀軍法、精兵建設、選帥任將等問題,均有深入的闡述:第一,加強戰備。吳起認為,搞好戰備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關鍵,所謂“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吳子·料敵》),“戒”就是戒備、戰備之意。為此,吳起非常重視軍隊的軍事訓練,他認為,將士在作戰中戰死往往是由于其軍事技能不熟練,作戰失敗的原因也多由于戰術要領沒有掌握,所謂“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吳子·治兵》)。第二,嚴明賞罰。吳起主張從嚴治軍,強調用嚴格的軍紀軍法來約束將士,做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有信”(同上),如此,可以使“三軍威服,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吳子·應變》)。反之,如果“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則“雖有百萬,何益于用”(《吳子·治兵》),即使有百萬大軍,也無益于勝利。第三,簡募良材。吳起提倡組建特種精銳部隊,以防備、應付突然不測事件,“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其思路是通過精心挑選,按照士卒的特長,組成不同的編隊,所謂“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逾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吳子·圖國》)。第四,選帥任將。吳起對將帥提出了嚴格的要求,總的原則是要文武兼備,剛柔相濟,所謂“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作為將帥還要做到“五慎”:“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吳子·論將》)“理”即治理,指統率三軍如同治理卒伍,要做到井然有序;“備”即戰備,指軍隊一旦出動,就要進入臨戰狀態;“果”即果敢,指跟敵人作戰時,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戒”即警戒,指在戰爭勝利時,要如同戰爭開始那樣,保持高度戒備;“約”即簡要,指給軍隊下達命令,應該簡明而不繁瑣。總之,為將者的膽識、才干,要足以統率部隊,戰勝攻取。
吳起的戰爭觀深刻反映了戰國時期軍事斗爭的一般規律,適應了新興勢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和從事兼并戰爭的需要,具有顯著的進步色彩和重要的軍事學術價值。雖然他未能真正揭示出戰爭的起因和戰爭的性質,但他對這些問題的論述卻是超越前人的,在中國兵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1][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417.
[2]薛國安,楊斐.吳子新說[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