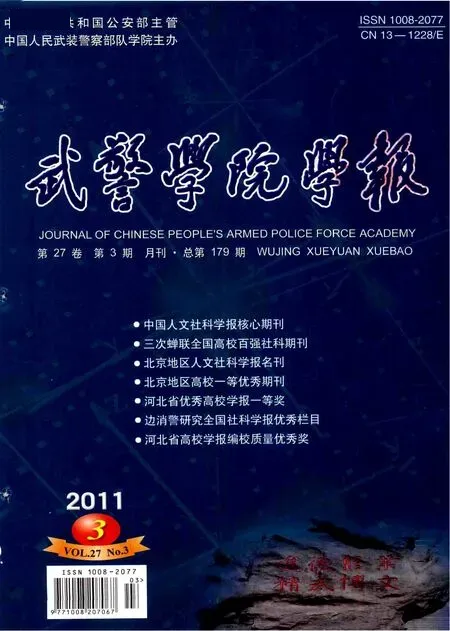非法拘禁罪之“共犯與身份”問題探究
●陳 山
(四川師范大學法學院,四川成都 610066)
(本欄責任編輯、校對 劉彥超)
“共犯與身份”問題主要涉及:無身份者加功身份犯之有身份者,或者身份犯之有身份者加功無身份者,應該如何定罪處罰?[1]雖已有大量文獻對此予以研究,迄今,并未形成任何有意義的理論共識,更遑論實踐中存有統一做法。本文嘗試以非法拘禁罪為樣本,對此傳統問題作深入的探究。
一、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
我國刑法第238條第四款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規定從重處罰。”通說認為,這規定了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2]
(一)不純正的身份犯的觀念
不純正的身份犯是與純正的身份犯相對提出的概念,也被稱為“不真正的身份犯”、“加減的身份犯”。具體而言,何謂不純正的身份犯,大陸法系與我國(大陸地區)刑法理論回答頗有差異。
日本學者大谷實指出,純正的身份犯是行為人由于具有一定身份才具有可罰性的犯罪,如受賄罪,其成立就需要公務員、仲裁人的身份。不純正的身份犯,是行為人具有一定身份,同一般情況相比,其法定刑或者較輕、或者較重的情況,也稱加減的身份犯,日本刑法中的業務墮胎罪就是不純正的身份犯。[3]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洪福增講到:“身分犯有兩種,其一,為真正的或純正的身分犯(echte Sonderdelikte)。此指條文所規定犯罪構成要件之犯罪主體,必須具有一定身分者(具有特定關系者亦同)始能犯之,無此一定身分之人即不構成犯罪也……其二,為不真正的或不純正的身分犯(unechte Sonderdelikte)。此指刑法將一般無犯罪主體的限制之犯罪……規定具有一定身分或特定關系者犯之,則予以加重、減輕科刑或免除其刑之犯罪類型也。”[4]兩位學者的把握基本一致:純正的身份犯是一種基本的犯罪類型(基本犯),行為人欠缺特定身份,根本不可能成立犯罪;不純正的身份犯是一種與基本犯相較的修正的犯罪類型,行為人具有特定身份成立此種修正的犯罪類型,加減刑罰(加重、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行為人不具有特定身份可以成立基本犯。正如臺灣地區學者蔡墩銘所繪示意圖所展示的那樣(如圖1所示)[5]:

可見,大陸法系通說是以犯罪類型來劃分純正的身份犯與不純正的身份犯的。與之不同,在我國(大陸地區),通說以身份對定罪或者量刑的影響來劃分兩者。[6]例如,張明楷曾論及:“身份犯包括真正的身份犯與不真正的身份犯。真正的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為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不真正的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響定罪但影響量刑的情形。”[7]
我國通說與法制現狀相關聯。在我國刑法中,依托于基本犯具有加減刑罰效果的修正的身份犯類型往往缺少獨立的法定刑與罪名。例如,我國刑法第243條第一款的誣告陷害罪(基本犯)與第二款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誣告陷害罪(不純正的身份犯),第307條第一款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基本犯)與第二款的“司法工作人員”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不純正的身份犯),等等。在大陸法系法制中,具有加減刑罰效果的修正的身份犯類型都有自身相對獨立的法定刑與罪名。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284條第一款的過失傷害罪(基本犯)與第二款的業務過失傷害罪(不純正的身份犯)、德國刑法第212條的故意殺人罪(基本犯)與第213條的義憤殺人罪(不純正的身份犯)、日本刑法第252條的侵占罪(基本犯)與第253條的業務侵占罪(不純正的身份犯)。
我國通說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其一,對我國刑法中明確需要利用身份便利(特別是“利用職權、職務便利”)的修正的無獨立法定刑與罪名的身份犯類型(例如,刑法第238條第四款)處理可能失當。需要利用身份便利的修正的身份犯類型會帶來相對于基本犯更多的不法,無身份者加功有身份者對這種多的不法是有影響力的。所以,在認為共犯成立僅僅關乎定罪的一般觀念下,無身份者的加功就變成了無意義的事件,從而使得在共犯處理上違背“違法的連帶性”原理。其二,事實上否認了具有獨立罪名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存在。從立法技術上講,修正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可能是更加方便地安排在基本犯的法定刑與罪名之下。于是,具有加減刑罰效果的特定身份由構成要件要素跌落為僅僅影響量刑的情節。但是,并無法排除具有加減刑罰效果的修正的身份犯類型在刑法中有獨立法定刑與罪名的可能性。換言之,當刑法個別地規定脫離基本犯的不純正的身份犯的情形,就會被視做純正的身份犯。例如,我國刑法第382條的貪污罪與第264條的盜竊罪之間就具有不純正的身份犯與基本犯的關系[8],而在我國通說中,貪污罪多被視為純正的身份犯。[9]這種做法的問題是,由于純正的身份犯被定位為基本犯,觀念上,基本犯又是刑罰創設的基礎,而導致刑罰創設的只能是不法侵害。所以,不純正的身份犯被定位為純正的身份犯后,那些可能屬于責任性質的身份就會被當然地釋讀為違法性質的身份,最終導致在共犯處理上違背“責任的獨立性”原理。①關于“違法的連帶性”、“責任的獨立性”的涵義,請參考后文“共犯之處罰根據”部分。
因此,在純正與不純正的身份犯的劃分問題上宜主張以犯罪類型而論,既承認與基本犯同一罪名的不純正的身份犯,也承認與基本犯不同罪名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同時,宜堅持共犯成立的問題不僅處理定罪問題(確定罪名)也處理量刑問題(確定同一罪名之下的犯罪類型)。這樣既尊重了我國的法制現實,也兼顧了共犯成立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我國刑法中的確存在大量的不純正的身份犯依附于基本犯的實情,如果認為共犯成立僅僅處理定罪,就無法將共犯成立的實際效果(“違法的連帶性”)貫徹到底。另一方面,回避了一律將有獨立法定刑與罪名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僅僅視為違法性質的身份犯的風險。
(二)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的規范特質
身份犯有什么樣的規范特質,決定著身份犯所引起的事實與法律效果能否被其他參與者所支配或者共同擔當。
大陸法系理論對身份犯的規范特質有一定的探討。日本學者山中敬一認為,應當將純正的身份犯與不純正的身份犯作不同的把握,純正的身份犯的規范特質是不法侵害,惟有身份者的實行行為存在侵害其特別的法益或者使其危險化是可能的,而不純正的身份犯的規范特質則是不法基礎上的特別責任,即特別地“違反期待可能”。[10]這是大陸法系理論上的通說,日本學者大谷實、大塚仁等均予以支持[11]。有少數學者,如日本學者西田典之[12]、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許玉秀等[13],在承認責任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的同時,還承認違法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即認為不純正的身份犯的身份既有責任性質的,也有違法性質的。與大陸法系相較,我國理論對這一問題探討較少。應當說,不純正的身份犯之身份究竟是加減責任性質的,還是加減違法性質的,本身是個法制中的立法事實問題。從可能性來看,立法者既可以在基本犯的基礎上添加責任性質的身份形成責任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也可以在基本犯的基礎上添加違法性質的身份形成違法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是否存在這些可能的類型,必須以刑法中的實際規定為準。就我國刑法而論,兩者都是存在的。例如,我國刑法第243條第二款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誣告陷害罪,即為責任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屬于責任性質的身份,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從重處罰,體現了刑法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更高程度的守法期待。還有我國刑法第307條第二款的“司法工作人員”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第349條第二款的“緝毒人員或者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等也是責任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至于違法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在我國刑法中,如有刑法第253條的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基本犯是刑法第252條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刑法第382條的貪污罪(基本犯是刑法第264條的盜竊罪)等犯罪。與責任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相比,違法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往往有“利用身份便利”(“利用職務便利”、“利用職權便利”等)的立法表述,或者在解釋上需要類似的要素。這些要素的存在,影響了行為人行為的不法,即增添了違法性質的身份帶來的更高程度的不法。例如,貪污罪與盜竊罪等相比,不僅侵害了財產權,還違反了國家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責義務要求。[14]
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是在基本犯基礎上添加違法性質身份形成的違法性質的身份犯。相對于基本犯而言,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增添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一違法性質的身份,在刑法的表述中明確要求“利用職權”便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非法拘禁他人的,在基本犯侵犯他人的人身行動自由的基礎上增添了職責義務違反的不法因素。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是一種以義務違反和法益侵害為違法性本質的身份犯。盡管絕大多數犯罪的不法本質應當以法益侵害為基準,但是,對于像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此類的身份犯而言,如果不結合義務違反就無法準確地說明其規范特質。“今日的刑罰法規,都是以從我們個人的觀點來看屬于生活利益或者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中的利益為保護的對象,可以認為犯罪是以法益侵害為其核心來構成的”,但是,“必須直率地承認犯罪中也存在應該作為義務違反來把握的一面”[15]。
二、共犯之處罰根據
無身份者加功有身份者或者有身份者加功無身份者,考量是否成立身份犯的共犯,必須有堅實的共犯之處罰根據立場。[16]探析共犯之處罰根據旨在回答:刑法分則僅規定了實施構成要件行為的正犯可罰,為什么刑法也將處罰擴展到幫助犯、教唆犯等共犯形態?即“問題是,共犯并沒有親手實施犯罪,為什么也要受到處罰?”[17]
關于共犯之處罰根據的理論有:“可罰性借用論”、“責任共犯論”、“違法共犯論”、“因果共犯論”[18]。可罰性借用論認為,共犯本身沒有刑法上的可罰性,而是借用了正犯的可罰性。按此,正犯缺乏可罰性,共犯就不可罰。例如,甲教唆乙盜竊自己(乙)父母的財物,一般認為,乙的行為屬于親屬相盜,乙具有阻卻可罰性事由,根據可罰性借用論,甲也不可罰。可罰性借用論認為共犯自身沒有獨立的可罰性,這忽視了共犯行為對法益的侵害性,同時,也與罪刑法定主義相悖,畢竟自身不可罰就不應當處罰。責任的共犯論認為,共犯之所以需要處罰是因為其引誘正犯陷入有責任的狀態,在道德上應該受到譴責。按此,正犯有阻卻責任的因素,共犯就不能成立。例如,丙教唆無責任能力的丁傷害被害人,丙并不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而應成立故意傷害罪的(間接)正犯。責任共犯論一度是我國刑法理論上的通說[19],由于有明顯的法律道德化的傾向,影響力正在明顯地減弱。違法共犯論認為,共犯的違法行為引起了正犯的違法行為。按此,正犯的行為違法,違法的共犯即能成立。例如,戊教唆己殺死自己(戊),己是故意殺人罪的正犯,戊就成立故意殺人罪的教唆犯。顯然,違法共犯論的結論是不當的。因為,連自殺都不違法,教唆他人殺死自己也就不應當違法。今天,正在成為通說的共犯之處罰根據論是因果共犯論之下的“純粹的惹起說”、“修正的惹起說”、“混合的惹起說”。純粹的惹起說認為,共犯之所以需要處罰是因為共犯行為本身對法益的侵害性,全面肯定違法的相對性。例1,A按照B的要求對B實施了重傷害行為,A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正犯,B要求A侵害自己的行為由于沒有法益侵害性——他自己就是法益的主體——就不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B無罪,承認“無共犯的正犯”。例2,C慫恿D實施重傷自己(D)身體的行為,D由于是法益的主體故不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正犯,D無罪,C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承認“無正犯的共犯”。純粹的惹起說對于必須透過正犯行為來侵害法益的共犯而言,忽視了共犯違法的連帶性,可能會過分擴大處罰的范圍,并不妥當。修正的惹起說認為,共犯之所以需要處罰是因為共犯引起的正犯行為具有法益侵害性。依據修正的惹起說,例1中,A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正犯,B也連帶地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即否認“無共犯的正犯”,例2中,D不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正犯,C就不能連帶地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即否認“無正犯的共犯”。修正的惹起說雖注意保護法益,但在共犯的違法性上過分強調共犯對正犯的從屬性,反而有違法益保護的精神。依據混合的惹起說,例1中,A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正犯,B并不能連帶地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即承認“無共犯的正犯”,例2中,D不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正犯,C就不能連帶地成立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即否認“無正犯的共犯”。混合的惹起說既重視法益的保護,又重視共同犯罪的規范結構,將違法及法益侵害的個別化與共犯的從屬性妥當地結合起來,最為妥當。
既然承認混合的惹起說之共犯之處罰根據,原則上就要堅持“違法的連帶性”、“責任的獨立性”。只要惹起了正犯行為違法,如果沒有特別地阻卻法益侵害的事由(例如,加功者本身即為被害人),就應當肯定共犯成立,將正犯違法行為對位的刑罰擴張地適用于共犯。同時,正犯之特別責任要素對位的刑罰不能適用于加功者,應否認共犯的成立。將共犯之處罰根據理論貫徹到“共犯與身份”問題之上,無身份者加功于違法性質的身份犯之有身份者,無身份者能夠成立違法性質的身份犯的共犯;無身份者加功于責任性質的身份犯之有身份者,無身份者不能成立責任性質的身份犯的共犯。
三、間接正犯
對于有身份者加功無身份者,尚需特別地探討身份犯之間接正犯成立的可能性。[20]意思支配他人實現構成要件的,意思支配者即為間接正犯,承擔正犯之責。間接正犯是正犯類型之一,與直接正犯相對。間接正犯是為了彌補區分正犯與共犯的處罰漏洞形成的概念。單一正犯論認為,凡對實現構成要件有原因力者都是正犯,反對區分正犯與共犯。[21]但是,我國現有刑法是區分正犯與共犯的,刑法第29條就明文規定了教唆犯的概念、第27條也蘊含了幫助犯的概念。這就需要間接正犯的理論工具。
張明楷的研究顯示間接正犯的主要類型有[7]:利用無辨認能力、控制能力者的行為,例如,教唆5歲的孩童在被害人的食物中投放“蒙汗藥”,使其陷入無行動能力的昏睡狀態;利用使他人不能抗拒的強制力實現構成要件,例如,用槍指著他人的頭,迫使其將被害人捆綁;利用他人無知或者過失的行為,例如,向警察誣告被害人強奸了自己,警察依法將被害人逮捕。這些意思支配者都可謂是非法拘禁罪(基本犯)之間接正犯。
對于有身份者意思支配無身份者實現身份犯之構成要件造成違法性質的身份犯之不法事實的,如何處理,理論上還有很大的爭議。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日本學者草野豹一郎主張,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謀,形成共同意思主體,無身份者取得身份犯之身份,故而無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直接正犯,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教唆犯。[22]我國學者莫洪憲亦持類似看法。[23]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柯耀程主張,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直接正犯,無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幫助犯。[24]我國大陸地區學者何慶仁也予以支持。[25]德國學者耶賽克[26]、日本學者大塚仁[15]等主張,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間接正犯,無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幫助犯。這是大陸法系的通說,目前,在我國也居于主流地位。[7]第一種觀點立足于共同意思主體的主觀主義刑法觀念主張無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正犯,完全忽視身份對構成要件定型的重要意義,并不妥當。第二種觀點認為有身份者為直接正犯,雖然重視構成要件的定型性,卻沒有尊重有身份者并未親自實現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實非可取。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即認為,有身份者意思支配無身份者作為實現構成要件的工具,有身份者當然是間接正犯,無身份者盡管實現了構成要件,由于欠缺身份,無法成立身份犯的正犯,在符合共犯之處罰根據的前提下,可以成立違法性質的身份犯的共犯(幫助犯)。
四、非法拘禁罪之“共犯與身份”問題的解決
欲解決非法拘禁罪之“共犯與身份”問題,應從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的規范特質出發,綜合考慮共犯之處罰根據與間接正犯因素,并將其放置于我國刑事法制之中,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無身份者加功有身份者非法拘禁他人
第一種情形,無身份者教唆、幫助有身份者非法拘禁他人的。例如,普通人A為打擊生意上的競爭對手B,教唆民警C利用職權的便利非法拘禁B。
A惹起了C侵害B的不法行為,C成立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的正犯,A應成立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的共犯。具體地說,C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正犯,A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教唆犯。由于我國刑法中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缺乏獨立的法定刑與罪名,裁判上,應對A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的教唆犯,對A適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教唆犯之刑,即在“非法拘禁罪”基本刑的基礎上“從重處罰”,并考慮教唆犯因素對刑罰的影響;應對C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的正犯,對其適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正犯之刑,即在“非法拘禁罪”基本刑的基礎上“從重處罰”。
第二種情形,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實行非法拘禁行為拘禁他人的。例如,普通人D與民警E前往被害人F的住處,E亮出自己的警官證與D一起將被害人F用手銬銬上帶走,后將被害人關押在公安局的預審室里,D與E一起共同看守。
無身份的D加功有身份的E共同實施了非法拘禁行為,E的違法性質身份會帶來加重的違法后果,無疑D與E的行為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共同犯罪。E自然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正犯。關鍵是,D能否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共同正犯。對于無身份者是否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問題,理論上大致有兩種方案:一是基于形式的客觀說[10],認為共同實行者即成立共同正犯;一是基于義務犯的觀念,認為對于義務違反類型的身份犯而言,必須考察行為人是否具備特定的義務身份資格,具備特定的義務身份資格者方能成立正犯(包括共同正犯)。[27]根據前者,D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共同正犯,裁判上,對D與E均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的正犯,都適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正犯之刑。根據后者,E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正犯,D僅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幫助犯),裁判上,應對E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的正犯,適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正犯之刑,應對D認定為“非法拘禁罪”的正犯,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幫助犯)之刑與“非法拘禁罪”正犯之刑中選擇較重的處罰。筆者贊同義務犯的觀念,“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是義務違反類型的身份犯,故支持后一方案。
(二)有身份者加功無身份者非法拘禁他人
民警G利用職權便利得知自己的好友H的債務人I在某賓館住宿,G即刻通知了H,并叮嚀H帶上自己(G)的警官證和手銬。H到某賓館處,量出警官證要求服務員帶其到I所住房間查房,H進入房間后立即用手銬將I銬在房間的欄桿上。
可以認為,有身份的G意思支配無身份的H實現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之構成要件,G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間接正犯,基于違法的連帶性,H成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幫助犯。還必須考慮與基本犯的共犯競合的問題。一方面,以G的行為為中心,G意思支配實現了非法拘禁罪之不純正的身份犯,G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間接正犯,H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幫助犯。另一方面,以H的行為為中心,H本身可以獨立評價為非法拘禁罪之基本犯的正犯,所以,G也成立非法拘禁罪之基本犯的共犯(教唆犯或者幫助犯)。因此,對G與H應選擇處罰更重的評價適用法律。從刑法規定的處刑輕重來看,G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間接正犯,即對其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并適用“從重處罰”的規定,H宜為非法拘禁罪之基本犯的正犯,即對其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僅適用基本犯一般的刑罰。
五、余論
非法拘禁罪之“共犯與身份”問題的處理方案具有標本意義。在我國刑法中,凡在形式與規范特質上類似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非法拘禁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類型,無身份者加功有身份者,無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共犯,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正犯,最后,有無身份者均應以基本犯的正犯或者共犯定罪,適用刑罰時方才考慮身份犯的共犯關系帶來的影響;有身份者加功無身份者,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間接正犯或者基本犯的共犯,無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幫助犯或者基本犯的正犯,最終,有無身份者均應以基本犯的正犯或者共犯定罪,適用刑罰時方才選擇更重的處罰方案。上述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適用于獨立于基本犯規定的違法性質的不純正的身份犯的“共犯與身份”問題。不同的是,身份犯的共犯關系由僅僅影響刑罰適用的量刑問題升格為確定罪名適用的定罪問題,即需確定:對于有無身份者,究竟應適用基本犯的罪名還是應適用不純正的身份犯的罪名。
[1][日]大谷實.共犯與身份[J].王昭武,譯.法學評論,2005,(4).
[2]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0.
[3][日]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M].黎宏,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409.
[4]洪福增.刑法之基本問題[M].臺灣洪福增發行,1964:268-270.
[5]蔡墩銘.刑法精義[M].臺灣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115.
[6]張本勇.純正身份犯的共犯問題[J].政治與法律,2006,(6).
[7]張明楷.刑法學[M].法律出版社,2007:127,332,334.
[8]閻二鵬.身份犯之共同犯罪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27-34.
[9]肖中華.真正身份犯之共犯問題探討[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3,(1).
[10]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150,629.
[11]蔡世祺.共犯與身分——以刑法第三十一條為中心[D].臺灣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5:170-173.
[12][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M].劉明祥,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43.
[13]許玉秀.刑事法之基礎界限[M].臺灣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486.
[14]李恩慈.論貪污罪共犯[J].中外法學,1999,(6).
[15][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M].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91 -92,285.
[16]林冠宏.共犯處罰根據之研究[D].臺北大學法律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1.
[17][日]曾根威彥.刑法學基礎[M].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5:135.
[18]陳山.比較法視野下的“共犯與消極身份”[J].政治與法律,2010,(2).
[19]楊金彪.責任共犯說批判[J].法律科學,2006,(6).
[20]甘添貴,等.共犯與身分[M].臺灣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271.
[21]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M].臺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160.
[22][日]吉川經夫.共犯與身分[J].洪復青,譯.臺灣軍法專刊,1969,(2).
[23]莫洪憲,李成.職務犯罪共犯與身份問題研究[J].犯罪研究,2005,(6).
[24]黃麗岑.特別犯之參與關系——以刑法第三十一條為中心[D].臺灣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157.
[25]何慶仁.義務犯研究[D].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160.
[26][德]耶賽克,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811.
[27]陳志輝.義務犯[J].臺灣月旦法學教室,(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