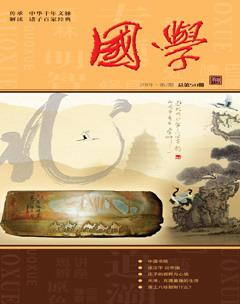史邊喁語
李肖雅
腹誹
腹誹,也叫“腹非”,即嘴上不說,心里卻嘰里咕嚕,認為不對。先秦時,好像還沒有這罪名。周厲王的時候,統治很嚴酷,說話相當危險,弄不好就被殺掉,老百姓在路上見面都不敢用嘴巴打招呼,使一下眼色就拉倒。到了秦王朝,特別重視輿論一律,亂說也不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但是,如果“不語”,好像不算犯罪。
西漢建立后,劉邦的子孫漢武帝設立了這個罪名。據《史記·平準書》所載,顏異早年為濟南亭長(大體相當于現在的村主任之類吧),為人耿直為官清廉,最后做到了九卿位置。在一次幣制改革中,皇帝及當時的廷尉張湯主張造白鹿皮幣,一個單位價值四十萬。顏異認為如此一來,這白鹿皮與它本身的價值差的太多了。不久,有人因別的事情告發顏異,漢武帝讓張湯辦理此案。經審問,查出顏異曾接待過一個客人。這個客人和顏異談到,朝廷新令有不方便之處,顏異聽后沒有說話,只是稍微動了動嘴唇。張湯做出的結論是:“不入言而腹誹,論死。”也就是說,顏異雖然口頭沒有反對這個政策,可他肚子里是反對朝廷的,所以當斬!結果,顏異掉了腦袋。
我們也常常責備天下奴才太多,不敢講真話,其實動一動嘴唇都可以惹禍的環境哪里會有真話?能夠在沉默中不被疑為“腹誹”就不錯了。
隱太子
隱太子即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李建成、三弟李元霸、四弟李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唐高祖多子,十八個后妃為他生了二十二個兒子。按照傳統立儲原則,登位之初,唐高祖就確立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
李建成能被立為皇嗣,并非僅僅靠嫡長子的身份,身份和功勞兩種成分加在一起,可能是他成為太子的基礎因素。《新唐書》說他“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舊唐書》稱:“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未必是真。
據說武德九年(626)夏,李建成、李元吉以征討突厥為契機,奪去秦王府的精兵強將,伺機殺死李世民。形勢如此,便有了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的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引箭射死李建成,李元吉被尉遲敬德射死。三天后,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八月八日,唐高祖李淵宣布自己退位為太上皇,由李世民繼位。歷史從此進入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
李建成是否如歷史所述的那樣不堪,因為記述他的史料“一邊倒”,難于刨根尋底。李淵也是南征北戰之人,諳熟政治運作,怎么會把社稷江山交給無德無才之人呢?勝王敗寇,是歷史的一個特點,同是一個人,當他登上勝利者的高位時,四周會響起一片歡呼聲,贊美之音也會不絕于耳;但當他成為別人的階下囚以后,唾罵、詛咒者也會成行成列。李建成的命運不能證明他的能力,只能證明他是失敗者。
起居注
“起居注”即皇帝日常言行的記錄,由皇帝的近侍臣工記錄和編撰。
不少握有權力者看重起居注,因為那里邊不僅記錄著他們的言論,也記錄著他們的行動。我們把白紙黑字看得很神圣,那是證據。對當時的事,當時的人還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后代就未必清楚了,靠什么寫歷史?一是地上的文字資料、實物,二是地下的考古資料。不管什么朝代,凡做史,閱讀起居注是基礎工作。因為重要,權力持有者總希望記錄的人把自己描畫得高大一些。據說明清多位皇帝都重修過“實錄”,為什么如此?不言自明。
《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想看起居注,主管這方面工作的是諫議大夫褚遂良。據史書說褚遂良拒絕了李世民的要求。實情如何,當時的人早已作古,后人不好亂猜。太宗問:“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褚遂良回答說:“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這是貞觀十三年(639)的事。后來李世民在房玄齡那里看到了部分國史,然后發表了重要意見,囑咐大家要堅持歷史真實。
有人說起居注是監督皇帝的。從理論上講,可能這樣,但在實際中要打不小折扣。連監督者的小命兒都歸皇帝所有,他怎么敢、怎么能監督?這里所謂的監督,不過如門上的一把無作用的鎖,道德特別高尚者可能見鎖而返,無德者就可能破門而入了。
“三吏三別”
世人稱《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和《無家別》為“三吏三別”。這六首詩很著名,凡講杜甫,很少有不提這六首詩的。怎么個好法,治文學者多有論述,在下不必饒舌。
唐人詩歌豐富多彩。多彩之一便是風格多樣,可以頌仙,也可以唱鬼,更可以詠史。詠史,既可以談陳年舊事,也可以述說當代。比如《石壕吏》寫官吏抓人,老百姓痛苦不堪。哪個年代的官吏?杜甫眼皮子底下的年代,也就是當代。文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描寫當代,這很了不起,不是哪個統治者都能做到。《容齋隨筆》“續筆”卷二說:“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
看“三吏三別”,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