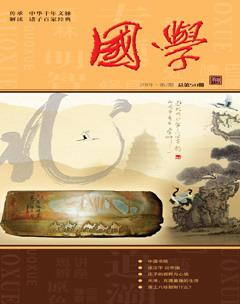齊桓公的謀事之道
黃樸民
在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中,晉文公“譎而不正”,楚莊王在當時中原人眼里算是“非我族類”,宋襄公傻得有些可笑,秦穆公功業(yè)偏于一隅,唯獨齊桓公才是貨真價實的一代霸主,以至孔子稱道他“正而不譎”,孟子謳歌他“五霸桓公為盛”。
齊桓公的“正”,說白了也很尋常,就是他的處事從根本上合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中庸、節(jié)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實現(xiàn)自己既定的戰(zhàn)略目標。用今天的話說,齊桓公的“厲害”表現(xiàn)在他的太極推手功夫,也就是穩(wěn)重。這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戰(zhàn)略上的大手筆!這種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實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不能至也。
齊桓公的成功,取決于他的穩(wěn)重。由于穩(wěn)重,他才善于權(quán)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汲取教訓,盡快剎車。對于政治家而言,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歷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計劃和方法有問題,但或因礙于面子,或因賭口意氣,或因心存僥幸,總是在那里死頂硬撐,結(jié)果事情是越來越糟糕,直弄到山窮水盡,無法挽回。然而,齊桓公與他們不同,他懂得該撒手時就撒手的道理,所以就成功了。
齊桓公剛登基時,也一樣雄心勃勃,血氣方剛,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yè),早早確立起齊國的霸權(quán),汲汲于“欲誅大國之無道者”。可是,他的熱情之火,很快便讓長勺之戰(zhàn)那一大盆冷水給澆滅了。他引以自豪的強大齊軍,居然讓曹劌率領(lǐng)的魯國兵馬在長勺之戰(zhàn)中殺得丟盔棄甲、慘不忍睹。不過這次出乎意料的慘敗,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使齊桓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tài)得以平復下來。既然靠單純的戰(zhàn)爭手段連魯國這樣軍力平平的國家都擺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對付比魯國強大十倍的楚國,去對付比魯軍能打仗的戎狄,豈不是自討沒趣?齊桓公馬上調(diào)整自己的爭霸戰(zhàn)略,改急進冒取為穩(wěn)重待機,變單憑武力為文武并舉。正是這種穩(wěn)重的做法使他一步步接近事業(yè)的頂峰。
齊桓公的穩(wěn)重,還表現(xiàn)在他善于正確判斷形勢,根據(jù)實際情況與對手作必要的妥協(xié)。善于妥協(xié),本身就是戰(zhàn)略運籌中的高明藝術(shù),是尋求戰(zhàn)略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方面的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無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標志。齊桓公就是這樣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召陵之盟,充分體現(xiàn)了他通過妥協(xié)的方式,實現(xiàn)其戰(zhàn)略利益的穩(wěn)重風格。當時,楚國兵鋒咄咄北上,成為中原諸侯的巨大威脅。“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在這種情況下,齊國當縮頭烏龜是不成的,保護不了中原中小諸侯,但如果心血來潮,同楚國真刀真槍干上一仗,也不是正確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是組織起一支多國部隊,兵臨楚境,給其施加巨大的政治、軍事、外交壓力,迫使對手作出一定的讓步。于是,齊桓公與楚國方面在召陵地區(qū)聯(lián)袂上演了一場妥協(xié)大戲。楚國承認不向周天子進貢“苞茅”的過錯,表示愿意承擔服從“王室”的義務(wù),給了齊桓公所需的臉面;而齊桓公也達到了警告楚國、阻遏其北進迅猛勢頭的有限戰(zhàn)略目的。這種戰(zhàn)略上不走極端、巧妙妥協(xié)的做法,可能會讓習慣于唱“攘夷”高調(diào)的人覺得不夠過癮,可它恰恰是當時齊桓公惟一可行的正確抉擇。
齊桓公的穩(wěn)重,更表現(xiàn)為他善于把握時機,算盤精明,從不做賠本的買賣,總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換回最可觀的利益。他讓后人津津樂道的幾件大事,如遷邢、存衛(wèi)、求助周室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買賣。譬如,他遷邢、存衛(wèi),并不是在邢國與衛(wèi)國一遭到戎狄的攻擊時就出兵施援,而是在局勢明朗之后才展開行動,所以當齊兵姍姍來遲,抵達邢、衛(wèi)時,邢、衛(wèi)早已被戎狄所攻破。如此一來,齊軍并未遭到損失,但卻贏得了抗擊戎狄、拯救危難的美譽,齊桓公本人也幾乎成了人們的大救星。
正因為齊桓公處事穩(wěn)重,深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盡管他在霸業(yè)上的成熟似乎不及晉文公、楚莊王,然而他的歷史形象卻遠比其他霸主來得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