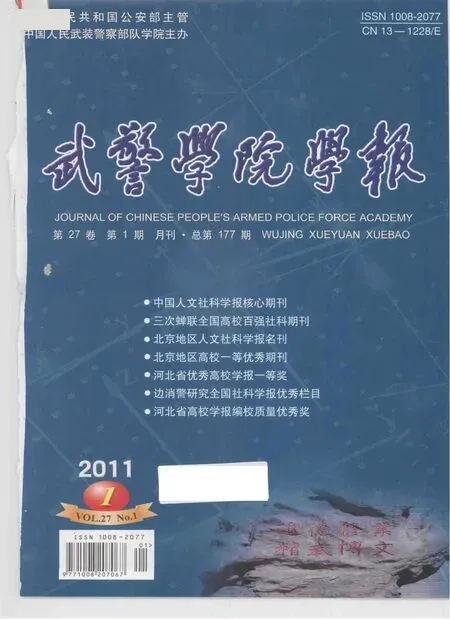軍事權的憲政解讀
●仲崇玲
(武警學院基礎部,河北廊坊 065000)
暴力一直是目的達成的最終手段,而權力則是統治秩序的外顯表達。當“暴力”發展成為“權力”時,合法暴力的壟斷者——國家便應運而生。自此,暴力便以國家軍事權的面貌出現。然而,人類的無數罹難證明,暴力這種事實性力量取得了軍事權的合法形式后更容易對自由構成威脅。于是,基于對軍事權潛在危險性和強大破壞力的憂慮,近代憲法挺身而出,以其特有的將“組織性規范”轉化為“程序性規范”的效用,力圖將軍事權安定在其預設的框架之內。自此,憲法之于軍事權的規制便是必不可少的了,軍事權的憲政解讀也逐漸被納入理論研討的視野。
一、沖突的消解:憲政理念中的軍事權
(一)軍事權的集權性與憲政的分權理念
軍事權并非與人類的憲政文明天然相容。從理論上講,軍事對抗因為具有瞬息萬變的偶然性和生死攸關的緊迫性,在軍事權的行使過程中,便不能允許因權能的不完整而在戰場上頓生肘腋,也不能允許軍事命令在兩軍對壘的形勢下被拖沓地傳達和敷衍地執行。更為重要的是,軍事對抗活動往往還具有同仇敵愾的民族性,需要社會資源給予軍隊最無私和最迅捷的支援。而這恐怕只有軍事權的乾綱獨斷甚至與國家最高統治權的合二為一方能做到。所以,盡管“專制政權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1],但前憲政時代的人類歷史仍然表明,軍事權分散的國家大多逃不掉四分五裂的宿命,聲名顯赫的帝國卻往往因為軍事權與統治權的高度契合而繁榮昌盛。
然而,在憲政語境里,任何權力都不允許強大到在整個國家的權力結構體系中占據絕對優勢的地步,軍事權也概莫能外。因為,“只有制約和均衡的格局才能限制掌權者的私欲膨脹,才能使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不依賴于掌權者的個人品德或去留,因而也就為社會的穩定與繁榮提供了一個持久而可靠的制度安排”[2]。所以,為盡量保持與其他權力的動態平衡和良性互動,憲政國家通常將軍事權分解為決定戰爭與和平的權力、統率與管理軍隊的權力、進行防務建設的權力以及實施軍事裁判的權力,并以不同的模式交由不同的國家機關掌控,在國家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中逐漸消解軍事權的集權性,謹慎地維系著它的安定。
(二)軍事權的強隸屬性與憲政的平等理念
原始初民的暴力行為通常是個體化的。隨著雇傭軍的出現,“軍隊不再是瑞士式粗暴的民眾,不再是封建式的好戰的個人的群體;它變得具有良好的組織性,每一英寸部分都聽從上級指揮”[3]。于是,軍事權便成了“有組織的暴力”[4]。在這個暴力組織中,“強隸屬性”是其高效運作的重要保障。由于它的存在,當軍事權以“漫射”狀從權力中心出發并逐次通過中間層后,其強度的減弱、方向的偏離甚至發生折射的可能都大大降低。軍銜制的廣泛施行更使得軍事權在等級差別的宏觀背景下昭然若揭地將強隸屬性定義為自己最顯著的特征。
然而,近代憲法的呼喊卻振聾發聵——“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是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于是,憲政理念的平等觀促使軍人要求擺脫特別權力關系的束縛,與普通公民一樣,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的保障。只有當軍事勤務所必需時,才可以受到必要的限制。并且這種限制也只能是局部限制,而非全面剝奪。這一趨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軍事權運行中強隸屬性的消解與反動。
(三)軍事權的極端性與憲政的正義理念
盡管德國天才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歷史學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我們不應該把戰爭看成是一種單純的暴力和消滅敵人的行為,不應該根據這種簡單的概念按邏輯推出一系列與現實現象不相符合的結論。”[5]但他仍無法否認戰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極端性。它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是“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5]我們說,雖然戰爭并不是軍事權力運行的惟一場域,但“它的這種強烈的暴力,如同一種普照的光,使得其他非戰爭的軍事活動的特點變了樣,從而具有了暴力的性質”[6]。因而,源于暴力的軍事權無論是在戰爭領域,還是在非戰爭的軍事活動領域,便都天然地帶有了極端性的可能。
但是,安全與存續對于國家來說是絕對的嗎?或者說,可以為了國家的安全與存續而將軍事權的極端性發揮到極致嗎?現代憲政理念對此給予了否定的回答。正如弗里德里希(C.J.Friedrich)所闡述的那樣:“國家安全與存續的問題正像它所面對著獨立自主的政府一樣,也面對著立憲的秩序,面對著法治政府。……思想家不能像霍布斯或其他馬基雅弗利的追隨者那樣,置秩序的正義不顧,證實秩序的正當性,輕易地為國家的最高價值辯解。”[7]所以,按照正義理念,戰爭的發動需是符合國際法則的,暴力手段的使用需是遵從道德底線的,社會資源的征用需是給予必要補償的。這一切便構成了對軍事權極端性的憲政約束。
二、艱難的抉擇:憲法文本中的軍事權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事實上的動機。”[8]所以,當各國以憲政理念消解軍事權某些“不合時宜”的權力特質時,隱含在憲法文本背后的“事實上的動機”往往透過憲法條文,在制憲者對軍事權的增強與節制、區隔與融合、明確與模糊的艱難抉擇中展現開來。
(一)增強與節制的選擇
各國憲法文本對于軍事權的規制往往發生在既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動作用又要遏制其不良傾向的進退維谷之間。因為,過于強大或過于羸弱的軍事權都會導致社會結構因憲政格局的打破而失衡,法治的終結甚至民族的毀滅恐怕亦將接踵而至。
然而,對于憲法文本的制定者而言,這種選擇卻是十分困難的。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曾關切地說:“提防外患,確保安全,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目標之一。……常備軍……是危險的,盡管同時可能又是必要的。最輕度地說,它帶來種種不便。嚴重地說,它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無論如何,它都值得予以慎重對待和小心提防。一個明智的國家應該將所有這些給予綜合考慮;它一方面不可以魯莽地舍棄任何可能對它的安全至關重要的手段,同時又應該極為小心謹慎,減少依賴這種有可能威脅到自由的手段的需要及其危險。”[9][10]
正是在該理念的指引下,美國憲法構建起增強與節制相對均衡的軍事權規制體系。在其憲法文本中,總統被任命為合眾國陸海軍和被征調為合眾國服現役時的各州民兵的總司令,控制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因而能夠迅速有效地將他們集結起來抵御外來進攻,保衛新生國家。同時,由于“行政部門是最熱心于戰爭而且最易于發動戰爭的權力部門”[11],美國憲法又將宣戰權、戰爭撥款權和軍事力量組織權悉數賦予立法機關——國會掌控,形成了對總統軍事統率權的制約。由此看來,既要培育強大的軍事力量,又要保證該力量受到國家理性的控制,恐怕是各國憲法文本在設計軍事權的運行規則時所要面臨的首要抉擇。
(二)區隔與融合的考量
軍事社區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以軍事活動為中心,以垂直社會關系為主線,以正規武裝人員為主體形成的社會實體。[12]早期的軍事社會學理論認為,軍事社區是與民間社會相區別的。在戰時,武裝力量自然是一種“半孤立的軍事社區”。即使在和平時期,它也同樣是一種組織化并脫離于民間社會的“人工化社區”。除了一些與外界的人和機構不可避免的接觸外,他們的生活就局限于軍事職責、慣例、意識和社交活動的范圍內。[13]然而,自憲政的平等理念滲入軍中以來,軍事社區的權力運作方式是否應當與民間社會的權力運作方式趨同,社區內的軍人是否應當獲得與民間社會中的普通公民相等同的權利義務,亦即軍事社區與民間社會的關系是定位于“區隔”還是定位于“融合”,或者在怎樣的“度”上傾向“區隔”與“融合”,便成為各國制定憲法文本時戮力研擬的又一重大課題。
上世紀 40年代末,德國基本法的制定過程某種程度上就是這兩種理論爭鋒的過程。傳統派主張“區隔”,認為“文武社會”的分別建立可以保持軍隊的“純度性”。如果“軍民合一”,民間社會的多元價值觀一旦滲入軍隊,軍隊戰力勢將瀕臨崩潰;革新派主張“融合”,認為“區隔”將軍隊“特殊化”,使軍隊變成“國家中的國家”,憲政秩序無法滲入軍隊體系,這與法治國家一切依法而治的原則背道而馳。[14]因此,以包狄辛(WolfGraf von Baudissin)將軍為代表的革新派認為“軍人乃穿軍服的公民”(Staatsbuerger in Uniform),他們只有切身感受并踐行民間社會的民主與法治理念,才能甘愿為保衛自由民主的國家而奮斗犧牲。
幾經權衡,德國基本法和隨后頒布的德國軍人法還是大致采納了革新派的主張,賦予軍人“穿軍服的公民”身份,確立了軍事社區與民間社會相“融合”的基本立場。但隨后,在德國國防部公布的第 11號行政命令中再次聲明:“基于軍事勤務之特性,社會發展的事項并非可以不經審慎的評估即當然地引用到軍隊之中;另外軍事勤務之必要考量亦非可作為社會的評斷標準。”重新將“融合”的“度”作了調整,體現了憲法文本制定者對“融合”的審慎態度,也足見“區隔”與“融合”的抉擇之不易。
(三)明確與模糊的權衡
“明確”與“模糊”關涉的是憲法文本規制軍事權時所采用的立法技術問題。“明確”著眼于“效率”,它力圖減少軍事權的運行摩擦,從而維護憲法條文的剛性與權威;而“模糊”著眼于“靈活”,它巧妙概括軍事權的作用空間,從而維護憲法條文的簡潔與包容。衡量利弊后,各國通常作出“模糊”大于“明確”的選擇,這除了憲法的宏觀性使得它不宜過于“明確”外,美國憲法成功運用“模糊”來應對危機的榜樣作用恐怕亦不能小覷。
18世紀末,華盛頓總統派兵鎮壓“威士忌酒暴動”便是鉆了憲法條款“模糊”的空子。1791年美國國會對酒類征稅嚴重損害了農戶的利益,所以賓夕法尼亞西部的阿勒格尼縣數百名武裝農民在民主會社的領導下召集了 4個縣的民兵來保衛釀酒自由,并成功地抵制了收稅官和聯邦法院的執行官。事態逐漸擴大甚至失控,已然危及到了新生國家的安全與穩定。然而,根據美國憲法,聯邦只有在州的請求下才能動用軍隊敉平內亂。形勢已是迫在眉睫,華盛頓總統卻遲遲未收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請求。于是他便依仗憲法賦予他的“監督一切法律切實執行”的權力主動出擊,征召民團平息了暴動。[15]這固然體現出華盛頓總統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是,若離開美國憲法賦予總統有權“監督一切法律切實執行”的模糊條款,恐怕他也是寸步難行。
當然,憲法條文過于“模糊”同樣在美國的憲政實踐中被證明是不利的。由于美國憲法對總統戰爭權的規定失之籠統,使得國會與總統在對憲法文本所賦予各自權力的理解上存在分歧。而正是憲法的“模糊”猶如將他們“置于拳擊場,敲響鈴,讓他們無休止地爭斗下去”[16]。所以,軍事權在憲法文本中“明確”與“模糊”的權衡恐怕難有定式,還需各國在軍事權的憲法規制實踐中逐漸摸索。
三、隱晦的真實:行憲實踐中的軍事權
“在法的問題上并無真理可言。每一國家依照各自的傳統制定制度與規范是適當的。”[17]但是,如果認為軍事權的憲法規制是由各國政治精英在憲法文本中“創設”的(即認為,這些規則不是源于自然秩序并反映現實社會的法則,而是由人類理性所創造的,改變并構建軍事權運行框架的構成性工具),便主觀地將研討的目光狹隘地聚焦在憲法文本上,那么便無法理解各國軍事權運行中那些貌似沒有憲法依據,甚至違背憲法規范,卻又往往能夠堂而皇之的得以推行的最終根由。這種完全囿于憲法文本解讀軍事權的進路必然給研究者帶來迷惑——“矗立于理想和現實的鴻溝兩岸,面對生動和復雜的社會政經現象,深感生命被撕裂的痛苦和焦灼,心智之枯竭暴露無遺:因為他無法解釋現實,不知身處何地,所以他伸張的理想總難免盲目荒誕,他展示的道路總難免誤入歧途”[18]。
所以,我們在對軍事權進行憲政解讀時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憲法從來都不只是用文字表達的形式文本,而是一個實質性的構成要素。它顯然包括了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國家主權權力分配或行使的所有規則。其中一套規則是嚴格意義上的“律法”;而另一套規則是由慣例(conventions)、默契(understandings)、習慣(habits)或常例(practices)構成。[19]這種潛伏在各國現實政治生活中的融貫于憲法文本,但又超越于憲法文本的“隱性規則”,才是影響軍事權運行的終極力量,也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真實描繪與解讀軍事權的重要因由。正如著名制度變遷理論研究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所說:“制度作為人類行為的結果,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是以憲法、法律、法規為基本內容的正式規則和以習俗、傳統、習慣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規則交錯構成的一整套的規則體系及其實現機制,是不同社會群體為了存續和利益分配而交互作用的結果。”[20]仍以美國總統與國會的戰爭權爭奪為例。盡管憲法相關條文用語模糊,但仍大致將對外戰爭的指揮權賦予了聯邦總統,將宣戰權賦予了美國國會。然而,現實中此種結構性安排卻在一系列非正式規則的作用下形同虛設。事實上,美國由地處北美一隅的撮爾小邦發展成為超級大國的過程,也可以看做是美國總統置憲法賦予國會的宣戰權于不顧,不斷突破條文預設的框架,肆無忌憚地對外展開征伐的過程。其中,杜魯門發動朝鮮戰爭、艾森豪威爾向黎巴嫩派兵、肯尼迪封鎖古巴、約翰遜號令軍隊開進越南都沒有以國會的宣戰為前提。即便是在1973年國會頒布了旨在限制總統的《戰爭權力決議案》(War Powers Resolution)后,美國總統戰爭權獨攬的癖好仍然未見收斂。在解救伊朗人質、轟炸利比亞、入侵格林納達和巴拿馬、發動海灣戰爭等一系列軍事行動中,國會宣戰權對總統的制約作用依舊相當有限。尤其是“9·11”事件以后,面對政治生態發生的巨大變化,美國國會和普通民眾對總統日益擴張的戰爭權表現出極大的理解和信任,使得其可以“使用所有必要和適當的力量來打擊那些與襲擊事件有關或可能在策劃新的襲擊事件的國家、組織或個人”[21]。這也可以看做是美國憲法文本不斷“為解釋所發展,判例所修飾,風俗習慣所擴張”[22]的生動表現。
由此可見,憲法并不是一種脫離歷史時空的抽象存在,相反,它以及對它的解釋都是特定歷史時空下政治經濟的反映,是特定歷史背景下不同的價值觀博弈的結果。所以,對軍事權進行憲政解讀時我們必須拓寬思路,關注那些與憲法文本密切相關的但又不為其所覆蓋的隱晦卻真實的規則。這便要求我們,一方面應當堅持從“憲法文本”出發的憲法解釋學立場,充分發掘并不斷完善憲法中軍事條款的深刻涵義,使得軍事權的憲法規制在文本上能夠做到邏輯自洽;另一方面更應當“超越憲法文本”,從憲法運作的角度來探究和發現那些能夠影響甚至決定軍事權的隱性規則,從而真正理解政治制度、文化傳統、風俗習慣乃至人們之間以默會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信念和原則對軍事權運作的重大影響。尤其是在成文憲法作用有待提升的國家,識別并闡釋這些隱晦卻真實的規則對于透徹理解其軍事權的憲法規制至關重要。
[1][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8.
[2]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M].上海:三聯書店,1998:52.
[3]景躍進,張小勁.政治學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74.
[4]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 1卷)[C].北京:戰士出版社,1981:38.
[5][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315,3.
[6]梁必骎.軍事哲學[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110.
[7]高全喜.我的軛——政治與法律之間[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10.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09.
[9][美]邁克爾·開羅.文官統率軍隊[EB/OL].(2010-09-18).http://rizhilu.fyfz.cn/art/608577.htm.
[10][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C].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09:209.
[11]楊健.從越南戰爭看美國國會與總統間的戰爭權之爭[J].美國政治,1992,(4).
[12]張明慶.軍事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87.
[13][美]查爾斯 H科茨,羅蘭 J佩里格林.軍事社會學[M].北京大學國防學會,譯.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52.
[14]陳新民.軍事憲法論[M].臺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81,76.
[15][美]莫里森.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M].南開大學歷史系美國史研究室,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400.
[16]李慶四.美國國會與美國外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98.
[17][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M].漆竹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2.
[18]翟小波.憲法是關于主權的真實規則[J].法學研究,2004,(6).
[19]強世功.“不成文憲法”:英國憲法學傳統的啟示[J].讀書,2009,(11).
[20][美]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陳部,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94:225-226.
[21]周海波.美國總統和國會的戰爭權之爭[J].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8,(2).
[22][美]迦納.政治科學與政府[M].孫寒冰,譯.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