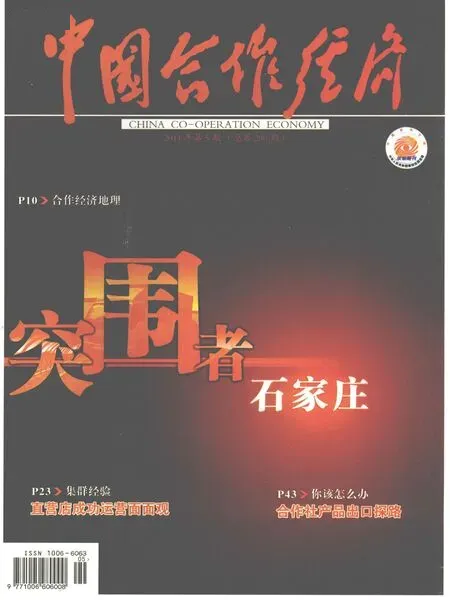持續釋放農業勞動力的思考
文/葉興慶
近幾年,每當春節之后,“招工難”現象是一個倍受關注的社會問題,且呈現由東南沿海向中西部蔓延、由季節性向常年性演變之勢。“招工難”是不是我國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勞動力供求關系的真實反映?現階段應對“招工難”的著力點,究竟應放在需求方、逐步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應放在供給方、繼續釋放農業勞動力?這是事關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如何同步推進的大事。
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已進入“劉易斯區間”
劉易斯區間
這是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和《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兩篇論文中形成的概念。
他認為,二元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拐點:在經濟發展初期,農業部門有大量剩余勞動力,以極低的工資水平就可以吸引他們向工業部門轉移,當工業部門只有明顯提高工資水平才能繼續吸引農業勞動力轉移時,達到第一個拐點;隨著農業勞動力繼續轉移,農業勞動生產率將持續上升,直至與工業部門相當,出現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二元經濟結構消失,這是第二個拐點。這兩個拐點之間的發展階段,稱作“劉易斯區間”。
為分析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的變化規律,學術界普遍使用“劉易斯拐點”、“劉易斯區間”的概念。
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正處于“劉易斯區間”。第一個拐點大致出現在2004年前后。此前相當長一個時期,由于農業勞動力剩余程度嚴重,農民工工資在低水平徘徊。從2004年開始,東南沿海一些地區出現“招工難”現象,農民工工資開始上漲。數據顯示,農民工月工資2001年—2003年年均增長 4.4%,2004年—2010年年均增長 13.5%。從第二個拐點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09年,我國第一產業占全國就業人員的38%、國內生產總值的10.3%。近2/5的農業勞動力,僅創造了1/10的國內生產總值,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我們離農業與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的發展階段還很遠。
對“劉易斯區間”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應把握住以下幾點:第一,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大于零,但仍低于非農部門,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過程并沒有結束,這種資源再配置仍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第二,非農部門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吸引農業勞動力向外轉移,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農業勞動力轉移對非農部門工資水平上升的彈性系數趨于下降;第三,農業部門必須及時進行物質技術改造,一方面為勞動力繼續向外轉移創造條件,另一方面補上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產能的影響,并且使農業產能逐步提升,也就是要“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
持續釋放農業勞動力需多方施策
在“劉易斯區間”,我國農業勞動力繼續向外轉移,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比其他國家在這個階段所面臨的更多、更復雜。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采取措施促進農業勞動力繼續向外轉移。
以農業機械置換農業勞動力。在第一個“劉易斯拐點”之前,我國農業勞動力處于絕對過剩狀態,向外轉移并不影響農業生產。在“劉易斯區間”,農業勞動力是相對過剩,如果不采取置換措施,向外轉移將影響到農業生產。最有效的置換措施是推進農業機械化。每當農忙季節,不少外出務工農民要回家參加農業生產,這說明農業勞動力存在季節性短缺問題。與其讓這些人緊急回家參加農業勞動,不如雇請農業機械幫忙,這表明農業中機械替代勞動力的經濟臨界點已經到來。這幾年農業機械化步伐較快,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2010年已達到52%,“十二五”時期末將達到60%左右。應當順勢而為,進一步加快農業機械化步伐。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主要是繼續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規模,向消耗勞動力較多的薄弱環節和關鍵農時、特別是經濟作物生產所需機械傾斜;鼓勵農民通過組建農機專業合作社,聯合購買農機具,提高農機使用率;促進農機工業發展,重點研發和推廣先進適用、節能環保、區域適用性強的農機產品。
以土地流轉解放農業勞動力。盡管農業勞動力持續向外轉移了近30年,多數地方土地流轉步伐卻難以跟上,小規模兼業經營格局趨于固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口增長和分家立戶,全國農業經營戶數不減反增,農業平均經營規模不增反降。對比1996年與2006年兩次全國農業普查,盡管全國耕地面積明顯減少,但農業生產經營戶數卻從19345萬戶增加到20016萬戶。雖然農業勞動力總量過剩,但具體到每戶現有勞動力又難以從農業中完全脫身,形成“有剩余勞動時間、沒有剩余勞動力”的尷尬局面。這導致農業經營規模、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力有效利用率均難以提高,陷入“土地難以流轉是由于農業勞動力缺乏就業門路,農業勞動力難以繼續轉移是由于現行農業經營方式不利于他們脫身”的僵局。打破僵局的根本出路在于促進土地流轉。在法律層面已沒有障礙,關鍵在于建立健全促進土地流轉的機制。應當加快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步伐,讓無論是留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的家庭,還是全家進城落戶的家庭,都能放心地轉出承包地,不用擔心土地承包經營權被收回;積極培育土地流轉市場,發展流轉中介組織,為流轉雙方提供信息溝通等服務;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實行流轉補貼政策,調動承包戶轉出土地、經營戶轉入土地的積極性。
以就地就近轉移撬動農業勞動力。農業勞動力轉移具有“精英移民”的特征,先出去的絕大部分是青壯年勞動力。據有關研究推算,2009年,30歲以下、31-40歲、41歲以上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分別為1.42億、5124萬、3699萬,分別占同年齡段農村勞動力的92.9%、42.8%和16.2%。這意味著今后能夠轉移出來的存量農業勞動力,主要集中在31—40歲和41歲以上兩個年齡段。對這些人,特別是對41歲以上的人而言,決定其去留的因素,不僅包括工資水平,還包括對家庭的牽掛、對未來生活前景的擔心。要想把這兩個年齡段的勞動力轉移出來,必須發展縣域經濟、走就地就近轉移的道路。為此,要調整工業化、城鎮化的戰略布局,加快中西部地區縣域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國家每年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應向中西部省份傾斜,各省應向縣域傾斜;在集約節約用地、嚴格保護環境的前提下,對農業縣的產業園區給予大力支持;推動勞動密集產業向中西部縣域轉移,加大對產業轉移承接基地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別是要對一些地方發展鄉鎮企業的好經驗,如塊狀經濟、產業集群、一村一品等進行深入總結,處理好集中與分散的關系,既要避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又要防止農村產業空心化。
以技能培訓提高農業勞動力。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逐步推進,新增就業崗位對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隨著農村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逐漸減少,今后需要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年齡偏大、受教育年限較短的問題愈加明顯。最近幾年各方面十分重視對農民工的培訓,但主要是針對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勞動力。應該根據農村勞動力結構的變化,重點開展中年勞動力培訓,在培訓內容、方式等方面更適合中年農民的需要,盡快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和就業競爭力。
以公共服務留住進城的勞動力。目前第一代農民工已人到中年,除少數人能夠在城市長期工作和生活下去外,多數人還處于“流動”狀態。城市的大門要敞得更開一些,讓進城農民工對未來的工作和生活有穩定的預期,加快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各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使他們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和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