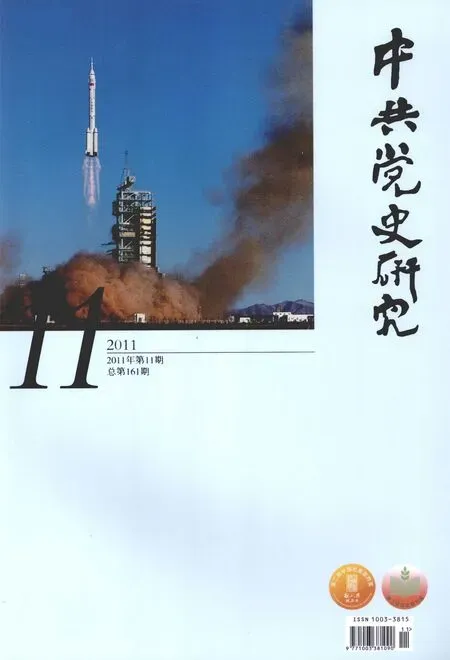堅持和弘揚《歷史決議》的科學歷史觀
石 仲 泉
堅持和弘揚《歷史決議》的科學歷史觀
石 仲 泉
今年是 《歷史決議》發表30周年。我作為參與決議起草的人員之一,當年工作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回首30年,《歷史決議》的基本精神、重大政治判斷和重大歷史結論都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我個人也一直遵循它研究黨的歷史,受益匪淺。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好決議。為什么會這樣說呢?就是因為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觀。這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黨的歷史,評價歷史事件和臧否歷史人物。說得更直白一點,科學歷史觀就是 “實事求是”四個字。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 《歷史決議》的靈魂。紀念《歷史決議》通過3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和弘揚這個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
一、與時俱進,堅持 《歷史決議》與黨的文獻相關論述的統一
《歷史決議》是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根本指導思想,對研究這段歷史起到了 “定海神針”的作用。但是,歷史在發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會有新的理解,或根據新的材料以新的角度作新的解讀。事實上,現在我們對 《歷史決議》的認識在內涵上比1981年時的認識豐富多了,特別是黨的領導人和黨的重要文獻對相關黨史的論述,大大地推進和豐富了 《歷史決議》的一些論斷。這就有一個如何根據 《歷史決議》的科學歷史觀,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 《歷史決議》與黨的領導人和黨的文獻相關論述相統一的問題。
比如,關于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起點問題。一種看法認為,應以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幫”作為新時期的起點。另一種看法認為應以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兩個時期的界碑,亦即新出版的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提法。從文字上講,這兩種看法都能從《歷史決議》中找到根據。作為學術問題,對這兩種看法可以繼續切磋探討。但應當指出的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其他領導人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文獻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很明確的,都是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時期的起點。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等領導人以及黨的重要文獻都這樣論述,更重要的在于它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客觀實際。我們應以30多年的歷史發展的實際走向和主要內容作為劃分歷史界限的根本依據和標準。正因為如此,30多年來,黨中央舉行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0周年、20周年和30周年的大會,卻從來沒有開過一次紀念粉碎 “四人幫”多少周年的大會。
怎樣理解 《歷史決議》講的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幫”的勝利 “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呢?在我看來,第一,“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主要是相對于此前的 “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時期講的,而不是就新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而言的。《歷史決議》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 “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則是就新中國的整個歷史發展來說的。這是屬于兩個不同層面的評價。第二,歷史在發展,認識在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越來越凸顯。起草 《歷史決議》時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間很近,對它的認識不可能有后來這么深刻。因此,也應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它。第三,《歷史決議》對粉碎 “四人幫”后的歷史發展是講了兩個方面的。在肯定它的偉大意義后,緊接著指出: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 “左”的錯誤,黨的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況且1977年黨的十一大還肯定了 “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說明路線問題并沒有解決。因此,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幫”的勝利,沒有能夠成為新時期的真正起點。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開創社會主義事業新時期的歷史起點,并不違背 《歷史決議》。也可以說,只有根據 《歷史決議》對粉碎 “四人幫”后的歷史發展的兩個方面的論述,并聯系后來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才能對 《歷史決議》的論斷作出完整的、準確的理解。
二、從歷史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
有這樣一種說法:《歷史決議》對一些重大事件的結論還不實事求是,沒有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涉及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也就是如何把握科學歷史觀的問題。在我看來,第一,實事求是不單純是對事實的判斷,還是對價值的判斷。因為對任何復雜客觀事物的認識,都涉及認識主體的立場、觀點、方法,與認識主體的人生經歷、文化素養和價值觀念密切相關。這就是對同一個人或事往往會有不同看法的原因。第二,實事求是是一個過程,如同真理的認識是個過程一樣。認識主體不僅有認識的局限,還有歷史的局限。任何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時空之中,不能不受歷史環境、史料解密和歷史真實情況披露的制約。脫離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不顧客觀條件的許可程度,要求絕對地 “實事求是”是不實際的,它只能逐步地實現。第三,實事求是有宏觀把握和微觀把握之別。能將兩方面都把握好,是最理想的。求其次,首先在宏觀方面把握好,在總體上做到對歷史的敘述和分析是客觀的;在具體史料上是努力求實的。這就應當說做到了實事求是,堅持了科學歷史觀。
比如對社會主義改造如何評價,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爭議的問題。因為改革就是從解決社會主義改造的遺留問題開始的。無論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都是以調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表現形式、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作為改革的起點的。因此,“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看法相當普遍,認為 《歷史決議》肯定三大改造不實事求是。
這里涉及對三大改造究竟應當根據什么作標準進行評價的問題。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是比原來預期的大大超前完成了。但是,衡量得失的標準是主要看時間長短,還是主要看對社會發展的實際影響?是只看它后期的工作中的問題還是主要看其基本方向的把握?當然,應當是后者。從社會主義改造全過程的總體上講,黨采取逐步改造的具體政策,第一,沒有造成生產力的大破壞,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二,沒有出現社會的大動蕩和混亂現象,社會各個階級、階層之間的關系大體穩定;第三,還創造了適合中國特點的由初級到高級的過渡形式,特別是積累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政策的經驗。基于這幾點,《歷史決議》對社會主義改造作出肯定性評價。
應當指出,評價歷史事件和總結歷史經驗,實際上是兩個思路。一般說來,評價歷史事件,是從權衡社會實際狀況的得失出發;總結歷史經驗,則是從理想狀態來要求。換句話說,這是兩個標準。對于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這樣,首先是肯定,然后總結經驗教訓,指出缺點錯誤在哪里。《歷史決議》在肯定它的同時,也指出了工作上的缺點和偏差。其分析是全面的,做到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是實事求是的。當然,從評價歷史角度 “充分肯定”它,不等于說當時的指導方針和工作部署百分之百的正確,沒有任何失誤。因此,我也不贊成將三大改造的成績說得很滿。因為它帶來的求快、求純的偏差,造成了長達20多年的后遺癥。后來黨的歷史發展曲線與它密切相關。第一,后來歷史的幾次反復,都因處理遺留問題而調整政策所引發;第二,許多干部 (包括有的領導人)和群眾為此一再受到批判和傷害;第三,盡管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沒受到破壞,但長期不調整的結果,就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受到束縛,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難以充分發揮。因此,“充分肯定”它,并不是說沒有教訓需要吸取。如果不能將兩者區別開來,就很難科學地說明黨的歷史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之所以從農村開始,就是因為那個時期的改造 “太純”了,超越現實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越了社會歷史條件。說白了,解決這段歷史遺留問題是啟動改革的一個直接動因。
三、反對兩種傾向,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10年前,龔育之在為紀念 《歷史決議》通過20周年答 《人民日報》記者問時,曾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從 《歷史決議》已經得到的成果后退。他說:這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淡化甚至否定《歷史決議》對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錯誤作出的結論,從這樣的結論后退。二是淡化和否定 《歷史決議》對中國社會主義成就的肯定,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肯定,似乎新中國成立以來什么成就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個接一個的錯誤。這是從另一個方向的后退。他認為,對 “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給人民、給國家、給黨帶來的那么大那么深的災難,對 “文化大革命”以前反右派斗爭、“大躍進”運動、“反右傾”斗爭中的錯誤給人民、給國家、給黨帶來的那么多的傷害,不能采取回避、淡化掉的態度;而是應該如實地、恰如其分地正視它、記取它。不這樣,怎么可能避免這樣的傷害和災難的重演呢?同時,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艱苦奮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也不能采取無視它、否定它的態度,而是應該如實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這也是尊重人民、尊重歷史。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全部歷史,必然導致否定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建設的全部歷史。因此,上述兩種情況都應當堅決反對。
我完全贊同龔育之講的要警惕和防止從 《歷史決議》已經取得的成果后退的兩種情況。盡管10年過去了,但這兩種情況仍然存在。我曾經講過黨史研究方面存在的五種傾向,也包含了這兩種情況。首先是黨史的虛無主義傾向。這種傾向對黨的歷史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講黨的歷史和毛澤東只講錯誤的一方面,將一個個錯誤串糖葫蘆似的連貫起來,這樣寫黨史把黨完全丑陋化、妖魔化了。這就是從 《歷史決議》已經肯定的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取得的基本成就方面后退。近些年來,對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妖魔化的傾向更加凸顯,有人千方百計地挖空心思剪裁黨的歷史,歪曲領導人的奮斗歷程,丑化他們的思想和心靈。有的甚至偽造中央文件,散播謠言,胡說什么中央領導人開過會,要再作歷史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還說什么 《毛澤東選集》的許多文章都是別人捉刀的,云云。這些人對黨的歷史和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評價,根本不尊重歷史事實,蓄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哪里有什么黨性和科學性?!連起碼的誠實性都沒有,對這種 “黨史虛無主義”的傾向不可忽視。另一種傾向,就是龔育之講的那種淡化甚至否定 《歷史決議》對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錯誤作出的結論,要從這樣的結論后退。有的人不是要為 “文化大革命”翻案和為 “四人幫”平反嗎?完全否定 《歷史決議》對 “文化大革命”的結論。
另外,在黨史研究領域還存在一種如毛澤東說的 “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功利主義”思想。比如對黨的曲折歷史和黨的領袖功過,只片面強調寫勝利、成就、正確一面,著墨用力于主觀愿望怎么好,怎么糾正錯誤,而對黨所經歷的某些曲折和挫折不寫或者輕描淡寫,對錯誤的嚴重后果不作如實反映。這種 “采取回避、淡化掉的態度”與人們所公認的歷史事實反差太大,乃至不為群眾認同。
有人說,寫黨史有一個立場、感情和講黨性的問題,批評黨史研究的狹隘功利主義,是不是否定了對立場、感情和講黨性的要求?我以為這樣提出問題,是對寫黨史的立場和感情以及講黨性作了片面的理解,或者說誤讀了對立場和感情以及講黨性的要求。黨的立場是什么?就是人民的立場,看人民滿意不滿意,看與歷史實際符合不符合。符合歷史實際,這就是黨的立場,也是黨性的要求。鄧小平一再講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對寫黨史來說,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就是黨的立場和黨性要求,既是黨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再講實事求是就是黨性,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這是寫黨史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現在是一個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中國網民高達5億,各種信息傳遞極為迅速和廣泛。不能實事求是地反映黨的歷史的立場絕不是黨的立場。感情亦然。所以,我不贊成以所謂 “立場和感情”作為回避或淡化黨所犯的錯誤的辯詞。在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下,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做到了這一點,也就是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也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觀。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