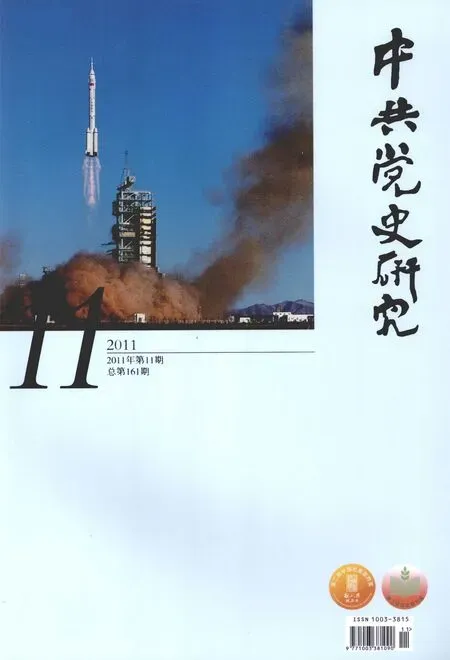重讀《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林 蘊 暉
重讀《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林 蘊 暉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歷史決議》,迄今已30個年頭。如同人們對任何歷史問題的認識一樣,《歷史決議》不能不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1981年6月,距離 “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到5年,當時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重塑人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念和信心,為此,必須要對新中國成立32來發生的歷史曲折作出為黨內外大多數人們所能接受的結論,以統一思想,并堅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四個現代化的信心。所以,這個 《歷史決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個 “政治決議”。
基于上述指導思想和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對問題的認識水平,為增強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的認識,《歷史決議》在開頭寫了一節 “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接著是對 “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然后再寫,“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的偉大轉折”;“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其中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1976年到1978年的兩年徘徊等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分析和人們所熟知的結論。
《歷史決議》最后向人們指出:“經過建國三十二年來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的反復比較,特別是經過近幾年來的思考和總結,全黨同志和我國各族愛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程度,顯然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水平。我們黨敢于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究只是一時的現象,而我們黨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鍛煉,我們黨經過長期斗爭形成的骨干隊伍的更加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顯著,要求祖國興盛起來的黨心、軍心、民心更加奮發,則是長遠起作用的決定性的因素。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偉大的前途,我國各族億萬人民有偉大的前途。”
應該承認,《歷史決議》的這些結論,在當年對人們拋開沉重的歷史包袱,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解放思想,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起到了極其重大的積極作用,達到了預期目的。
隨著時代的前進,黨對歷史的認識也隨著人們的實踐而不斷深化。如:鄧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說:“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頁。1984年、1985年,鄧小平在同外賓談話中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頁。
在對1957年到1976年20年歷史的評估方面,鄧小平也有過論述。1987年6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可以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 ‘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鄧小平的這些重要論述,是對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到1976年這段歷史的再認識,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如果看不到這種對歷史認識的前進和發展,把 《歷史決議》的結論凝固化、教條化,那就不可能有鄧小平理論,也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那種對 《歷史決議》搞“兩個凡是”的思維方式,是不可取的。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出版的可稱為權威的一些歷史著作,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某些重大歷史問題和事件作出新的論斷和評說已不是個別事例。
如: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 《毛澤東傳 (1949—1976)》寫道:
毛澤東審閱的提綱中有這樣一句話:“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而并不確切的觀點。這句話不是毛澤東寫的,但他贊成,還作了發揮。在這句話之后,他加寫了一段文字:“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
這個理論觀點,代表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對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所達到的認識水平。根本出發點是為了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鞏固人民政權。但是,認定只有使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 (即公有制)成為國家唯一的經濟基礎,才能做到這一切,是不符合實際的,尤其不符合中國這個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家的實際。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以及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些根本問題上的認識,還很不成熟,還缺乏甚至沒有實踐經驗。這個理論觀點作為中國共產黨在以后幾十年間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指導思想,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過于求 “純”的消極影響。
再如:關于高崗、饒漱石事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主要講高崗 “分裂黨”,沒有再提 “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話。
又如:關于對華國鋒在粉碎 “四人幫”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期間的評價,《黨史》二卷與 《歷史決議》的基調有了極大的差別。《歷史決議》指出:(粉碎 “四人幫”以后)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 “左”的錯誤。盡管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 “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 (包括 “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 “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 “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也負有責任。
《黨史》二卷對華國鋒在粉碎 “四人幫”中所起的作用予以肯定,明確首先提出要解決 “四人幫”的是華國鋒,是他先同李先念就此問題進行商談,并請李先念征求葉劍英的意見。《黨史》二卷對華國鋒在 “兩個凡是”和鄧小平出來工作問題上的態度,作了實事求是的客觀的敘述。《黨史》二卷指出,對1977年經濟理論界開展關于按需分配和 “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和華國鋒都表示了明確的支持,并指出在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召開的會議上,華國鋒都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黨史》二卷沒有再說華國鋒壓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 (包括 “天安門事件”)的進程,以及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從整體來說,《黨史》二卷對華國鋒肯定的方面多了。
總之,對 《歷史決議》的歷史作用,應予肯定;把 《歷史決議》教條化,用來束縛人們對歷史進行再認識,是錯誤的。
(本文作者 國防大學退休教授 北京 1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