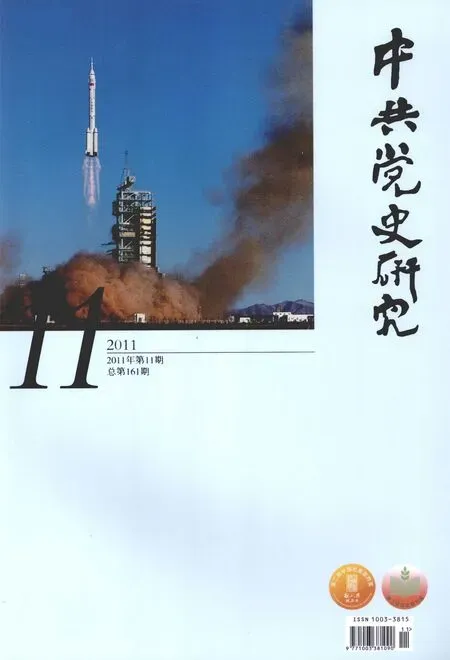抗爭與妥協(xié):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的發(fā)展與鄉(xiāng)村革命——以一九二八年的永定暴動為例
曾耀榮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近代中國城鄉(xiāng)關系的發(fā)展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及當時知識分子的高度關注,他們紛紛提出解決農村問題的種種主張。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紛紛撤離城市,向鄉(xiāng)村發(fā)展自己的勢力,通過武裝斗爭和建立紅色政權,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深入研究近代城鄉(xiāng)關系和中國革命問題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利于理解中共革命的合法性,而且還可以借此以觀照當代中國城鄉(xiāng)關系問題,并尋求城鄉(xiāng)矛盾問題的解決具有積極意義。目前,學術界對近代城鄉(xiāng)關系與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略有涉及①相關成果主要有:宮玉松、聶濟冬:《科學認識中國近代城鄉(xiāng)關系與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選擇》,《黨史研究與教學》1992年第3期;梁敏玲:《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的大致走向——以時人所論所行為中心的梳理》,《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 (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賀黑生:《毛澤東提出紅色政權理論的客觀依據——近代中國的城鄉(xiāng)關系》,《衡陽師范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等等。,這些研究主要著眼于近代城鄉(xiāng)關系與中國農村革命道路的選擇問題。本文則從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發(fā)展和變化的視角,揭示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領導鄉(xiāng)村革命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并以此解讀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的發(fā)展與中國革命緣起和發(fā)展趨向問題。
一
學術界對近代以前城鄉(xiāng)關系的認識,主要形成了“城鄉(xiāng)對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和“城鄉(xiāng)對立統(tǒng)一”三種不同的觀點②參見梁敏玲:《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的大致走向——以時人所論所行為中心的梳理》,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由于傳統(tǒng)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在經濟領域大體處于統(tǒng)一發(fā)展階段,它們在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也存在著明顯的同構性。“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xiāng)村為基礎,并以鄉(xiāng)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xiāng)村而來,又為鄉(xiāng)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yè)等莫不如是。”③《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0頁。。因此,傳統(tǒng)中國城鄉(xiāng)之間除了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對立外,其他方面則又是統(tǒng)一的,甚至這種廣泛的統(tǒng)一性要大于其對立性,呈現一種對立統(tǒng)一的城鄉(xiāng)一體化關系④參見張國:《中國城鄉(xiāng)結構調整研究:工業(yè)化過程中城鄉(xiāng)協(xié)調發(fā)展》,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02年,第40頁。。這種對立統(tǒng)一的城鄉(xiāng)一體化關系正如著名學者徐勇所言:“古代中國城鄉(xiāng)一體化的趨向格外突出。當然,這種一體化只是就整個社會的共同體基礎和整合性而言的,并不是指城鄉(xiāng)無甚差別……”⑤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xiāng)村比較》,中國廣播出版社,1992年,第45頁。然而,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經濟的引入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經濟的發(fā)展,改變了傳統(tǒng)中國城鄉(xiāng)一體化的社會關系。因為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經濟主要在城市得到發(fā)展,城市工業(yè)化隨之而起,并引起近代中國城市化的加快推進。“近代以來,城市的早期現代化運動的不斷深入,以及早期現代化因素由城市向鄉(xiāng)村的深入,并釋放出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使近代中國城鄉(xiāng)關系呈現出兩極發(fā)展的新特點,即城鄉(xiāng)間聯(lián)系性的加強與對抗性矛盾的加劇的兩極化態(tài)勢。”⑥蔡云輝:《論近代中國城鄉(xiāng)關系與城市化發(fā)展的低速緩進》,《社會科學季刊》2004年第2期。
這種兩極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在近代福建永定城鄉(xiāng)關系上也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城市與鄉(xiāng)村間,鄉(xiāng)村與鄉(xiāng)村都是隔絕不相往來,或者互相對立,沖突。也有站在利害關系上互相聯(lián)絡的。”⑦《趙亦松關于永定工作概況報告》(1928年7月29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1984年7月,第128頁。這段話透露著近代永定城鄉(xiāng)關系的基本史實:城市和鄉(xiāng)村的隔離、對立和沖突是近代永定城鄉(xiāng)關系的常態(tài)。相反,城市和鄉(xiāng)村的聯(lián)系是建立在城鄉(xiāng)利害關系的基礎上的。
那么,近代永定城鄉(xiāng)關系之間的聯(lián)系到底建立在何種利害的基礎上呢?
首先,近代以來由于政治動亂和社會不安,鄉(xiāng)村地主和豪紳出于安全需要紛紛離開鄉(xiāng)村;而居住城市的商人、官僚和軍閥卻投資于土地,農村土地所有權不斷轉移到農村以外的人手中⑧參見〔日〕長野郎著、強我譯:《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1—114頁。。永定鄉(xiāng)村社會結構是地主、豪紳、富農占少數,佃農和半佃農占大多數⑨參見《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報告——永定最近工作概況》(1928年4月3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1983年11月,第197頁。。土地大部分是城內地主、豪紳的土地和宗族公田。佃農和半佃農為了生存,需要向城內地主、豪紳和宗族公田租種土地。因此,永定縣鄉(xiāng)村社會階級結構和土地占有現狀,決定了農民在經濟上需要依賴城內地主和豪紳而存在。
其次,永定縣山多田少,單純依靠農業(yè)耕種是無法解決生活問題的,手工業(yè)成為永定農民經濟生活的必要補充。 “永定物產有米,番薯,花生、豆子。煙葉尤為特產,造成條絲煙每年運銷各省,為永定唯一大的經濟來源。又有木頭紙等出口。鴉片產量亦多。木頭紙亦為永定運出品之大宗”①《趙亦松關于永定工作概況報告》 (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125—126頁。。地處閩西的永定民眾“即用這些土產工業(yè),來交換食鹽、煤油、布料及日用工業(yè)品等”②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 (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8頁。。來自農村的農產品和源于城市的工業(yè)品之間的交換,強化了城鄉(xiāng)之間經濟上的聯(lián)系和交往。
最后,“地主豪紳將他們剩余資本集中于市鎮(zhèn)。在鄉(xiāng)村市鎮(zhèn)或較大的城市中,豪紳地主的力量,日益加大”③《趙亦松關于福建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88頁。。由于商業(yè)資本高度集中于城市或市鎮(zhèn),高利貸在鄉(xiāng)村盛行。“而地主往往就是高利貸者。借貸利息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高利貸則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甚至百分之百……”④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永定文史資料》第1輯,1982年9月,第20頁。即使當時鄉(xiāng)村借貸是高利借貸,大部分農民為了維持生計,必須靠借債度日。“農民窮了必舉行借貸,地主乘此機會放高利貸以榨取農民……更使農民破產日亟。”⑤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 (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6頁。此外,永定附近鄉(xiāng)村的農民還經常需要到城市賣柴或賣炭以維持生計。
由上述可見,近代永定的鄉(xiāng)村對城市形成了嚴重的經濟依賴關系,它使農村和農民成為了城鄉(xiāng)關系發(fā)展變化的受害者。
與此同時,永定近代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和沖突:一是在政治上,城市主要勢力包括軍閥、豪紳、地主等與鄉(xiāng)村的對立。辛亥革命后,打著各種旗號的大小軍閥在永定加派軍餉、抓壯丁,任意勒索。在城市或鄉(xiāng)村豪紳則包解捐款、訴訟、勾結軍隊,壓迫農民。“失業(yè)農民和手工業(yè)者當兵及別地謀生的都不過是很少部分,他們大半是為土匪”,由此造成了永定土匪數量非常多,而“匪首與土豪有密切的聯(lián)系。各鄉(xiāng)各村各區(qū),都是形成一種土匪與豪紳相勾結的政權”⑥《趙亦松關于永定工作概況報告》 (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126—127頁。。二是在經濟上,福建全省經濟發(fā)展表現出極端不平衡性,“東南重要城市已是商業(yè)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而西北偏遠鄉(xiāng)村,仍保持原始的農業(yè)社會”⑦《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緊急代表會議文件》(1928年10月),《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213頁。,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加深城鄉(xiāng)之間的對立和城市對鄉(xiāng)村的剝奪,也加重了農民生活的痛苦。三是在思想觀念上,由于近代城鄉(xiāng)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和城鄉(xiāng)差距的凸顯,加劇了城鄉(xiāng)思想觀念的分離,導致了城里人的心理優(yōu)越感及對農民的偏見和歧視。“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對于鄉(xiāng)下人有鄙視輕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fā)生了城鄉(xiāng)惡感。”⑧《閩西斗爭意義與教訓的討論》(1929年1月9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1984年3月,第27頁。
二
鄉(xiāng)村的農民受城市軍閥、地主和豪紳經濟上的剝削、政治上的壓迫和思想文化上的歧視,引起了近代城鄉(xiāng)矛盾的不斷激化。“閩西的工農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極端的壓迫底下,所過的生活簡直是非人類的生活。他們解決 (放)的要求,是萬分迫切”⑨《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關于閩西秋暴工作方針》(1928年7月2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56頁。。“農民最痛苦的是土匪與豪紳的壓迫,……最迫切的要求是要解決生活問題,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他們共同的表現是要求槍枝,要求與豪紳土匪決死戰(zhàn)”①《趙亦松關于永定工作概況報告》 (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129頁。。
1927年閩南特委在漳州成立,并在上杭、龍巖、永定、平和、漳州和詔安等縣發(fā)展農民協(xié)會和組織農民自衛(wèi)軍,廣泛宣傳共產黨關于組織農民、解放農民的主張。7月下旬和8月初,閩南特委在南靖縣召開會議,討論決定今后的任務是深入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廢除苛捐雜稅和減租減息的斗爭,并準備開展武裝斗爭②參見《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4頁。。10月,閩南特委認為永定黨組織基礎比較好,可以首先成立永定縣委。隨后,在金砂公學召開全縣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共永定縣委,羅秋天任縣委書記,張鼎丞、阮山、陳正等人任縣委委員。此時,中共閩南特委書記羅明也來到永定,與羅秋天、張鼎丞、阮山、陳正、曾牧村等商量,提出通過發(fā)動“抗租、抗捐、抗稅、抗糧、抗債”所謂的“五抗”斗爭,借此以發(fā)動群眾;大家還同意以溪南 (區(qū))為中心據點,與湖雷、金豐、下洋等鄉(xiāng)連成一片,發(fā)展革命力量,以形成包圍縣城的態(tài)勢的行動計劃③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永定文史資料》第1輯,第22頁。。
在縣委的指導下,永定縣農民開始起來開展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斗爭。1927年年關和1928年1月,永定黨組織在金砂鄉(xiāng)開展了“反對冠婚喪祭屠宰捐”的運動,1000余名群眾進城向國民黨縣政府情愿,迫使其答應“冠婚喪祭屠宰捐”可以暫時不交。2月,龍門鄉(xiāng)和陳東鄉(xiāng)農民發(fā)動了反抗攤派軍餉的斗爭;上湖雷農民協(xié)會發(fā)動了反對收租、逼債的斗爭;金豐等鄉(xiāng)發(fā)起了“平谷運動”和“借糧度荒”斗爭。4月,由于當時全縣春荒問題嚴重,永定縣委決定在各地開展“分糧吃大戶”的斗爭。這些斗爭使地主、豪紳及國民黨政府十分恐慌。1928年5月,國民黨永定縣政府召開了全縣的豪紳、地主會議,討論“清鄉(xiāng)辦法”,組織“清鄉(xiāng)委員會”,對革命斗爭實行殘酷的鎮(zhèn)壓④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永定文史資料》第2輯,1983年5月,第10—13頁。。此時,永定東溪、西溪的民眾開始上山進行有組織的抵抗,結果引起城鄉(xiāng)交通中斷。“交通斷絕之后,各鄉(xiāng)就發(fā)生經濟恐慌,因在這 (青黃)不接時期,各農民多靠賣柴炭借債生活。那時大地主不肯借債,柴炭又不敢進城里賣,無論大小,甚至自耕農所有銀錢米谷,俱幾乎凈。”⑤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各縣委文件1928—1931年),第20頁。
永定縣各地,特別是靠近縣城一帶的農民,“因為受城里的豪紳政治勢力壓迫太厲害的緣故,常有一種普遍的“殺盡城內人”的觀念……”⑥《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報告——永定最近工作概況》(1928年4月3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第200頁。在革命形勢發(fā)展舞下,廣大農民群眾紛紛要求組織暴動,打到城里去⑦參見朱汝安、顧真:《永定暴動與張鼎丞同志》,《革命回憶錄》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頁。。他們認為攻城可以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好處:一是攻進城里,可以沒收地主、土豪財產,解決目前生活的困境;二是可以殺盡地主和土豪,減少對農村的壓迫;三是與其不舉行暴動被反動派抓走處死或者被活活餓死,還不如發(fā)動武裝暴動,或許還有一條生路⑧參見《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為永定暴動給中央的報告》(其二,1928年8月1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151頁。。對于基層暴動的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有所了解。1928年7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城市鄉(xiāng)村工作指南》中指出:“農民群眾的心理常認縣城是地主豪紳貪官污吏會集之所,以為只要殺戮了在縣城的壓迫者便是農民的天下,因此把縣城看得像很是鄉(xiāng)村的敵人而主張完全毀滅,忘掉城市中貧苦民眾的革命,稍有力量即要求作孤注一擲的攻取縣城或鎮(zhèn)市,不顧城市中工作的重要,不管自己是否可以戰(zhàn)勝城市,也不管打下縣城后的出路如何……”,并提出:“奪取縣城政權,是全縣政權的完成,是全縣暴動最后的一幕,必須全鄉(xiāng)村政權抓在我們手里,城市有了基礎,并且在一省的范圍內這一區(qū)域的暴動不是處于孤立的地位而可以與其他各縣廣大的斗爭聯(lián)成一氣。才能出此一舉”。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526、288—289頁。因此之故,當永定暴動的農民要求攻占縣城之時,永定縣委認為條件還不成熟,要求他們停止攻打縣城。但是,大多數農民不愿意這樣做,而永定縣委始終未能指出不能攻打縣城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致使大部分農民感到非常失望。“有些強悍的人說要去做土匪;有些人罵縣委負責人沒有膽量,怕暴動;有些人自己決定自由干;甚至還有人想先殺了縣委負責人,然后再舉行暴動”。永定縣委在群眾的強烈要求下,決定“與其不暴動而失敗,不如暴動而失敗”,同意農民暴動攻城的要求。②《中共福建省委致閩西特委并轉永定縣委信——對永定暴動的指示》,《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62頁。
1928年7月1日,張鼎丞指揮東、西、北三路攻城隊伍攻打縣城,與守軍展開了激戰(zhàn)。由于守城敵軍不支,暴動隊伍攻進城內。但是,由于群眾是初次作戰(zhàn),熱情很高,也很勇敢,一直向前亂沖;縣委領導同志也缺乏指揮戰(zhàn)斗的經驗,不知道先清除城內殘敵。暴動隊伍與守軍激戰(zhàn)兩小時,雙方相持不下。后來,出城援軍聞訊趕回援助,暴動隊伍被迫撤離縣城,攻城斗爭失敗③參見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閩西革命根據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頁。。不久,駐防永定的獨立第1師2團1營江湘策劃了對暴動地區(qū)的軍事“清鄉(xiāng)”。江湘的軍隊和當地的民團對永定鄉(xiāng)村實行“清鄉(xiāng)”和“割禾”政策,導致暴動各鄉(xiāng)村農民無法安心生產和生活。“各鄉(xiāng)民眾日出操作,夜歸山林,饑寒疾病相繼而來”④《羅明關于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 (1928年10月10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閩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1984年8月,第17頁。。
永定縣委千方百計地想把革命引向建立蘇維埃政和開展土地革命的斗爭,并借此來推進革命的發(fā)展。但是,由于大部分暴動地區(qū)的民眾因為損失過大,內心很想妥協(xié),而此時在金砂暴動時僥幸漏網的一個地主分子寫信回來說:“只要張鼎丞離開,取消蘇維埃,改選保長,那么分了的土地可以按舊不動,其他事情也好商量”⑤中共永定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 《永定人民革命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85頁。。溪南和金豐大部分農民表示愿意與反動派講和。不過,他們內部對“調和”主張并不完全一致。如溪南農民群眾對于“調和”態(tài)度可以分成三派:一派是年老的農民,認為:“我們若無力抵抗他們,那只好調和,使生活可以暫時安定”,并要求共產黨不要把他當作反動派看待。一派是收入比較富足的中年農民,覺得不調和當然最好,但此時又不得不調和;同時還擔心共產黨對他們不好,所以心中想調和,只是不敢出聲。一派是比較貧苦的青年農民,平時參加革命斗爭比較積極,擔心調和之后很難立足;同時也認為自己收入本來不多,如果一旦實現了調和,則無法清償積欠,因此不愿調和。雖然人們對調和態(tài)度持有三種不同意見,但大部分群眾還是傾向于調和的。他們說:“我們目前無力抵抗他們,只好與他們講和,我們才能收禾過冬。同時我們外面雖然掛白,暗中可以我們紅的工作,一待我們力量強大之后,再來斗爭。”⑥《羅明關于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 (1928年10月1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閩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第17—18頁。
三
當永定暴動攻城失敗,革命群眾要求“調和”之際,福建地方黨組織該如何作出自己的回應呢?中共福建臨時省委一方面批判了永定縣委“雖然焚燒了田契債據,屠殺了豪紳地主做得很起勁,可是關于沒收土地、分配土地及建設蘇維埃的工作一點沒去做。……僅僅貼了一些標語,在這些標語中土地革命的標語不過只占了一部分,而大部分則為三大——大燒,大殺,大搶;五抗——抗捐,抗稅,抗糧,抗債,抗租”①《中共福建臨時省委致閩西特委并轉永定縣委信——關于永定暴動的指示》(1928年7月2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64頁。。“本來農民運動發(fā)展到攻城暴動要割據一縣或數縣時,農民的要求很迫切的一定是土地和政權。……可是現在永定農民尚未普遍這樣的政治意識,暴動還是在‘五抗’的口號底下號召起來的,攻城的目的也不是在有意識的奪取城市的政權,而只在‘三大主義’”。這是“農民的落后的意識就支配了這次暴動,并且支配了我們的黨”②《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關于永定暴動等問題給閩西特委的指示信》(1928年8月1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157—158頁。。另一方面,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再三強調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性:“以抗租抗捐兩口號號召群眾,同時特別注意普遍與深入的土地革命與蘇維埃的宣傳”③《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給上杭、永定、平和、龍巖四縣委的指示——關于成立閩西特委及了解永定農暴情況》(1928年7月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32頁。,“要向民眾指出暴動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蘇維埃,實行土地革命,乃是勞苦群眾徹底解放的唯一出路”④《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通告第二十四號——關于永定暴動的原因、經過及今后的任務》 (1928年7月12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52頁。。如果一旦“各鄉(xiāng)斗爭起來時,當召集群眾大會,成立蘇維埃。有兩個鄉(xiāng)蘇維埃時,當即召集群眾大會或代表大會,成立區(qū)蘇維埃。城內鄉(xiāng)村有兩個區(qū)蘇維埃時,可召集群眾大會或代表大會,成立縣蘇維埃”⑤《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關于閩西秋暴工作方針》(1928年7月2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58頁。。
可是,當時永定基層黨組織對福建省委提出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精神反應不夠積極。“暴動已經十余日,攻取鄉(xiāng)村十數個,從未開過一次群眾大會。甚至有些鄉(xiāng)村婦女請我們同志去演說,我們因為‘暴動忙’也都忽略了”⑥《中共福建臨時省委致閩西特委并轉永定縣委信——關于永定暴動的指示》(1928年7月2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62頁。。此時,上杭縣委宣傳部長鄧子恢趕到永定,向永定縣委建議,應按著根據黨的八七會議決議及龍巖、上杭暴動的教訓,立即在暴動區(qū)域進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⑦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黨史研究與教學》1983年第5期。。在福建省委和閩西特委的再三敦促和要求下,永定縣委和溪南區(qū)委通過廣泛地宣傳發(fā)動,把群眾在暴動中煥發(fā)出來的、高漲的革命情緒及時地引導到政權建設上來。各鄉(xiāng)紛紛召開群眾大會,選舉政府委員和主席,建立蘇維埃政權。鄉(xiāng)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立即開展了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8月召開全區(qū)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溪南區(qū)蘇維埃政府,并頒布了土地法、勞動法、肅反條例、婚姻條例等新法令。其他各區(qū)鄉(xiāng)也陸續(xù)在鄉(xiāng)村召開群眾大會,宣傳解釋蘇維埃政權和土地革命意義,領導各鄉(xiāng)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打土豪、分田地,展開以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為中心的革命斗爭⑧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永定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永定文史資料》第1輯,第36頁。。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開展為永定縣的革命斗爭指明了發(fā)展方向。但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卻面臨著敵強我弱的社會現實,無力保護革命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安全,也無法阻止農民向城市中的反動勢力妥協(xié)調和。“最近反動勢力向我們進攻,我們無力抵抗,民眾屢次受了大的摧殘與損失,所以一部分農眾(最初只一小部分)覺得沒有別法應付,只好與反動派講和”⑨《羅明關于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 (1928年10月1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閩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第22頁。。然而問題的關鍵卻在于,在“赤白對立”的格局中,群眾“對于‘今天蘇維埃,明天又坍臺’的政權,實在覺得于他們沒有實際利益,而且有殺頭燒屋危險”10《贛西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贛西報告第七號),轉引陳道源:《二七會議反對贛西南黨內錯誤傾向的斗爭》,《江西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盡管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以及土地革命的開展給農民帶來了相當的利益,如在土地革命中,農民分得了土地;在蘇維埃政權建設,農民得到了參與政治的權利等。然而這種革命所帶來的利益與“殺頭燒屋”的危險相比,顯得根本無關緊要了。
革命群眾因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懸殊,產生了“調和”主張,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此,永定縣委認為與反革命調和妥協(xié)是危險的,并且殺死了群眾派出去和敵人談判的代表①參見中共永定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永定人民革命史》,第85頁。。對永定縣委而言,在攻城失敗后,縣委先后在溪南和金豐等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并開展了土地革命,把日常經濟斗爭引入到政治斗爭的軌道,革命的勝利果實是來之不易的。但是,當蘇維埃政權遭受來自政府軍隊和民團的不斷“清剿”之時,縣委也認識到自己無力抵抗,便于1928年12月底停止了蘇維埃政府的公開活動,開始實行“埋伏”政策。然而,縣委還是不愿意革命群眾同敵人妥協(xié)調和,因為實行調和就會使革命具有和平發(fā)展的危險,“在已有斗爭過的地方,……是消滅第二個高潮的工作”,最終形成了過去是“暴動打到了 C·P·”,以后會是“C·P·打倒了暴動”②《中共福建省委對閩西特委工作的指示——關于武裝斗爭問題》(1928年12月28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372頁。。
閩西特委也反對調和并主張暗殺求和代表③參見《羅明關于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 (1928年10月1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閩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第22頁。。因為閩西特委本來就是適應閩西革命斗爭形勢而建立的政治性組織,永定部分民眾的調和主張不僅與其斗爭原則不合,而且勢必會影響其他地方和以后革命斗爭的發(fā)展。福建省委雖然不贊成調和,但也不贊成永定縣委和閩西特委的暗殺手段。“綁票和暗殺自然全非我黨主要的工作,而且其流弊很大,我們是應當防止的”,“對于主張調和的群眾,我們只能說服,不可用強迫”。當時省委宣傳委員兼巡視員羅明指出:農民具有很強的保守觀念和地方主義,因此很容易產生調和主義④參見《中共福建省委對閩西特委工作的指示——關于武裝斗爭問題》(1928年12月28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371—372頁。;永定縣委和閩西特委實行“殺盡一切調和妥協(xié)分子”的行動是完全錯誤的,必須馬上取消。我們需要向群眾說明調和的利害關系:一是調和有很大的危險,我們不要受反動派的欺騙和蒙蔽,上了他們的當;二是無論調和與不調和,反動派都會想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和剝削我們,決不可幻想調和之后反動派可以對我們作出退讓,我們便可以安定地生活;三是我們目前所受的損失不久可以掙回,此時所受的痛苦不久可以報復⑤參見《羅明關于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 (1928年10月1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閩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第24頁。。福建省委進一步指出了革命發(fā)展的前進方向。“我們的黨必須發(fā)動暴動區(qū)域內的廣大群眾普遍并深入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發(fā)動城市工人斗爭,準備各種革命勢力及各地革命運動相配合相適應的條件,糾正農民落后的意識和盲動的傾向”。只有這樣,“在福建省的革命的前途,與其他省一樣,同是群眾的武裝暴動,推翻現存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前途”⑥《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緊急代表會議文件》(1928年10月),《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221—224頁。。
四
1928年永定暴動起始于農村開展的“五抗”運動,并由此發(fā)展到暴動攻城斗爭。農民暴動要求攻打永定縣城,表面上是城鄉(xiāng)之間經濟聯(lián)系中斷,農民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威脅;實質上則是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的發(fā)展變化所造成的城鄉(xiāng)對立的集中體現。近代以來,軍閥、官吏、豪紳、地主等居住在城市的有產者成為壓迫和剝削鄉(xiāng)村農民的主要對象,農民反對的是居住在城里的剝削者和壓迫者,他們代表著鄉(xiāng)村對城市剝削和壓迫的不滿。然而,當時農民沒有階級意識,“看見壓迫他們的軍閥豪紳,剝削他們的地主捐棍都是從城市出來,就以為城市是反動的象征……”①《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關于永定暴動等問題給閩西特委的指示信》(1928年8月1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158頁。,“在革命進程中,農民常會有落后的反動意識,如不認清階級關系,籠統(tǒng)的反對城市,斗爭一起來便要攻城,便要殺盡城內人,而傾向于‘大燒’、 ‘大殺’、 ‘大搶’的途徑”②《農運工作決議案》,《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緊急代表會議文件》(1928年10月),《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243頁。。這樣,鄉(xiāng)村農民對城市的軍閥、官吏、豪紳和地主等剝削者的仇恨和反抗轉化為“殺盡一切城里人”的農民籠統(tǒng)的反城市的意識③《黨的政治任務決議案》,《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緊急代表會議文件》(1928年10月),《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220頁。。
永定暴動攻城失敗后,被迫撤出縣城,退向鄉(xiāng)村。此時,永定人民的革命斗爭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嚴重問題。福建臨時省委和閩西特委要求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永定縣委對福建臨時省委和閩西特委的指示反應不夠積極,遲遲未能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在福建臨時省委和閩西特委強烈要求下,永定縣委在溪南和金豐等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開展土地革命。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開展的確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但是,革命斗爭畢竟是靠實力說話的。當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領導下的革命力量 (主要是武裝力量)無法保證革命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安全時,永定縣農民對“今天蘇維埃,明天又坍臺”的蘇維埃政權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不信任感。在國民黨軍隊和民團的“剿撫”之下,革命群眾惶惶不可終日,身心俱疲,除了選擇調和,別無辦法。在“赤白對立”的社會格局中,由于敵強我弱的客觀情勢,農民的生存安全選擇優(yōu)先于政治信仰的選擇。他們雖然認識到共產黨是“窮苦人的黨”和土地革命是好的,而日益惡化的生存環(huán)境迫使農民不得不選擇對敵人的妥協(xié)和調和。對調和主張,永定縣委和閩西特委的選擇高度一致,堅決反對并暗殺了調和代表。福建臨時省委不贊成“調和”,也不同意永定縣委和閩西特委對“調和”代表的暗殺行動。福建臨時省委、閩西特委和永定縣委在暗殺“調和”代表上的不同態(tài)度,反映了他們對同一問題,考慮的著眼點是不同的。閩西特委和永定縣委暗殺“調和”代表多少帶有威懾群眾的味道,并借此以維持群眾的革命熱情;福建省委則認為暗殺“調和”代表很容易引起群眾的反感從而失去群眾基礎。由于閩西特委和永定縣委的堅持,最后4個“調和”代表在金砂被暗殺。然而,這種暗殺改策卻無法阻止群眾革命熱情的冷卻,“溪南、金豐兩萬民眾的革命情緒已日見低落,而趨于荀安了”④《中共閩西特委關于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11月2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閩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第30頁。。直到1929年5月,紅4軍第二次入閩,攻占了永定縣城,永定縣的革命形勢才得以恢復和發(fā)展,并成為中央蘇區(qū)的重要組成部分。
永定暴動是近代城鄉(xiāng)關系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的發(fā)生預示鄉(xiāng)村和農民對近代城市的激烈反抗。永定縣委、閩西特委和福建省委對永定暴動均作出了積極的回應,這種回應說明了中共為解救民生敢冒風險的革命精神。然而,在永定農民暴動中反映出來的黨組織和暴動農民之間的矛盾,透析出永定縣委未能完全取得農民的完全信任,也折射出中共要求奪取城市政權的政治需求和農民要求解決生活困境、生存安全需要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另一方面永定縣委、閩西特委和福建臨時省委在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對“調和”代表實行暗殺行動的態(tài)度上的不同,也反映出中共地方組織內部在革命策略問題上的差異性。1928年的永定暴動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前期推動農村革命的生動例證,也揭示出中共內部、中共和農民在關于革命選擇上的不一致性及中共農村革命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