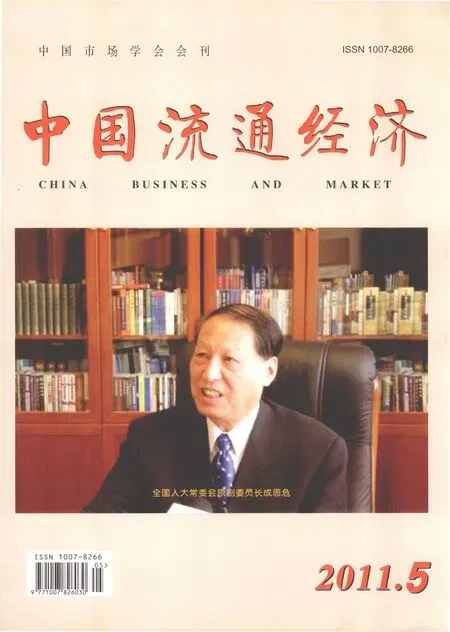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抉擇思考
李廣義
(北京物資學院勞動科學與法律學院,北京市 101149)
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抉擇思考
李廣義
(北京物資學院勞動科學與法律學院,北京市 101149)
目前,我國很多人力資源管理部門越來越鐘情于量化考核,其甚至被異化運用到了物極必反的程度。在實踐中,績效考核量化要發揮應有的激勵作用和效果,關鍵在于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和抉擇。人力資源管理者既要有先進的量化理念,也要掌握科學的量化技術,既要把握量化的正確方向,又要從工作性質的實際出發尋找定量與定性的平衡,充分體現人性化原則及其與工作的高度關聯性。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選擇要有利于改善員工生理和心理健康,采用提升技術、方法創新、優化環境、有效配置、彈性工作等方式拓展效率提升的空間;根據工作性質確定量化的考核范圍與項目內容,量化應以85%以上的員工經過努力能夠達到或超過的水平為標準,讓員工“快樂工作”。
人力資源管理;績效考核;量化;定位;勞動標準
一、問題的提出
量化技術的優勢不容質疑,因此才得以被廣泛運用。但任何量化技術應用超過必要的度,都會走入痛苦的深淵。
在績效考核方面,企事業單位的量化考核遍地開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躍進”式的應用與發展,但績效考核量化卻出現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現象,有些管理者缺乏正確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陶醉于面子工程,拋棄了應有的社會責任,使績效考核的量化成為變相引導造假或者對造假推波助瀾的工具。缺乏依據而脫離實際的績效考核標準,目前正成為損害整個社會成員幸福的潛在殺手。人們普遍存在一種壓抑感,深刻地感到不公卻充滿無奈。有一種幾乎成為社會共識的觀點:“人力資源管理者工作越勤奮,員工就越累,人們就越壓抑”,這無疑是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的極大諷刺。對鬧得沸沸揚揚的富士康14連跳事件、西安交通大學科技造假案、北京大學教改風波等現象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背后的推手與績效量化考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面對過度使用量化考核而出現的資源浪費、過勞死、心理扭曲、道德問題等負面影響,量化考核的科學性受到空前質疑,從早期泰勒對“一天公平工作量”的探索,到今天績效考核量化運用的扭曲,人們必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對績效考核量化進行定位,并對其應用作出科學合理的抉擇,才能使績效考核量化管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績效考核量化濫用現象及其存在的問題分析
在我國績效考核實踐中,績效考核量化濫用現象十分普遍,其帶來的問題也十分突出,分析和揭示這些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進而對績效考核量化進行科學定位與抉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績效考核量化的人性化及其依據問題
人力資源管理的人性化,不是口頭上說說就可以實現的,也不是僅憑良好的態度就可以實現的。人力資源管理的人性化,體現在績效考核的量化方面,主要是績效考核的量化內容與標準確定依據的人性化。這個問題描述的是績效考核量化的內容、標準及其完成這些量化內容的工作方法等。一般來講,績效考核量化的內容和標準更多依賴于勞動定額標準,既包括一定生產技術組織條件的確定,也包括關于特定工作方法前提下的活勞動消耗量的限額,而這種活勞動消耗量與人體的勞動生理規律緊密相關。任何勞動定額都必須在人的生理負荷與供能極限之內,確保工作者的生理、心理衛生與健康。如果拋開特定環境條件以及工作方法來確定勞動定額標準,那么作為績效考核的量化內容和標準就必然缺乏人性化。例如,確定績效考核量化內容與標準的依據,像工作環境條件、技術及管理手段、工作的具體方法以及工作者自身的條件等等,這些依據如果明顯超越人的心理和生理極限,違背自然規律和人類文明發展方向,或者未充分考慮或脫離這一背景,必然成為摧殘人性和榨取高額利潤的工具。
目前企事業單位績效考核量化最為突出的問題在于,工作定額的制定幾乎沒有相對統一的原則可循,大部分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都是以別人的“經驗”為基礎來制定本單位的考核量化指標,隨意性非常大,而很少考慮是否超越了人的生理和心理極限,是否會給人們造成精神壓抑,很少考慮背景因素的影響,也沒有給出一個可以信賴的依據。筆者在對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訪談中看到,勞動定額在有些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已經成為過時的東西,甚至有些人力資源管理者不知道其真正含義,卻可以想當然、依靠經驗或拍腦門制定出量化標準,根本談不上量化標準的人性化。富士康之所以發生“連跳”事件,誰又能說其績效考核的量化內容與標準不是造成員工心理扭曲和壓抑的罪魁禍首呢?!
績效考核量化內容與標準的人性化還體現在定額標準的構成[1]上,包含一定的作業寬放,而作業寬放是科學的量化方法確定出來的,這在國內外都得到認可,具有極強的科學性。但是,在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中,具體績效考核量化標準中不再包含這些沉淀的科學成分,而往往是幾個領導憑著感覺和近似于外行的經驗作出決策,工作定額與人性之間的聯系,被許多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者所遺棄。
績效考核可以量化,但量化的基礎是勞動定額,而且還應該分析量化的背景條件,充分考慮工作方法的人性化,考慮人們體能消耗與休息等需要,考慮工作者生理、心理極限,只有兼顧量化與人性化的統一,績效考核量化才會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有效工具。
2.績效考核量化的工作關聯性問題
績效考核的量化,顧名思義就是將工作目標、工作效果與業績用客觀的量進行考核指標及標準設計和評價的過程,其目的在于消除人為因素對考核效果的影響。然而目前存在一種普遍現象,就是許多企事業單位績效考核的量化內容和標準脫離了工作本身,沒有與具體工作緊密聯系起來,無節制地、生硬地擴大量化考核標準的運用范圍,有的單位甚至為了緩沖管理工作中的矛盾,量化為權謀所用,為領導專權服務,而不是出于工作需要。結果使績效考核的量化指標與工作失去關聯性,從而失去量化考核的基本方向。用這樣的績效考核量化指標評價員工,往往是人人都感覺很累,卻看不到預期的績效結果,而把人們引導到“以指標為中心而不是以工作為中心”,進而把大量的精力投向非工作領域。例如,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張澤認為:“多年來,學術指標化管理、量化管理過度。科研人員把很多時間精力用來跑項目、應付評估,難以安心搞科研,也容易滋生學術腐敗。量化的評價體系不適應學術的內在屬性——原創性和非功利性,學術功利主義泛濫,可能導致學者為達到目的而采取不合理、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與資源分配部門個別人員共謀非法利益,助長腐敗”。[2]
績效考核的量化指標設計與管理之所以脫離工作本身,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閉門造車,缺乏實際工作人員的參與,用主觀或經驗推測的數據作為績效考核標準的依據。例如,對于我國高校英語四級考試一直爭論不休,筆者不想評論其已經成為強制量化標準的對與錯,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國情下,其標準至少是不現實的,尤其是遠離了與工作需求的關聯性。試想,一個人在大學四年究竟什么才是其最主要的目標。從人性化角度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短期內不可能同時實現越來越高的英語目標,如果把學生送到專業的外語學院學習兩年,也許比現在的方法更能節約資源,也更容易取得好的效果。由于考核標準失去了與工作的關聯性,導致人力資源浪費在持續瘋狂地進行著。
第二,管理者缺乏科學績效考核量化設計的技術與方法,隨意使用有關數據的表面信息,生硬地照搬別人已有的量化結果,濫竽充數,粉飾自己在管理上的技術缺陷,使績效考核指標與標準背離本單位實際,進而成為挫傷積極性、浪費資源、強化心理壓抑的工具。一個值得深思的例證就是北京大學的教改。韓水法教授認為,大學本身就是學術研究機構,具有學科上的綜合優勢,應當具有實證研究的意識和責任。他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這場改革事先沒有經過實證研究、不成系統、缺乏后續步驟,這些都是致命的缺點。”大學的決策不應該是拍腦袋拍出來的,這位教授的觀點理性地說明了北大教改為什么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們不擁護,而至少是其自身的科學性問題成為人們質疑的根源。在現代科學文明的社會里,人們沒有理由為一個無法預知后果的改革承擔痛苦和利益損失。可見,這種改革只看到了量化美好的表象,而沒有考慮量化與工作之間的內在聯系。北大教改失敗的最大原因在于,它沒有尋找到一種人力資源管理者可以利用的量化科學方法,卻主觀地、隨意地、過快地出臺了缺乏科學根據的改革方案。
第三,績效考核量化管理的基礎脆弱,不具有開展績效考核量化設計工作的條件。組織內部量化管理的基礎工作包括勞動定額管理、標準化管理、計量管理、信息管理以及崗位責任制。這些基礎性工作是人力資源管理量化的基礎,而這種量化基礎都必須與工作相關聯。
3.績效考核量化的一般標準及其依據問題
績效考核量化的一般標準主要是指績效考核量化指標數值的高低或大小。它決定了員工完成工作的可能性,其主要依據是勞動定額水平,如果量化指標數值過大,員工完成的難度就大,反之就相對比較容易完成。
績效考核量化實踐中,主要難點是對量化大小的定位與選擇,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管理者對績效考核量化指標數值的高低程度缺乏科學的掌控意識,盲目設置高而大的目標,追求面子數據,超越員工的能力、水平和實際條件,結果導致大部分員工無法正常完成,但礙于面子和績效考核的懲罰而不得不采用弄虛作假、透支體力、放棄正常休息、加班加點等方式來達到考核要求,長此以往,就會出現社會資源浪費、極度疲勞導致過勞死、壓抑導致心理扭曲、作假導致社會道德水準下降等負面現象,既給社會、家庭及個人身心帶來損害,也不利于企業效率的持續上升和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4.績效考核定量與定性平衡的定位與選擇問題
定量的美在于其精確,定性的美在于其模糊,而模糊的穿透力不是用量可以衡量的。量化的最大好處是客觀并消除了人為操控的影響,但同時也限制了人們潛能自由發揮的空間,抑制了人們快樂工作的創造力。人間總有量化無法觸及的東西,因此,定性永遠不會消失。人力資源管理最美妙的境界,莫過于達到定量與定性相平衡,精確與模糊相協調。因此,過度量化和對量化的絕對追求顯然不是績效管理的最佳選擇。
傳統定性分析方法的應用范圍非常廣泛,它更加適用于靜態人事管理和職業指導方面,在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定性具有高度的一致認可性,不論是語言的表達方式還是定性描述的用詞,都沉淀著企業背景下的文化認同,蘊含著企業文化的精髓,不需要精確的量就可以準確無誤地表達共同的意愿,而且有更多的靈活性和管理上的回旋余地,這正好符合了人力資源管理對靈活性需求的特點。但定性分析的確具有潛在的局限性。事實上,那些最熟悉的專業語言使用者在用短文把意圖轉達給讀者時也可能出現失誤,更何況讀者的語言理解能力也存在差異。于是,人們持續努力地開發更為科學系統的工作分析方法,更多地最終趨向于定量化,認為定量分析方法的信息傳達明確、簡潔、精準。在實踐中,二者結合使用成為主流,定量與定性各自具有其特定優勢。
目前許多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量化,似乎把人們帶進了痛苦的深淵。從量化考核的無節制擴展,到精英量化價值的無節制推廣,從某種程度上看,人力資源管理在迅猛發展的同時,量化的隨意無節制已經到了有悖人性的巔峰。
江曉原寫下了對現實量化考核的吶喊:《懷念昔日中國科學院的考核制度》。[3]他寫道:“我近兩年來一直在批評學術管理中的量化考核,也許有人會問:你總是說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么好的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呢?”“1984年至1999年間,我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工作了15年,并在那里獲得了我迄今所擁有的所有學術頭銜。至少在此期間,那里就是一處不搞量化考核的地方。”“我知道,如今陷溺在量化考核誤區中無法自拔的管理者們,早已經喪失了理解這種學術管理制度優越性的能力了。沒有量化考核時,研究人員也照樣會做學問,而且可以做得很勤奮。中國科學院系統直到如今,仍然不容置疑地占據著中國科學技術研究的國家隊地位,其總體水準遠遠超出高校系統。這個地位并不是在近年量化考核的制度下得來的,而是在以前實行多年的合理的管理制度下得來的。”
江先生說出了目前許多人想說而未說出的話。同樣,過度的量化考核,讓每一個人付出了不應該付出的精力和成本,而真正用在目標上的時間大大減少了。令人痛惜的是,現實中許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等,在績效考核量化上的浪費是驚人的,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沒有像人們希望的那樣給國家帶來更多利益,給人們帶來更多幸福和公平,而是深切地感受到,在虛假量化管理的旗幟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工作越努力,給員工帶來的痛苦就越多,員工的不公平感就越強烈,社會資源浪費就越嚴重,人們的利益損失就越大,工作積極性被挫傷得就越厲害。當前迫切需要反思人力資源管理在考核量化的道路上如何定位,如何選擇量化與定性的合理平衡。王選院士對學術研究管理的理想環境有過精辟的描述:“給足錢,配足人,少考評,不干預”。在實際中,不同性質的工作需要選擇特定的考核方式,而不能過度依賴于絕對的量化考核。
三、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抉擇思路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績效考核量化要充分發揮應有的激勵作用并達到預期效果,關鍵在于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和抉擇。人力資源管理者既要有先進的量化理念,也要掌握科學的量化技術,既要把握量化的正確方向,又要從工作性質的實際出發尋找定量與定性的平衡,使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真正成為實現組織目標的有效工具。
1.樹立績效考核量化定位與抉擇的先進理念
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抉擇,要考慮社會責任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要有利于社會良好道德與秩序的強化。樹立“快樂工作”的理念,體現在具體績效考核量化設計中,要堅持“三個有利于”:
第一,要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而不給員工帶來過度的心理壓抑與情緒緊張。也就是說,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抉擇是科學合理的,確保其應用的有效性。
第二,要有利于提升“工作少回報高”而不是“多干活少拿錢”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創造輕松愉快的工作環境,向管理要效率,通過管理克服組織中的浪費而不是通過增加工作量來提升效率。
第三,要有利于減輕員工的工作疲勞。也就是說,績效考核的量化定位與選擇要傾向于改善員工生理、心理健康得到滿足的工作方法及環境,采用提升技術、方法創新、優化環境、有效配置、彈性工作等方式拓展效率提升的空間。
2.把握績效考核量化定位與抉擇的正確方向
要很好地把握績效考核量化定位與抉擇的正確方向,需要在具體績效量化工作中考慮下面三個問題:
首先,要判斷績效考核量化的價值性。也就是說,如果要實施量化的績效考核,就必須弄清楚實施量化有沒有價值,是否具有實施的必要性。可能的情況下,還應該列出實施的價值清單,并進行必要的說明。
其次,如果有必要實施績效量化考核,那么要明確量化的范圍和形式選擇,即根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分清楚哪些項目定性考核,哪些項目定量考核,以及量化的考核范圍與項目內容,并決定如何進行量化。量化的形式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數據具有完全的客觀性,一般只要與工作相關,會毫無疑問地被采用;第二類數據具有主觀性,常常需要作出主觀判斷才可以在量化中運用,這種判斷需要衡量。這種衡量分為四種類型:名義標度、序數標度、間隔標度、比率標度。[4]
第三,對量化的程度進行定位與選擇,以確定量化標準的水平。量化標準水平的確定,主要依據勞動定額水平確定的含義進行,保證量化標準水平的合理性。量化標準水平合理主要是指經過努力大多數人能夠達到或超過的標準水平,一般認為應該是大約85%以上員工經過努力就可以達到或超過的標準水平。從完成工作的速度看,這個水平可以用“標準績效”來描述,是指能勝任工作的員工,假設按照規定的方法,并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在一個工作日或輪班內不用過分努力就能自然地完成的平均產量的比率。[5]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英國標準協會的“標準績效”概念的出現,徹底顛覆了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或者增加勞動強度來提高效率的不文明管理,為追求一天公平的工作量奠定了科學的重要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4163-2009,工時消耗分類、代號和標準工時構成[S].2009:4-5.
[2]姜泓冰,陳星星.期待新的科研學術評價標準早日形成 [DB/OL]. 人 民 網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1-03/13/nbs.D110000renmrb_01.htm,2011-03-13.
[3]江曉原.懷念昔日中國科學院的考核制度[J].社會觀察,2006(7):56.
[4]恩尼斯特·J·麥克米科.工作崗位分析的方法與應用[M].安鴻章,等譯.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1991:135-136.
[5]D.A.惠特茂.作業測定[M].任允厚譯.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8:59.
The Consideration on Quantitative Positioning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Choice
LIGuang-yi
(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101149,China)
At present,a lot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ndulge great passion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anagement.But such negative issues as the waste of resources,death from overwork,mental illness and moral problems led by the undue usage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s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And this also aroused unprecedented suspicion about if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s scientific.Starting from the undue usage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the author analyzes some issues of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the problems with the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choice.After tha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practical ways of thinking on quantitative positioning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choic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performance evaluation;quantitative;positioning;labor standard
F243.3
A
1007-8266(2011)05-0108-05
李廣義(1962-),男,陜西省大荔縣人,北京物資學院勞動科學與法律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管理與社會保障。
林英澤